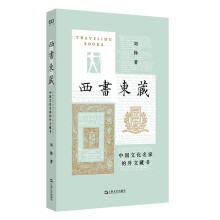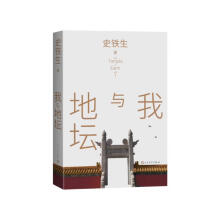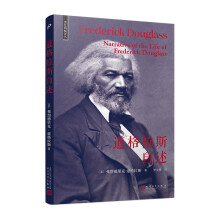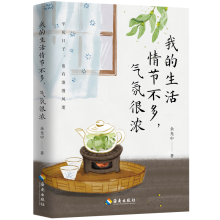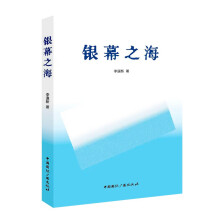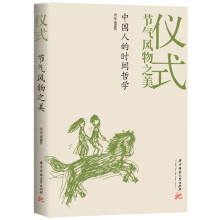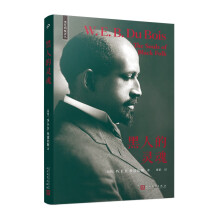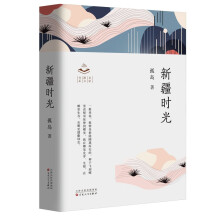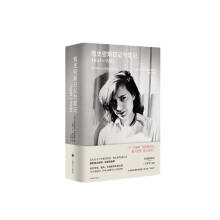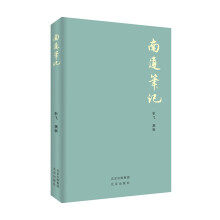《老村庄/里下河生态文学写作计划丛书》:
老大街
儿时的村庄一直珍藏在记忆里,仿佛一张老照片,旧得发黄,也有些模糊。因为年代久,觉着很遥远。有时,似乎近在咫尺,可伸出手去却够不着。村庄的印象如一幅写意的水墨画,有的地方墨重色浓,有的地方浅淡依稀,有的细节分明,有的只是约略的轮廓。
村庄在一块四面环水的垛上,像一片浮在水中的荷叶,大街小巷蔓延着,正好比叶面的茎脉。南北、东西各一条主街、三条辅街,街道在庄中心孙氏老宅大院交汇。南北主街纵贯全庄,被孙氏大院隔成两段,南段在孙氏大院门前与东西贯通的主街成“丁”字交接,南北辅街从东、西两侧经孙氏大院东西两侧延伸向北,先后与东西向的一条主街三条辅街交叉。街道构成博古架的形状,三四百户人家就分布在10多处框格之中。老街展示着村庄的独特风貌,也演绎着乡村人生世相。
这些街道何时形成,没有人说得清楚。老人的说法,都能跟明朝扯上点关系。据说明朝时这里曾驻扎兵营,庄西北第三生产队打谷场上曾留有卞元亨的系马桩。虽然无从考证,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卞元亨,历史上确有其人,与施耐庵是朋友,亦说是表兄弟,还是《水浒传》打虎英雄武松的原型,曾从张士诚起兵。村庄往西四五里地有个叫赦马舍的村子,村名的传说也与当年驻兵有关。往东偏北四五十里的便仓,即是卞元亨的家乡,那儿生长奇异而颇负盛名的“枯枝牡丹”,民间传为当年卞元亨的马鞭插在地里长成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村庄上挖到过一座古墓,里面发现有身穿官服好似活人一般的古尸。查阅老县志,明朝胡顺华撰修的县志记载,时县有四镇:芙蓉、安丰、陵亭、长安。“芙蓉”赫立首位,且注:县东北三十里。村庄至今一直沿用名称“北芙蓉”,且所处方位与县志所注也完全一致。由此可推,村庄的街道或成于明代。
所有街道都是清一色的青砖侧立铺就,十分齐整条实。工艺上充分考虑了雨过地干的效果,每条街两头都通向河边的码头,从庄中心大院处向四面延伸逐渐降低形成坡度,路面也保持“马脊梁”式的弧度,两侧窄窄的水沟。街边人家生活用水从自家院子阴沟排到街道的边沟,就直接顺流下河。下雨天,街道路面的水也是淌到两边水沟再汇入河里。可见,这些街道当初建设时相当精心用心。一场暴雨过后,水洗过的路面在阳光下显得油润清亮,墨玉色质,平滑柔光。几处风蚀剥落破损的大小深浅不一的坑洼,侧边水沟底砖被屋檐滴水形成的凹窝,是时光留下的痕迹,也是岁月沧桑的印记。
街宽不足两米,沿街挤满各户人家房屋。站在一头望过去,狭长不见尽头,远处与天相接连成一线。货郎的叫卖和大人呼唤小孩归家的声音在街道如空谷传响,回荡整条街。街边人家,身在屋里,街上动静听得一清二楚,庄上的新鲜事儿很快会家喻户晓。庄上的人们,不论东头、西头、南头、北头,均相互熟悉,打门前一过就知道是谁,祖上几辈都能扳指头数过来。外村人来庄上走亲戚,走在街上无需看他跨哪一家门槛,邻居就能从来人的长相辨出是哪一家的什么人,热心地笑吟吟打招呼:来看姐姐啊,可好些日子没见你来啦。哪家新女婿上门,那边才进门,街上就议论开来:这家女婿怎的怎的,如此这般一张人物画像便在人们嘴里描述个大概。
白天的街上很是热闹,随处可见小孩三五成群捉迷藏、过家家,蹦蹦跳跳,穿梭嬉戏。小狗、小猫、大公鸡、芦花鸡正在悠闲地晃悠,突然被飞跑而过的孩童惊得四下里乱窜。北街西侧有一口古老的枯井,井栏边不时有小孩趴在上时探究稀奇。近旁的十字街口跨着一座悬空吊楼,楼下面从早到晚总有人团坐在四根立柱的石础上,胡侃神聊,谈笑风生。庄中心商店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店里断断续续传来收音机里刘兰芳说书的铿锵语调。东码头那儿的烧饼油馓店飘过来一阵阵的香味,诱得人满口生津。街边的炒米机旁围满了男女老少,忽然间众人捂着耳朵退散开来,“轰”的一声雾气像硝烟一样弥漫了半条街。铜匠担子的炉火烧得正旺,糖摊子上戴毡帽的老头儿手锣“当当当”敲个不停,卖豆腐、卖麻虾、卖青货的沿街吆喝此起彼伏。满街洋溢着乡村生活的气息,街上的气象生动了整个村庄。
夜晚的街,黑漆漆的,点点星光映照深蓝天穹,穹窿之下灰蒙蒙一片,街两侧低矮的房舍黑乎乎的一团,屋顶与天空形成波纹式曲线轮廓。几扇窗口透出微弱的煤油灯光,仅是消融在黑暗里的一点昏黄。走在街上步伐不能完全迈开,臂膀会不自然的张开,生怕撞上哪一处墙角。远处行人的脚步声十分清晰,一声声震动耳鼓,令人神经高度紧张,走到近前也辨不清面目,相互咳嗽两下,这才全身松弛。倘若一时半刻碰不见行人,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吧嗒吧嗒”,越走到街深处则越觉着有些毛骨悚然。街道仿佛沉入水底,只等天亮再一次浮现出来。
几经拆建,老大街早已不复存在,大明遗镇消遁无踪,曾经的村庄也渐行渐远。时光留不住,毕竟东流去。遥远的村庄,只能从记忆里去寻找。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