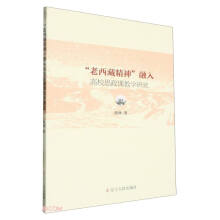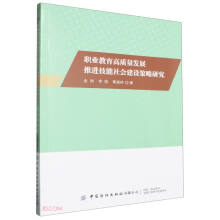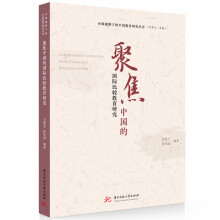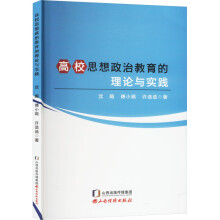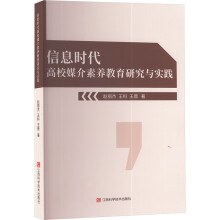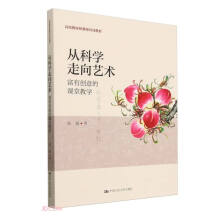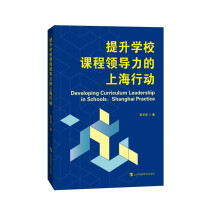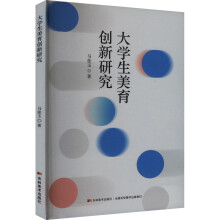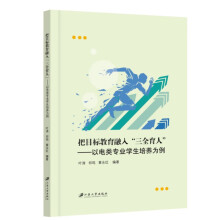序
/李希贵/
这本《教育从何处出发》是汪正贵校长从教几十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晶。拿到这本书后,一个“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求索者的形象即浮现在眼前。
正贵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历史是他的专业,这个专业让他养成了在历史的轴线上思考当下的习惯。一般人熟视无睹或者习以为常的现象、事件、问题,他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会不断追问其来自何方,欲去何处,以及对当下的意义。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诸多苦恼和困惑。大部分人可能到此为止了,而正贵的可敬之处就是随后永不放弃的求索。从这本书的一些篇目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一些问题思考的长度,当然从中也自然看到了他思想的宽度、深度和厚度。因而,在他身上显现的读书人的特征尽管特别突出,但远没有他的善于思考耀眼。
正贵还是一个特别缜密的人,无论是他的思考还是他的处事。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他的条理性、逻辑性可谓出类拔萃。而且他同时还拥有特别突出的开放意识,他接受新的思想、学习各方经验、消化多元信息,其尺度之大令人叹服。他曾经自谦,说是到北京后希望把自己清零。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一说法时,着实有些害怕,因为他身上早就有了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育的情深、管理的意切。自 30 岁起便担任校长工作的历练,让他拥有了常人没有的深沉、从容和淡定,这不仅十分难得,也完全可以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读完正贵的这些文章,我的这一感受更加强烈。
与历史学科有关,也无关,正贵始终如一的表现,让我不自觉地把他作为“人文精神”的形象大使。他的善良,让他拥有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根基。他时时处处对师生天性的关照、包容、呵护,他在面对诸多矛盾、冲突时的选择,他对学校利益、教师利益和学生利益的处理,都让我看到了他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情愫。
文如其人,这本《教育从何处出发》不仅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不忘教育初心的问题,而且还从多个维度告诉我们教育的未来方向,同时在娓娓道来中提醒我们,哪里有教育的暗流和管理的陷阱。正贵的思考、缜密和人文情怀,都在书中表露得淋漓尽致。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正贵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价值追寻的路上,我们应当脚踏实地,扎根现实,聚焦问题,并从中寻找实践智慧。”他如是说,也如是行。我衷心祝愿正贵校长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升华自我,给中国的教育带来新的气象,栽大木以柱长天。
2020 年 12 月 16 日
正文节选
学校是一个什么地方
一、复学记
2020 年 6 月 2 日是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后青岛市小学一二年级孩子复学的日子。早晨,初夏的校园迎来了最后一批回归的小神兽。
孩子们结束了长达四个多月的居家学习,终于迎来了复学。孩子们重回校园,学校又重现生机,有了色彩、欢声和笑语。正所谓,“春风十里,不如校园有你”。一位一年级的学生家长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送孩子上学时看见好几个孩子在学校门口抱着老师又哭又笑的,我看了都感动得鼻子发酸,感慨青岛中学的神奇。您和老师们辛苦了!”
一位老师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开学第一天,早晨在校门口我看到一位母亲开车送女儿上学。母女俩下车后看见学校,看见老师,瞬间泪目。经历过这段特殊时期,我们一定要珍惜和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每一天啊!”
体育、艺术、技术学科的老师们,自发地组织鼓乐队,在校门口载歌载舞,欢迎归来的孩子们。老师们说,孩子们居家线上学习,没有机会见到艺术、体育和技术学科的老师,他们估计,孩子们一定特别想见到他 们,所以特地在校门口欢迎孩子们归来。
一二年级的教师们给每个班准备了一个大蛋糕,为孩子们补过六一儿童节。一年级有一个班的几个孩子提议,应该给校长送点儿蛋糕。我平常不爱吃甜食,孩子们送来的蛋糕却吃得有滋有味。
课间,我去一二年级的教室转悠。在一年级的一个班里,我问他们:“今天有没有同学哭呀?”有个女生举起手,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终于能来学校上学了,高兴得哭了。还有个学生说早上 5 点多就醒了,高兴得睡不着。我问大家,昨晚有没有同学梦见回到学校的,好几个同学说有。
一位家长朋友告诉我,疫情期间,孩子因为想念学校,特地让爸爸开车来学校,在校园的外围转了几圈。
二、教育是对影响的影响
在学生居家学习的日子里,师生都急切地希望有一天能重返校园。现在,师生终于回到校园,重回熟悉的教室和课堂,重回朝夕相见、教学相长的时光。
重返校园曾经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心心念念的事,而今终成现实,我们需要倍加珍惜,珍惜每天和学生面对面的真实的连接和直接教学,珍惜这看似平常而又来之不易的时光。
学生渴望重返校园,教师也期望重回真实的课堂。这让我们反思:与线上教学相比,线下教育有什么不同?学校里究竟有什么?儿童为什么要去学校上学?
有一位家长朋友问自己 10 岁的孩子,为什么想回学校上课,孩子回答:“学校里有老师和同学。”那么,学校究竟意味着什么?教师、同伴对学生意味着什么?
学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还是一个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和场景中,有一种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情感的氛围,这是一种场域。构建这种氛围和场域的核心元素无非是师生关系、课程与教学和同伴交往。
师生关系显然是学校空间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对学生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影响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并不是所有的师生关系都富有教育意蕴,只有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蕴藏着教育的力量,甚至就是教育本身。
顾明远先生说,好的师生关系是最大的教育力量。李希贵校长认为,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师生关系是学校里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关系会产生意义。青岛中学实行全员育人,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实行导师制,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除了师生关系,同伴交往也是学校生活的要素之一。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场所,同伴交往满足了儿童成长的情感需求和社会化需求。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儿童的情绪与情感、道德与伦理、个性与人格、心理与身体等得到健康的滋养和成长。青岛中学发挥 12 年一贯制的优势,推行学长制,构建混龄的成长共同体,让学生在这个成长共同体中,学会做人,学会共同生活。
课程与教学是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校是一个学习共同体,学生在学校里,在教师的指导下,与同伴一起学习知识,建构理解,培养能力和素养。青岛中学视课程为核心产品,开发了近 200 门分层、分类课程,以课程的选择性、丰富性、综合性、贯通性和实践性,为学生的成长服务,满足不同潜质的学生的多样化成长需求,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并成为最好的自己。
学校是这样一个地方:除了教学,还有教育;除了学习,还有校园生活;除了对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还有人格培育和身心的健康发展;除了自我成长,还有同伴交往、合作学习和社会化成长。
学校是这样一个地方:教师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既要启迪智慧,也要培育人格,涵养个性。
学校是这样一个地方: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要学习,还要体验和成长;学生的成长是教育的全部意义,这也是学校之所以成为学校的理由。
因此,我们要给学生带来完满的校园生活体验。完满的校园生活应该是道德的、情感的、智力的、身体的、审美的,是完整的人的全面成长,而不是枯燥、乏味、单调、沉重、缺乏色彩的。如果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只有功课与作业,那么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极其单调、枯燥和沉郁的,学校也就可能成为学生想要逃离的地方。
学校教育是对影响施加影响。学校教育是对最能影响学生成长的几个要素,诸如教师、同伴、课程和教学等,施加教育影响。
三、学校是一个什么地方
学校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学校因什么而存在?儿童为什么要去学校上学?
这些是需要不断追问和回答的问题。
1983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I. 古德莱得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叫作《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A Place Called School)。他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追问:那个称作学校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这样的追问由来已久,从未停歇。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说自己曾经收到一个 10 岁孩子的母亲的信:“我的女儿流着眼泪打开写满了两分的记分册,恳求说:‘妈妈,咱们搬到没有学校的地方去住吧……’”
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作为教育工作者,今天读来,仍然为这个 10 岁孩子带泪的恳求而感觉内心的悸动和愧疚。
日本的教育学者佐藤学先生在他的《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一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诘问:“儿童为什么必须有学校呢?为什么必须上学呢?学校为什么必须存在呢?”
学校应该是儿童的成长乐园,应该是他们喜欢和依恋的地方,而不应该是他们厌恶和想逃离的地方。
“我们从儿童入学的最初几天起,就在他的眼前把通往周围自然界的大门关上了,于是,儿童再也听不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听不到春天融雪的滴水声,听不到云雀的歌唱声了,他只能背诵关于这些美好事物的那些干枯乏味的、毫无色彩的句子。”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样的情况,一直存在。
对全国的学生来说, 2020年的春天是一个特别的体验。长达数月的居家学习,给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特别是给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让人们对学校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在有的地方,不该发生的悲剧在这个春天的复学季发生,让人痛心。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要持续追问和思考:学校,究竟是让学生依恋的地方,还是让学生想逃离的场所?
时代发展到现在,学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问:学校为什么必须存在?学校究竟是什么地方?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抛弃了原初的价值与意义?如何重新定义学校?如何重建学校的意义?这是我们教育人的自我追问,我们必须用实践予以回答。
可能性是教育者的信仰
马克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 ―― 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重新定义儿童:“何谓儿童?看待儿童其实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
儿童就是“包含可能性的实体”。儿童是一粒包含着丰富可能性的种子。儿童的成长过程,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过程,即受教育的过程。教育的使命就是发现、培育和实现儿童的可能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其实,这句话是说儿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即具有可教性。可能性是教育的基础。正是因为相信儿童的生命具有丰富的可能性,相信这种丰富的可能性需要通过教育来转变成现实,教育才具有必要性。
我非常认同沈祖芸老师的说法:“可能性是教育者的信仰。”这是她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我读后为之一振,这个观点与我不谋而合。教育的全部假设都是建立在儿童的可能性和可教性的基石之上,教育者如果没有这个最基本的信仰,教育就无从谈起了。雅斯贝尔斯也认为:“接受教育的勇气是建立在对潜在能力的信任之上的。”
一、儿童应拥有更长的可能性的孕育期
从生物学上来说,相较于其他动物,人类的婴幼儿显得更加脆弱和无能。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幼崽生下来不久就可以站立,甚至能够主动觅食,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成年动物的基本技能,迅速长大。但是也仅此而已,下一代具备的技能和上一代相比,几乎没有多少进步。
但是人类完全不是这样。人类的婴幼儿特别脆弱,刚出生时,如果没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几乎不能存活。《人类简史》这本书推测,人类的婴幼儿都是早产,因为人直立行走后骨盆变小,为了降低分娩危险,人类在进化中自然选择早产。但也正是人类漫长的儿童期,孕育和涵养着儿童无限的可能性。小鸟很快就会飞,小鸭几乎生下来就会游泳,但它们生命的可能性迅速实现并且见顶,而儿童的可能性却不可限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期越长,蕴含的未来可能性就越丰富。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过早地对儿童进行成人化的教育,甚至有人提出延长人类儿童期的主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谈到教育即生长时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需要一个较长的婴幼期,以便获得所需要的力量;这种依赖的延长就是可塑性的延长,或者就是要获得可变的和新奇的控制模式的力量。因此,这种延长能进一步地促进社会进步。”
如果将儿童期看作孕育和涵养可能性的过程,那么我们有理由支持这样的主张;如果将人的成长过程看作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人的成长过程也是可能性不断减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支持儿童拥有更长的可能性的孕育期。
但是,在这个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人们似乎已等不及一朵花的自然开放,更等不及一个人的缓慢成长。儿童期被人为地压缩,儿童该有的欢乐与幸福也被人为地剥夺。儿童过早地背上竞争的包袱,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群体性焦虑中,过早地结束了真正的童年。
这是成长的悖论。越是期望过早地起跑和加速,越是难以在后半程领先。儿童的可能性过早地丧失在教育的功利、短视和浮躁之中,欲速则不达。
二、将童年还给儿童
儿童是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人,而不是小大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儿童是未成年人,处于未成熟的状态,“未成熟状态就是指一种积极的势力或能力――向前生长的力量”。未成熟之“未”有着积极的意义,即拥有生长的可能性,并不是指缺乏什么。儿童期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这种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可能性。
但是,发达的现代媒体和信息技术,使成人的信息过早地充斥在儿童的生活空间中。过去对儿童而言,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秘密,现在却成为儿童的日常话题。儿童与成人的边界日渐模糊。“童年时代,作为人生发展的阶段,也在逐渐消失。” 尼尔•波兹曼专门写过一本书《童年的消逝》,感叹童年期的缩短甚至是消失。
马克斯•范梅南警告说:“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让留给孩子们自己去探索的秘密寥寥无几。然而,这种早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看护者们一样脆弱。” 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充斥着成人化、早熟的文化产品,在文学、艺术、游戏等领域,适合儿童和少年的优秀的文化作品极度缺乏。在教育中,成人化的空洞的教育与规训,也使儿童过早地社会性成熟。
现代社会的速度、压力,以及家长的期望和功利的言行,也在改变着儿童。成人希望孩子快速成长,这无异于拔苗助长,对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儿童来说,是一种善意的摧残。儿童的好奇心、天真与浪漫、创造性与可能性,在过早的成人化过程中被抑制或湮灭。
将童年还给儿童,既是社会的话题,也是教育的命题。
三、教育的最终责任是将人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教育的责任就是发现、保护、培育和实现儿童的可能性。“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被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 拔苗助长和盲目贴标签都是对儿童可能性的摧残。教育是生长,是教化,是存养;教育是农业,是慢的事业,是静等花开。静下心来,倾听花开的声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时代,人们甚至已不愿等待一棵树长大,更不愿等待一个人成长。
尊重儿童的可能性就是按照儿童自己的样子来培育,让他长成他自己的样子。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一个儿童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来将不一样的儿童培养成同样的人。可能性的价值,正在于多样性。
教育是培育,教育是生长。种子蕴含的是可能性,教育就是让种子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我们需要培育它,让它自然地生长。
生长期长的农作物营养和口味都更加上乘,早熟的庄稼则相形见绌。教育也是一样,应该尽可能地涵养儿童的可能性,而不是过早、过快地兑现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内生的,是由内而外地生长,而不是靠外部的塑造。
教育的责任是实现可能性,而不是消灭可能性。“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展,教育不能改变人生而具有的本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天分中沉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是生命的潜能。教育的最终责任是将人潜在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让他成为他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教育的全部使命,“正是在这种自我发展的可能性问题里教育学找到了它的真正含义”。教育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大抵如此。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