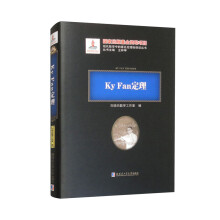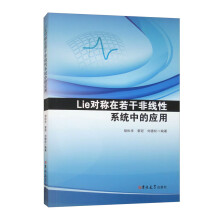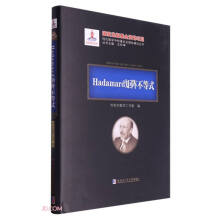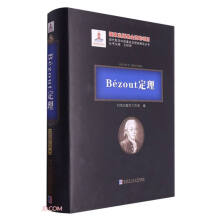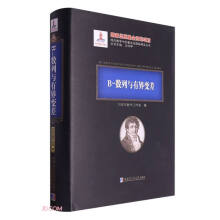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
天文学史的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二十五史中的《天文志》《律历志》都是总结当时天文学上成就的文章。历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史也都是相当熟悉的。例如,一行的《大衍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奏议》,都将天文和历法的演进说得很清楚。这一优秀传统到了清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钱大昕(1728~1804)、阮元(1764~1849)、李锐(1768~1817)和顾观光(1799~1862)等对中国天文学史都曾作出重要贡献。阮元和李锐等编辑的《畴人传》,搜集了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不少史料,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便利条件。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内,朱文鑫做了不少工作。他编著的《历法通志》《历代日食考》《天文考古录》《天文学小史》等书都有相当价值。此外,竺可桢、钱宝琮等人也有一定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科学工作者负担着一个新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编写祖国的历史。在自然科学史方面,中国科学院于1952年召集对科学史有兴趣的科学家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来讨论如何开展工作。1954年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规划与协调有关科学史的研究与编辑工作。1956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关于天文学史的有4篇。9月竺可桢副院长率领代表团到意大利参加第8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在提出的论文中关于天文学史的有3篇,即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问题》[1]、钱宝琮的《授时历法略论》[2]和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3]。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室内设天文学史组。两年来,这个组的干部配备逐渐有所加强,目前正在组织协作,准备写出一本“中国天文学史”。
1957年2月6~11日,中国天文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和紫金山天文台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一并在南京举行。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钱宝琮的《盖天说源流考》和席泽宗的《汉代关于行星的知识》等4篇是属于天文学史的。
十年来,天文学史方面的普及工作也做了不少。1956年5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的地方成立了中国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作为一个永久机构,宣传我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成就。
现就十年来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论文,选择几个重要的项目,分别介绍于后。
一、关于盖天说的研究
钱宝琮对《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曾研究多年。他在《盖天说源流考》这篇文章中总结了他对于盖天说的研究[4]。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先根据《周髀算经》介绍了盖天说的内容,并指出《周髀算经》中所用的观测数据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因此“很难认为都是实际测量的结果”。作者进而讨论盖天说中的七衡六间图,并指出它的困难。作者也讨论了该书中所用的测量二十八宿距星间度数的方法。论文的后半部分讨论了盖天说的产生时代。作者指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大概是*原始的“天圆地方”说。这种说法后来修改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像《周髀算经》中所说的。作者指出盖天说中关于二十八宿的知识符合前汉初年天文学的水平。因此,作者认为修改过的盖天说是在前汉初期产生的。作者指出盖天说的主要内容是把关于天的高明、地的广大、昼夜的更替、四时的变化等感性认识加以整理,提升到理性认识。它虽然有些假借形象和勉强配合数字,但基本上是合于客观现实的,对当时天文学的发展起了主导的作用。
二、中国史籍中客星记录的整理
中国史籍中关于客星的资料甚为丰富。所谓客星就是现代天文学上的新星与超新星。新星与超新星的出现表示一种爆发过程。当代的天体物理学工作者认为爆发后的星虽然暗到无法用光学望远镜观察到,但是它可能变为一种射电源而可用射电望远镜观察到。因此,古代的客星所在之处现在还可能观察到射电源。1955年,席泽宗从中国史籍中整理出90项可能的客星记录,编成《古新星新表》[5]。这篇论文引起了各国天文学界的注意,因为它可能帮助天文工作者寻得还没有发现的射电源。
这篇论文对于回答天体演化学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例如,在银河系内,超新星爆发的频率如何?新星是否能多次爆发?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得出平均每150年银河系内有一次超新星爆发的结论。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认为除了现在已知的七颗再发新星以外,可能还有两颗再发新星(一在牧夫座,一在武仙座)。
三、宋代水运仪象台模型的制作
中国古代用壶漏的方法测量时刻。但时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天球运转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得人们相信可以把天球的运转当作均匀运转的标准,也就是说,当作时间的标准。因此,标准壶漏的基本方法就是把壶漏所给的时刻与天球运转所给的度数相比较。汉代的张衡创制了水转浑天象,唐代的一行和梁令瓒又有所改进。到了宋代元祐年间,用水为原动力的机械运转装置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苏颂等用这种装置创置的水运仪象台是在1088年完成的。苏颂所编的《新仪象法要》就是这个台的详细说明书。很可欣幸的是这部书现在还存在。195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王铃和普拉斯( Derek J. Price)把《新仪象法要》的内容和欧洲中世纪的天文钟做了比较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所代表的“中国天文钟的传统似水运仪象台的模型乎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6]。
因为宋代的水运仪象台对于天文学及钟表机构来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应该做出它的模型,作为历史博物馆中的一项重要陈列。1958年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照耀下,王振铎和故宫博物院以及中央自然博物馆的工人一道,做出了宋代水运仪象台的模型。模型制造比例为原大的1/5,但已有2米多高[7]。此外,刘仙洲也介绍了历代的水运浑天象[8,9]。1956年12月他又发表了《中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一文[3],对唐宋以来用水力和沙漏的仪器的主要机轮的相互关系做了分析。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正在就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仪器,如五轮沙漏等进行复原。
水运仪象台复原透视图
①浑仪;②鳌云、圭表;③天柱;④浑象、地柜;⑤昼夜机轮;⑥枢轮;⑦天衡、天锁;⑧平水壶;⑨天池;⑩河车、天河、升水上轮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来的中国天文学史工作,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新的开端。中国史籍中与天文学史有关的丰富资料还需要用科学方法加以系统地整理。世界天文学史的广阔园地还有待开辟。未来的任务是繁重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ГоЦзин-чy.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ученияодвадцатнвосьмнзнакахлyнногo Зoдиака.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иТехники,Вьщ.4,1957:56-62.
[2]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天文学报,1956,4(2).
[3]刘仙洲.中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天文学报,1956,4(2).
[4]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科学史集刊,1958(1).
[5]席泽宗.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3(2).
[6]Needham J,Wang L,Price D J. Chinese astronomical clockwork. Nature,1956,177(4509):600-602.[中译文见《科学通报》,1956(6)]。
[7]王振铎.揭开了我国“天文钟”的秘密.文物参考资料,1958(9).
[8]刘仙洲.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机械工程学报,1953,1(1).
[9]刘仙洲.中国在传动机件方面的发明.机械工程学报,1954,2(1).
〔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天文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作者:叶企孙、席泽宗〕
中国天文学的历史发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天文学总是*早开始的一门科学,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要依照四季循环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决定他们的行动。远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我国的劳动人民大概就已经注意到,每逢初昏时在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亮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到了殷代已经有了日食记录,有了简单的计时制度。现在可以肯定,那时已经用干支记日(即用甲子、乙丑 排列日序)。对于西周的历法,我们虽很不清楚,但从已出土的金文来看,知道当时对于月亮的圆缺变化非常注意,《诗经》里的《七月》一篇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天文文献。
《春秋》与《左传》两书中有丰富的天文资料,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中记录了37次日食,其中有32个已经证明是可靠的。“(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哈雷彗星的*早记录。大概在春秋中叶已盛行用土圭来观日影长短的变化,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那时把冬至叫作“日南至”,以有日南至之月为“春王正月”。《左传》中共记有日南至两次:一次在鲁僖公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