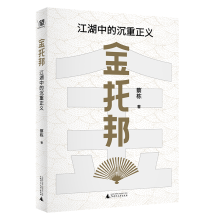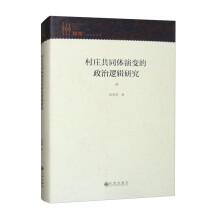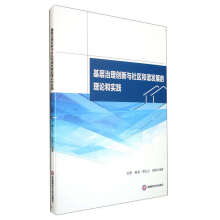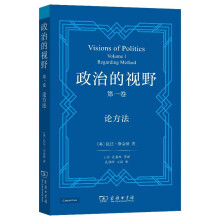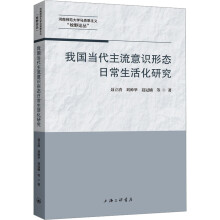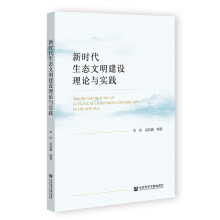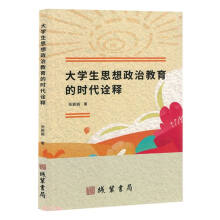《意识形态批判:吉登斯与马克思的跨时代“对话”》: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货币
吉登斯看到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现代社会更加凸显。对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吉登斯主要归功于“货币”。作为脱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载体,货币实现了跨地域的时空重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借助货币得以脱离地理限制,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再现。
(一)标准化是货币得以组织时空的基础
在吉登斯看来,作为一种标志符号,货币不仅仅是商品得以流通的一种物理媒介,站在社会关系的角度,货币同时还是一种信息媒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货币本身向人们传达了一种信息,即货币可以实现一切交换。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这已成为一种常识深藏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中,它是人们默契于心的一种交换法则,无须言说便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顺利展开。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货币被称之为‘多才多艺的妓女’,她是这样一种交换工具,不论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用非个人的标准去代替它们。”①吉登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比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货币的一大特征即是“标准性”。货币的这种特征对于现代社会缺乏选择标准的人们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心理安全。正因为如此,进入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量化标准,以精准的数字来衡量各种事物的价值,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货币来实行交换,包括劳动力。由此,货币构成了无所不能的符号象征,它被赋予了一种权威形象。
货币的标准化属性使得处于不同时空的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都能够进行经济交易,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时空延伸范围。它打破了地域经济活动的限制,是时空得以延伸的一种重要工具和载体。
(二)货币关系中的信任危机
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活动是现代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一种惯例。作为生活常规,各种常见的经济活动是人们获得稳定心理的一大保障,它同样能够提供“继续下去”的生活信念。“但是这里信任的,是货币本身,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信任那些用货币作具体交易的人。”①也即,货币交换得以作为一种结构化存在,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交换双方都承认货币的价值,并且按照这种价值进行交换。因此,货币成为一种“信托物”,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出的“信用货币”和“信贷”,便承载着货币延期支付的一种信任。“信用货币……它所依赖的是人们对居于国家边缘地带的商业组织之生产能力的信任,还依赖于国家自己对自身的通货价值的担保。……它是产品的商品化交换得以在全球推广开来的前提。”②
现代全球交换系统的建立是以信任作为依托,这种信任一旦发生危机便会导致全球性的灾难,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便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吉登斯也看到,以货币所维系的社会关系是脆弱的,它所提供的本体性安全只能在基本层次上得到较好的维持。现代人反思性和怀疑性的增强,时刻威胁着彼此之间的信任。一方面,人们渴望按照货币的标准性进行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互动;但另一方面,支撑这种公平交易的信任感又遭到人们反思性的解构,因为交易中的欺诈现象屡见不鲜。人们只能将信任和认可更多地寄托于货币本身。
(三)货币知识的不对称催生出货币意识形态
作为组织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货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借助货币的标准性向全球渗透,与此同时,隐藏在货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化经济交换活动而被带到世界各地,并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货币已成为一种权威,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标准尺度和不可或缺的意义框架为其塑造了坚实的合法性。但在现代货币关系和全球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背后,事实上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在进行着全盘操控,这种支配关系恰好借助人人习以为常的日常经济活动得以再生产和巩固。
吉登斯看到,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促使货币资本的计算形式发生了新的改变。“虽然较大的前现代社会体系也都发展了某种货币交换,但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成熟,庞大的货币经济则更为精致,更为抽象了。”①例如成本、利润和亏损指标的计算包含了货币本身,它们被列成表格或编成索引,并以纸张或其他记录媒介得以标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货币不再具备物理形式,而是以信息形式得以储存和调配。这些复杂的计算程序构成了新的知识成为人们掌握和使用货币的资源。但是日常生活的普通民众,通常只能掌握简单的货币知识,他们视这些知识为“常识”并例行化地进行交换活动;而更为复杂的货币知识往往为精英集团或资本家所掌握。后者利用这种知识的不对称可以从大量普通民众那里获取意想不到的货币收益。在这种意义上,货币便成为资本家敛取财富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为普通民众所不知晓的是,他们用来维护自身稳定需求的例行化经济交易活动事实上正是资本家动员货币这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渠道,而后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