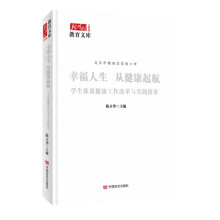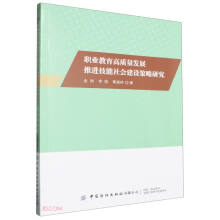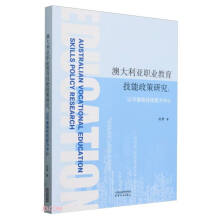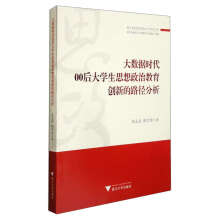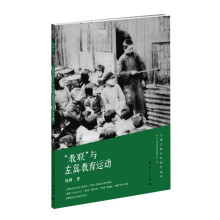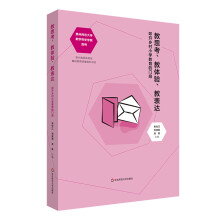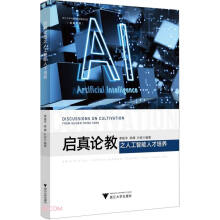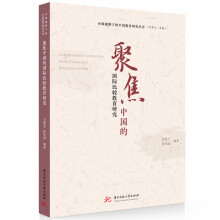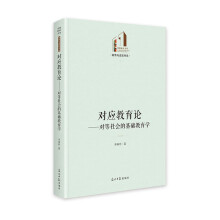引言
0.1 研究生教育学的特征
研究生教育学有如下特征:一、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链的*高端;二、研究生教育的运行动力可划分为宏观 (国家范围)、中观 (大学范围) 与微观 (学科范围) 三个层次;三、研究生教育受到其内在体制结构的影响。上述特征之一使得研究生教育学在教育学的一般框架上添加了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的本质内涵。前者使得我们必须在学科空间上探讨研究生教育学;后者使得研究生教育不光涉及资源的配置,还伴随有资源的增生 (即知识与人才的新生) 和教育成果的转化。特征之二预示着研究生教育将包括以培养机制、知识创新动力和学科发展动力等为核心的微观教育学理论;以学科协同发展、学位品牌塑造、跨学科研究生管理等为核心的中观教育学理论;以宏观资源配置、调控、管理、发展预测为核心的宏观教育学理论。特征之三预示了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管理结构和导学结构这些内变量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在中国所具有的研究生教育历史短、体量大,实行以国家学位为底线保障,以学校学位为品牌背景的特色下尤为如此。
0.2 研究生教育的经济基础
研究生教育与其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功能有关。
研究生教育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物,其学科结构依赖于社会的认可与学科资源的投入;在某学术机构或学科实施研究生教育时,也需要满足其对应的经济门槛。当一个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时,其研究生教育只能以零散的、精英式的、师徒传承的方式出现。经济基础和信息传播水平决定了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结构和平均水平。研究生的规模化教育是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为背景的教育;分门别类的专业学位教育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出现了细化分工而产生的结果;学术产出的激增和学术型博士学位的预设学术认可度门槛是学术出版界信息通畅化的结果。
首先述及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这可以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来予以讨论。从需求侧来说,一个国家的研究生总量需求取决于其人口总数与人均 GDP。后者与社会人口构成的知识结构有关。中国每年新出生婴儿 1000 万—1500 万。在可预测的将来 (如二十年后),可能其中的 80% 将会受到高等教育 (当前略高于 50% ),20% 将会受到研究生教育,这样我国可能每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就会高达 200 万—300 万(作为参照,我国 2020 年的研究生招生约为 110 万人)。这样在二十年内,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可能会达到目前规模的 2—3 倍。这样的年增长率超过 6% 的发展速度,如果没有人均 GDP 的中高速以上的增长是无法支撑的。今后二十年,我国人口的知识结构可能从现在的金字塔型逐渐变为橄榄型,即具有博士、硕士、学士、大专或高职、高中/中专或中职、初中、小学及以下的教育层次经历的人口比例演化为 5% 、15% 、30% 、30% 、12% 、5% 、3% 。从供给侧来说,学术型研究生总量与总人口与基础研究投入的乘积有关。目前我国的人口约为美国的4 倍,而基础研究经费数 (按照汇率计算) 约为美国的 1/6,若进行购买力平价修正 (PPP) 则大约为美国的 1/4[1],而我国学术型研究生的数量恰与美国大致相当。二十年后,基础研究经费的一半,以及学科建设经费中的一半都将转化为支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而届时学术型研究生的规模和层次比例会发生较大变化。专业型研究生总量应与人均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研与开发) 比值有关,后者决定了专业化的层级门槛和其分工的细致程度。同时,中国的学术产出量与研究生人数正相关。由中国产出的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论文大约有 1/2 以上是以研究生作为生力军而完成的。
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也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相关。在前工业化阶段,人文、农学、医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先得到发展,起到了人类文明的启蒙作用。在工业化为主要驱动引擎时,对理工科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无论是工作岗位还是社会观念认同) 走到了舞台中央。在信息化发展加速时,信息科学变得炙手可热。如当前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五年后的薪酬分布出现双峰,而高端峰就是由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薪酬而造成的反常峰。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这些与上层建筑相关的领域,其对研究生的需求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比例。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财务自由的逐渐逼近,人们将逐渐青睐于更能体现个性自由发展的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与艺术;或从仁者爱人的理念出发,投向与生命和精神联系更紧的学科,如医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等。
0.3 研究生教育的文化传承
研究生教育的文化传承体现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四种发展模式:以英国绅士淑女型教育为背景,以好奇心驱动为动力的书院式研究生教育;以德国哥廷根学派为代表,以学科群师徒传承为特征的集群式研究生教育;以美国“二战”后在研究生院管理框架下的大规模、多学科的集成式研究生教育;以中国在*近二十年形成的,以国家、地方、学位授予单位实行的多层次管理与调控为特征的动力型研究生教育。
作为东方文明的传承大国,中国近代的研究生教育表现出文化传承的复杂性和高速演化特征。首先是有着横跨两千余年的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传承,体现了人文学科的论理与思辨特征,以及随之而来的士人的清流教育传统。接踵而至的是书院式的集群性教学的方式,秉承师徒相传的导师制度。启蒙自 20 世纪的研究生教育,其内容与方式的综合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既有人文学科的孔孟之道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自省精神;又有社会科学的数据科学和意识形态特征,理科的西方科学文化特征,应用学科 (工科、农科、医科) 的理论联系实际特征。不同的学科教育模式*后在现代大学理念上得到了统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导师制下的精英研究生教育形成了我国*初的现代研究生教育文化。“文革”之后,研究生教育重启,又赋予了国家品牌、学位点控制等新内涵,逐渐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研究生教育新文化。研究生教育这一新的规模教育层次带来了两个新动力:一是各个学校的层次分化和层次跃升动力;二是学科建设的动力。从学位点申报、“211 建设”、“985 建设”、重点学科评估、一级学科评估、到“双一流建设”,研究生教育的新动力成为各个学校发展的*强音。从“211”/“985”到“双一流”,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学绘出了可称之绚丽的发展轨迹,乃至于美国科学理事会在其 2020 年度的《科学与工程索引》长达千页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挑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1]。
人民需要满意的教育:需要满意的幼儿教育,满意的小学、中学教育,满意的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满意的普通大学教育等等。然而,*上位且通往希望之巅的,是满意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教育。***同志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 如果说:从一流幼儿园到一流大学,是家长们望子成龙的长征;而这一长征目的地是世界一流大学。办好幼儿园,是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办好中小学,是为了叩开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之门;办好职业教育,是为了不同职业的均衡和谐发展;而一流大学,是全国人民神往的子女教育的终极目标,是王冠上的明珠。若我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的好苗子就会大量流失到国外一流大学中;我们的孩子尽管没有输在起点,却无法在祖国向终点冲刺;整个教育,将失去其追求的*高目标。多少间大学,都把“双一流建设”视为其中心任务;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把“双一流建设”视为其教育战线的头等大事;每家企业在制定其人事政策时,都体现了对“双一流建设”大学毕业生的青睐;每一名家长,都期盼着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就读。综上所述,“双一流建设”是全国人民对教育的*大期盼。
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路线固然有上述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个弊端,即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交融和整个大学 (University)理念的彰显。在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各个学科竞赛发展的态势下,跨学科的交融存在理念上、体系结构上、人事制度上、评估体系上的困难。强大的学科以吃掉弱小学科的资源配置为荣,它们更乐于见到学科之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山形结构,而不是多中心的川形结构或大协作的网联结构。理科和生命科学愿意在全校宣贯引用性评价和国际影响力,工科与医科愿意以实用性和大项目论英雄,文科愿意更多地谈论深刻性与引领力;行业性学校着重于对领域的渗透性与贡献度,综合性大学更愿意谈论总体实力。研究生教育的文化是一个多重文化、特色文化,同时也是一种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 [3] 的文化。
0.4 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学功能
高等教育的社会学功能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层次流动与地域间流动。这种地缘社会学的概念也不完全都是正面的:一方面,它对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人群提供了一种凭借个人或家庭的努力而向上攀升的动力,包括社会层次与地域的攀升;另一方面,它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人群与区域起到一种 “人才荒” (Brain Drain) 的抽吸作用,使得社会层次与地域差别更为固化。由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大多不能达到自我创业的能力,且在相对欠发展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又有去发达地区高校攻读研究生的动力,所以在欠发展地区的本科高等院校,除了部分解决教育公平的目标外,并不能全方位地解决地区发展的人才配置差异。
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学功能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4],地方的治理者无不想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的申请,带动区域社会发展,从而提升教育为社会服务的等级。在著者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期间,办公室所收到的两会代表委员建议或议案提案中,就有大约一半是建议在该区域或增设“211 建设”高校,或增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研究生教育是高级人才社会流动的高动能通道,并往往成为高级人才就业的地域起点。教育层次越高,非本省生源的比例就越高;教育层级越多,社会层次流动与地域间流动的渠道就越多;博士后和跨国境研究生教育加强了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学功能。它起到了三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