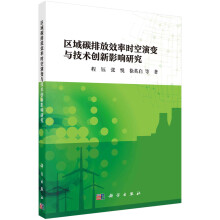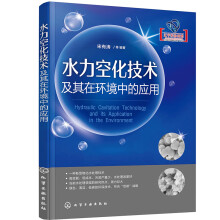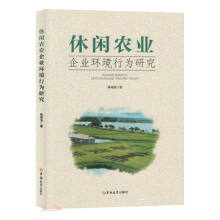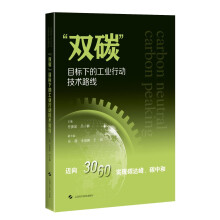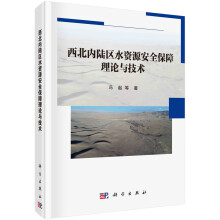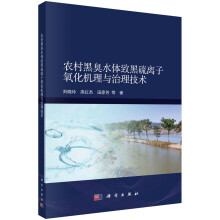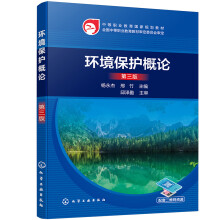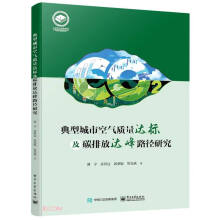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土壤侵蚀是世界性的重大环境问题。强烈的水土流失是生态环境恶化、土地资源退化乃至彻底破坏的重要原因,制约了土地生产潜力的发挥,严重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与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悖(Wei et al.,2016;Li et al.,2016,2011a,2011b;唐克丽,2004)。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高原是全球黄土分布面积*广、厚度*大、地层分布*全的高地,面积约为63.5万km2,是我国乃至世界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陡坡侵蚀、沟道侵蚀独*且严重,产沙强度高。因此,它以强烈的土壤侵蚀并向黄河输入大量的泥沙而著称于世。研究表明,黄土高原向黄河贡献了97%的泥沙(胡春宏等,2020a;刘晓燕,2020),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Zhaoetal.,2019;刘晓燕等,2017;Wei et al.,2016;Li et al.,2016,2011a,2011b)。然而,黄河泥沙每年约有4亿t淤积在下游河床,使黄河下游形成千里“悬河”,直接威胁着黄淮海地区人民的财产安全(穆兴民等,2014;水利部等,2010)。“黄河之患,患在泥沙”,泥沙问题一直在黄河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加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减少入黄泥沙,根治黄河水害,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先后开展了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淤地坝建设和坡耕地整治等一系列生态工程(胡春宏等,2020a;Fu et al.,2017),使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地表覆盖条件发生强烈演变(胡春宏等,2020a;Feng et al.,2016;Chen et al.,2015)。经过几十年的水土流失治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李宗善等,2019;刘国彬等,2016;董仁才等,2008;刘震,2005),黄土高原主色调已由黄变绿,入黄泥沙量由1919~1959年16亿t/a锐减至2000~2018年约2.5亿t/a(刘晓燕,2020;陈祖煜等,2020;冯家豪等,2020;胡春宏等,2020a,2020b,2018;Zhengetal.,2019;穆兴民等,2019;Wang et al.,2015;Yueet al.,2014)。虽然从总量上来看黄河泥沙显著减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问题得到了控制和解决。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复杂影响,严峻的水土流失仍是黄土高原地区*大的环境问题。大量的泥沙不但加剧了黄河的洪水灾害,严重威胁着黄河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且给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可以说,能否在黄土高原地区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是根治黄河之患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我国经济繁荣昌盛的进程。
实践证明,单靠坡面水土保持措施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当地严重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状况。因此,以小流域为单元,坡面、沟道综合治理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被广泛应用(刘国彬等,2016;彭珂珊,2013;董仁才等,2008;王礼先,2006;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2005;刘震,2005)。现今,小流域综合治理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但由于缺乏权威和标准的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董仁才等,2008),且不能全面反映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流域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董仁才等,2008;康玲玲等,2002)。淤地坝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径流泥沙控制的昀后一道防线,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坝地淤积物记录着淤积年限内坝控流域气候变化和侵蚀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对于上方没有任何支流汇入,坝体附近没有任何泄洪设施的“闷葫芦”坝,其坝地淤积物全部来自坝控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表层或者更深层的土壤。因此,“闷葫芦”坝坝地分层淤积物所蕴含的分层淤积信息可以反映坝控流域淤积年限内的水土流失情况,对分析坝控流域土壤侵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已有研究认为土壤是一种具有分形特征的分散多孔介质,土壤颗粒分形维数是反映土壤结构几何形状的参数,表现为黏粒含量越高、质地越细,分形维数越大;反之,砂粒含量越高、质地越粗,分形维数越小(Weietal.,2016;方萍等,2011;Liu et al.,2009;苏永中等,2004)。此外,土壤颗粒分形维数能客观地反映退化土壤结构状况和退化程度,可以作为退化土壤结构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鉴于此,本书对陕北黄土高原的淤地坝进行实际调研与勘测,选取典型淤地坝,提取其坝地分层淤积物信息,利用分形理论,评价淤积年限内典型淤地坝坝控流域已有水土保持措施的合理性。
1.2研究进展
1.2.1淤地坝建设与发展历程
淤地坝是指在水土流失地区的各级沟道中,以拦泥淤地为目的修建的坝工建筑物,主要用于拦蓄坡面径流泥沙,是防治沟道侵蚀的主要工程措施之一。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同水土流失的斗争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既能拦截泥沙、保持水土,又能淤地造田、增加粮食产量而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淤地坝坝前淤积的泥沙稳定和抬高了沟道侵蚀基准面,防止沟底下切和沟岸坍塌,控制沟头前进和沟壁扩张,可拦泥、蓄洪和削峰,减少入河入库泥沙,减轻下游洪水泥沙灾害,且淤积的泥沙颗粒养分含量高、水分条件好,因此坝地生产力明显优于坡耕地,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淤地坝的主要作用和效益具体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1)沟道坝系建设是治理水土流失和减少入黄泥沙的关键措施
沟道是径流泥沙的集中通道。有数据表明,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40%的沟谷地,其产沙量能占到总产沙量的60%以上。沟道淤地坝工程建设能够快速、有效地拦蓄径流泥沙,抬高侵蚀基准面,遏止沟床下切、沟岸扩张和沟头前进,降低重力侵蚀的发生概率,从而减少进入流域下游的径流泥沙量。实践证明,不论是较大区间的重点支流,还是较小流域,淤地坝工程拦蓄径流泥沙作用显著,是其他水土保持措施无可比拟和无法替代的。
2)沟道坝系建设是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退耕还林还草的基础
沟道坝系工程将洪水泥沙就地拦蓄,水土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荒沟变良田。在人多地少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淤地坝建设成为增加基本农田面积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由于淤地坝所拦蓄的泥沙大多来源于流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表层的土壤,腐殖质含量高,相应有机质含量也高,坝地水分充足,坝地地表比降小,给粮食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3)淤地坝建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淤地坝工程拦减了入黄泥沙,保护了下游安全,并且泥沙就地截留淤成坝地,实现了水沙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同时,淤成的坝地变为高产、稳产的农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尤其是随着流域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水地、坝地、梯田等基本农田面积逐年增加,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大量陡坡地得以退耕还林还草,为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创造了条件。由于黄土高原大规模建设淤地坝系,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劳动强度,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促进了群众脱贫致富和区域经济发展。
4)淤地坝抬高侵蚀基准面且降低重力侵蚀发生的风险
淤地坝拦淤泥沙后,侵蚀基准面抬高,阻止了沟底下切,使沟道比降变小,延缓了溯源侵蚀和沟岸扩张,提高了沟道的稳定性,降低了滑坡、崩塌、泻溜等重力侵蚀发生的风险。同时,淤地坝运用初期能够利用其库容拦蓄洪水泥沙,还可以削减洪峰,减少下游冲刷,减缓地表径流,增加地表落淤。淤地坝运用后期形成坝地,使流域产流、汇流条件发生变化,从而起到减少洪水泥沙的作用。
5)淤地坝建设能以坝代路且便利交通在黄土高原地区,长期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千沟万壑的破碎地貌。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是制约黄土高原地区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修建淤地坝后,可以实现坝路结合,坝顶成为连接两岸交通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坝系经济区交通网络的形成,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促进了物资、文化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因此,淤地坝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一道防线,通过其“拦”“蓄”“淤”的功能,既能将洪水泥沙就地拦蓄,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又能形成坝地,充分利用水土资源,使荒沟变成了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效解决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和干旱缺水两大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在黄土高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的淤地坝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50年代的试验示范阶段,60年代的全面推广阶段,70年代的高潮阶段和80~90年代的以治沟骨干工程为主体的坝系建设阶段。2003年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作为水利部启动的三大“亮点”工程(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牧区水利建设、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之首,取得了大规模的进展。目前,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沟道治理的淤地坝工程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截至2019年11月统计,黄土高原地区共有淤地坝58776座,其中大型坝5905座、中型坝12169座、小型坝40702座,分别占淤地坝总数的10.05%、20.70%、69.25%(刘雅丽等,2020)。多沙区、多沙粗沙区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其淤地坝数量分别为52241座、40876座和12072座,各占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总数的88.88%、69.55%和20.54%(刘雅丽等,2020),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重点区域淤地坝数量统计见表1.1。近年来,黄土高原的治理使得黄河水沙情势发生剧烈变化(刘晓燕,2020;冯家豪等,2020;胡春宏等,2020a,2020b,2018;穆兴民等,2019;姚文艺,2019),其中潼关控制站年均输沙量由1919~1959年的16亿t减少至21世纪以来的2.45亿t/a(胡春宏等,2020b;刘晓燕,2020)。有研究表明,在当前的侵蚀环境下,很多坝控流域实际侵蚀模数小于设计值,淤地坝大量空置(刘立峰等,2015),坝内多有积水而无法利用,造成经济资源和水土资源的双重浪费。因此,应根据小流域侵蚀产沙现状适当缩减淤地坝建设规模,以免造成水土资源浪费,影响下游的用水安全(梁越等,2019);重点从“守底线、补短板、强监管”等方面着手,具体而言就是从加固除险、销号、转型、慎建四个方面开展工作(惠波等,2020;刘雅丽等,2020;曲婵等,2016);需要对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战略定位进行重新思考(陈祖煜等,2020),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2.2淤地坝减水、减沙、减蚀研究
1.淤地坝减水、减沙、减蚀效益定量分析
李靖等(1995)研究表明,淤地坝的减沙量占水土保持措施总减沙量的60%~70%。王宏等(1997)研究表明,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黄河河龙区间南片淤地坝年均减水效益分别为80.8%、67.6%、54.2%,年均减沙效益分别为83.5%、58.5%、66.4%。方学敏等(1998)研究表明,淤地坝不仅可以拦蓄径流泥沙,还可以降低沟道比降,抬高局部侵蚀基准面,降低重力侵蚀发生风险,控制沟道冲刷侵蚀。田永宏等(1999)研究表明,韭园沟流域淤地坝在1953~1997年年均减沙效益为78.6%,流域输沙模数减少了80.9%,基本实现了水沙不出沟,就地拦蓄消化。焦菊英等(2001)分析了皇甫川、窟野河、佳芦河、秃尾河和大理河5条黄河支流上的淤地坝和坝系减水减沙效益。冉大川等(2004)认为,河龙区间1970~1996年淤地坝减水减沙量分别占该流域水土保持措施减水减沙总量的59.3%和64.7%。付凌(2007)利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对淤地坝的减蚀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提高了坝地减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