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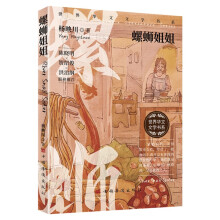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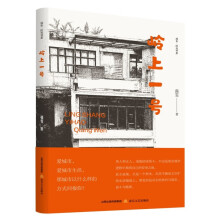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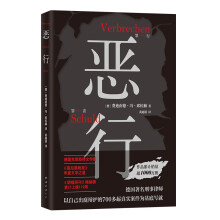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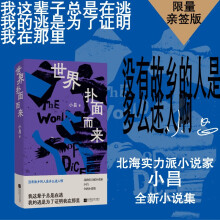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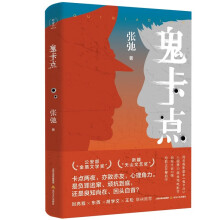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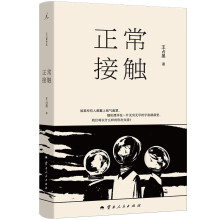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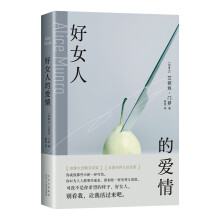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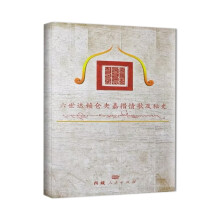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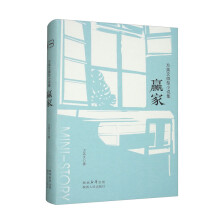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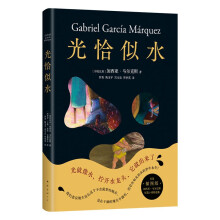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特别推荐
来颖燕:在博物馆的那一夜,发生了什么?
本期《小说界》的主题,来自“超现实主义画家当中最具文学气质”的勒内·马格里特的画作《一夜博物馆》,“画面上是博物馆的四格展示柜:一只手的模型,一个苹果,一块光滑的、形似山峰的石头,以及一幅图案对称的剪纸。这些明晰可辨的物象,被安静地放置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与所有在博物馆中出现的展品一样,它们被从原生的情境中剥离,而博物馆的时空让它们在一种新的叙事结构中重新获得意义。”
在来颖燕看来,“短篇小说在气质上正与博物馆中的展品趋近。因为篇幅所限,短篇小说注定要陷入指向寰宇的决心与言短意长的体裁限制的裂隙之中。于是,截取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或几个段落,并倾力打造它以赋予这有限的‘段落’以丰富的景深和丰厚的意蕴,成了短篇小说家们心心念念的事业。于是,许多成功的短篇,成功在作者明白要将什么纳入这有限的取景框中,又要将什么留在框外。”
她以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要不你们跳个舞?》为例,剖析了短篇小说可以如何面对生活的“段落”以及“段落”间的空白,并这样写道:“以简约和含蓄著称的卡佛一派的创作,最为明显地内化了短篇小说本身的特质——情节和结构至简甚至断裂,但依稀又能接续成故事,并因此显出某种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而这样亦步亦趋的‘接续’本身,也重新拷问了短篇小说的特质和意义。”
高鸣:想潜到水底去看一看
很多人最初知道导演高鸣,是因为他在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排骨》——这也是他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排骨是个卖碟的青年,一边文艺,一边现实;一边向往都市,一边无法离开农村;一边渴望爱情,一边又不能把握爱情……
趁着电影《回南天》在南京上映的机会,《小说界》杂志特意专访了高鸣。
《回南天》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的片名,用高鸣的话说,南方人听到这三个字“会有本能的体感”。回南天潮湿闷热,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笼罩着,渴望挣脱,但又挣脱不了。这也正是电影中四位主角的状态。高鸣用碎片化的方式将四个人下沉的情感拼贴在一起,“甚至只有负面情感,没有正面”。电影中两男两女四位主角,被他设计成花朵的四个不同状态:“从含苞到开放,再到开过了,然后凋谢。”
采访时,看到他随身背着一个很重的单肩包,包里有三本书——他有出门随身带书的习惯,“不然没有安全感”,每晚睡前看一点,才能安心睡去,“否则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缺点什么。”
“阅读对于导演来说太重要了!”高鸣认为阅读文学是对人类的灌溉,导演的视野、眼界,甚至创作方法都可能被文学所开拓。“阅读可以改变,可以温暖,可以软化,可以让人变得有温度,可以让人变得平和……”
那天,在他随身携带的书中,有一本是雷蒙德·卡佛的《新手》。高鸣很喜欢卡佛,他无所谓大家给卡佛贴怎样的标签,极简主义也好,肮脏现实主义也好,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觉得卡佛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困境,以及两性关系,“还包括对于情感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这些对他都特别有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