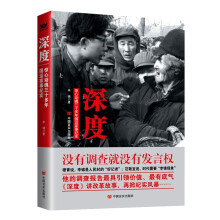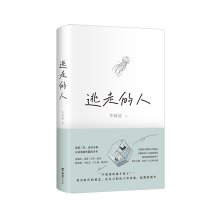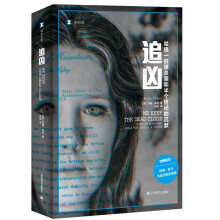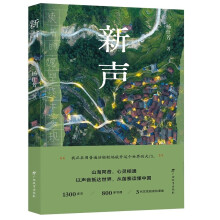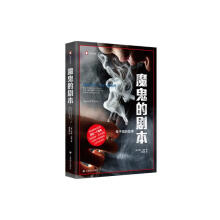踏访张家楼
一
越野车绕着曲折的U形海湾,驶过太平湾沿岸的楼群,从龙口附近开始爬山。这是海洋岛青龙山西南麓,水泥铺就的盘山路非常狭窄,从低海拔攀爬到山腰,已经弯转折叠了几次,Z形盘绕上升,如果不是因为密林的遮掩,从山下仰望,盘山路会像玉带一样缠绕着青龙山坡,每弯转一次,高度会上升几十米。此时,在凝固的绿涛间,玉带一样的水泥路时隐时现,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狭窄和险峻。
翻越北坡一处垭口,就进入岭后地界,继续弯来绕去,能透过茂密的植物看见被树丛切割的海面一闪又一闪,每闪一次,画面的帧幅就向前推移一次。车窗左侧,北坨子陡峭的山体在不断变换角度中拉长,由聚为一坨扭动成横陈海面的一列,像海洋岛北端拖着一条粗壮的尾巴,高高隆起,又陡然垂落。
目光从北坨子收回,落到我们左侧的坡下,那是原岭后大队驻地苇子沟屯。因山脉的延续和茂密林木与陡崖的遮挡,苇子沟的地形地貌,只能由想象去补充完成。
岭后曾经有两所小学,有一所就设在苇子沟。第一代女炮班班长张淑英在那里上学三年,终因从张家楼到苇子沟路途弯曲、沟岭太多、行走极其不便又没有同伴而辍学。
海洋岛北部偏隅之地向大海敞开,却几乎与外界隔绝。山路太难走,人们轻易不离屯。20多年前,我在退潮时登上过北坨子,采访几位救人者。他们是外来打工人员,冬天也在寒风呼啸的坨上坚守。我对此地的偏僻冷清有了切身体会,但对苇子沟没有印象,更没有到过今天必须前往的张家楼。
越野车弯弯绕绕行驶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右侧是林木覆盖的青龙山。我们蜿蜒盘旋在青龙山北麓,树木从上方搭起曲折的长廊,光的碎片从重重叠叠的枝叶间筛落,窄道外侧的绿色金属护栏光影斑驳。此时我对山的高度已经毫无概念,青龙山主峰海拔300多米,我们无疑是行进在山坡的低处。左侧崖下就是海,道路狭窄得对向来车时,一方要后退至山路的拐弯处靠边停下,另一方才能在险些剐蹭的情况下勉强驶过。
川蹄沟在哪儿?当年女炮班炮长王淑琴和引信手徐福英,就住在那个夹在崖缝里的海边小屯。
车速很快,川蹄沟可能已经路过了,而我却浑然不觉。
山路拐弯处,车轮碾压路沿,密林给险路增加了虚拟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看,北坨子狭长起伏的侧面轮廓,围出苇子沟一带静谧的海湾。黑色塑料浮力球、绿色玻璃浮力球和粉色胶囊状浮力桶分区排列,昂首站立,在曾经停泊演习军舰和支前渔船的海面布成田园的格局。这在60年前是不曾有过的光景,而曾经只有两户人家的川蹄沟依然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两户人家的房子建在哪里?是否还存有遗迹?此时已成谜。坐在行驶中的车里向下望去,陡坡与海衔接,更没发现从川蹄沟通往张家楼的山路,树林和茅草主宰着山表,满目皆是藤葛类植物近圆形的叶子,无法想象当年王淑琴和徐福英是怎样从此处海边的小山坳攀爬到对面的张家楼。那条不足一尺宽的陡峭山路,早已被岁月尘封,即使能够确认路径的大体位置,“路”的踪迹也早已荡然无存。有哲人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反过来,什么样的路,长久没有人走,路也就不再是路。从张家楼到川蹄沟的路没有了,青龙山上,还有当年的“路”吗?
李白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我看来,海洋岛东北隅的巉岩沟壑,攀爬难度甚于蜀道。
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