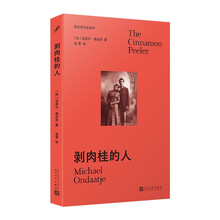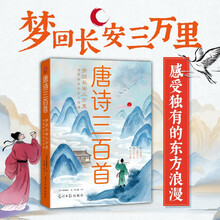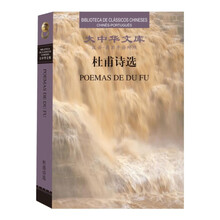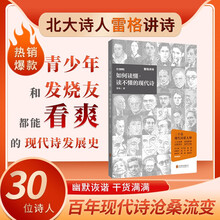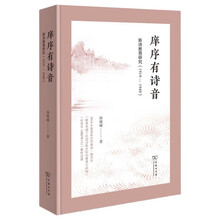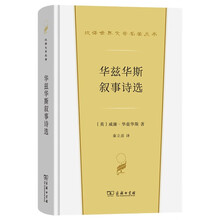第一回 虞舜帝梦托大任 安命公喜得麟儿
《道德经》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说的是这天下万事万物,都逃不开阴阳之演变。自然中,阳极生寒,冬去迎春,花开花谢,月圆月缺;人事中,盛极而衰,静极思动,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然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可看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唯有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方可得民安国泰、天地和谐!
说起大唐,无疑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伟大王朝,唐诗、唐文、唐楷、唐草、唐音、唐画、唐装,这些文化艺术,迄今为止,依然屹立于中华文化的巅峰,令中国人叹为观止、引以自豪;天可汗、辽阔版图、万国来朝的唐代辉煌,让海内外每个中国人梦绕魂牵、心生骄傲!而自宋朝以后,“唐”则为“中国”的代名词,为海外诸国所尊称,海外华侨将故土称为“唐山”,自称“唐人”,聚居的地方则为“唐人街”,也足以体现中国人对这昔日辉煌的大唐心存怀念和仰慕。
大哉,赫赫兮其有武业!伟哉,焕焕乎其有文章!然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巍巍大唐也逃不开阴阳规律之演变。唐朝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唐玄宗“开元盛世”后,国强民富,达至鼎盛巅峰。然而唐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六万大军征南诏而全军覆灭;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率领七万大军再次进攻南诏,又全军覆灭。两次败于西南边陲小国,不仅大唐在四夷眼里成了纸老虎,而且大唐天子在国内的尊严也不再,那些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的藩镇因此蠢蠢欲动。一年后的天宝十四年(755年),久怀异志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由此爆发。历经八年平灭之后,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由兴入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不见了,吞吐中西、睥睨天下的东方帝国威严不见了,天宝年间全国的五千万人口,经此乱之后,只剩下了一千多万。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战争的爆发,无疑带来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流血遍地、哀鸿遍野的悲惨,然而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却也是“有无相生、利害相随”的事情,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原文化的向南传播。东越、闽越、南越、长沙等自古以来远离中原王朝的蛮荒之地,因为中原士大夫的逃命南迁,于是带来了当今浙江、福建、两广、湖南等人文富庶之地的兴起。冲气以为和,使得中华文化得到大交流、大碰撞、大和合,有利于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均衡发展,从这点来看,这也是不幸之万幸了。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是诗人李白描写安史之乱的句子,继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后,安史之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潮,中原士族纷纷拖家带口,向南逃命。在这逃难的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彬的东京洛阳人,带着一妻一子,一路匆匆地往湖南方向赶去。
胡彬是个读书人,由于科举不第,因此也就一直在洛阳过着“晴耕雨读”的太平日子。其祖籍在安定郡,即今天的甘肃省镇原县,祖上曾经有多人做过大官,先祖胡伟绩还是贞观年间从三品的散骑常侍,可惜这几代下来,却沦落为平民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成为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焦点,当然也是兵灾最严重的地方。755年12月安禄山攻占洛阳,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757年10月唐军收复洛阳,759年9月叛军重新占领洛阳,762年10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相比前三次发生在洛阳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洛阳的老百姓可就更惨了,因为唐军这次收复洛阳,依靠了回纥军的帮助,而这回纥军进城后,在洛阳大肆烧杀抢掠,大火连绵数十日不灭。
胡彬住在洛阳郊区,前两天刚看完父亲胡泉的朋友杜甫写的“三吏”和“三别”,既感慨《新安吏》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兵士悲酸,又感慨《无家别》中“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的百姓流离之苦,没想到“海中月是天上月,眼前人变剧中人”,自己也面临兵火的到来。逃还是不逃?村里的人都走光了,看来是不得不逃!可儿子胡任旭才两岁,刚刚学会走路,这逃起来怎么走得动呢?而且要逃的话逃到哪里去呢?回安定故里吗?还是去长安投奔亲戚?何去何从,真乃两难之境,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真是度日如年!
一天夜里,他入睡后,隐隐约约来到了一个白云缭绕、奇山隐秀的地方,远处的山峰上有一块三分的石头,如三把利剑直插云霄,令人仰慕,他步履轻盈、心情愉悦地缓缓前行。走了不远,忽然看到路边有块碑,碑上隐约有“九嶷山”三个隶书大字,胡彬心想,这是不是到了舜帝驾崩的九嶷山了?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悦耳动听的音乐声,胡彬于是顺着声音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只见路边有个高台,高台上有一位白发银须的人在抚琴奏乐,琴声悠扬,宛如仙乐。那人见到他后,琴声戛然而止,胡彬凑近一看,见琴上有“虞舜帝五弦琴”的字样,而见那老翁,则是双目重瞳、慈眉善目。胡彬猛地一惊,双手作揖问道:“请问仙翁,您是虞舜帝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