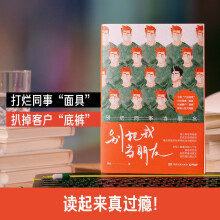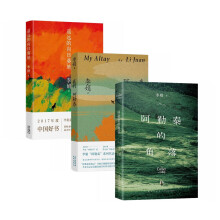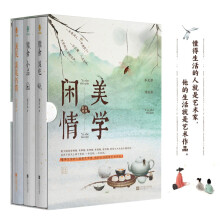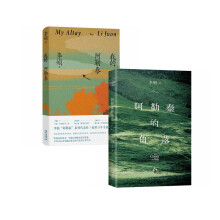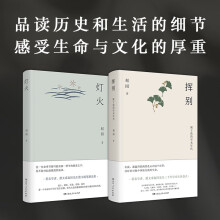此为赵令畴写给仲仪的一通信札,记录了他得到皇上赐茶的经历。唐代以后,饮茶之风逐渐盛行,茶叶也成为帝王赏赐臣下的重要物品之一,至唐中期,随着官焙茶院的贡茶制度建立,赐茶制度也就应运而生。赐茶制度既有岁时之赐,亦有因人因事而设的不时之赐。唐代关于赐茶的记录,多在谢茶表中。大臣得到皇帝赐茶之后,也有一套谢赐的规矩,尤其是大臣要作谢赐表,即作诗或作文章表示感谢,这也被称为“谢茶表”。
有宋一代,随着赐茶制度的完善以及茶在人们生活中所占地位的日益重要,名茶也成为统治者赐物名单中重要的物品之一,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宋史·礼志》记载:“中兴,仍旧制。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
赐茶在北宋已经有一套详细完备的制度了,讲究法制化和规范化,便于操作。蔡居厚《蔡宽夫诗话》载:“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这里详细规定了清明赐茶的来源、程序和范围,细致合理,可操作性强。《宣和北苑贡茶录》载:“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公主,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赐白乳。”由此可见,赐茶是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的,得到赐茶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同等级的官员得到不同等级的茶叶,获得赐茶是一种荣耀,正如梅尧臣《七宝茶》诗所云:“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
翻检古代历史笔记,赐茶之事,处处可见。
比如宴席赐茶。周密《南渡典仪》载:“车驾幸学,讲书官讲讫,御药传旨宣坐赐茶。凡驾出,仪卫有茶酒班殿侍两行,各三十一人。”可见,皇上出巡时还带上几十人的“茶酒班”。这是宴席赐茶之一种。宴席赐茶的另一种是皇帝亲自布茶,如蔡京《延福宫曲宴记》所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
再比如殿试赐茶。张舜民《画墁录》:“予元祜中详定殿试,是年分为制举考第,各蒙赐三饼,然亲知分遗,殆将不胜。”张舜民作为考官,分得三块茶饼后分予亲友,可见其对赐茶的看重,而分之不足也可见出所赐之茶的珍贵和量少。
还有一种,臣子在京外,皇帝会让人捎带茶叶以示慰问,如哲宗秘密向苏轼赐茶。王巩在《随手杂录》中记载:“中使至……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
皇帝向臣子赐茶,加深了君臣感情,而受茶之臣子,无不欢欣鼓舞,珍爱有加,或藏之秘箧,或分享友朋,或孝敬严慈,或品题自怡。周必大曾作《入直》诗表达感恩:“绿槐夹道集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王元之有《龙凤茶》诗云:“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烹处岂期商岭水,碾时空想建溪春。香于九碗芳兰气,圆似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王元之要将皇上赏赐供奉给双亲。欧阳修在为蔡襄的《茶录》所写的《龙茶录后序》中记载,有一次南郊大礼,致斋之夕,皇帝赐给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共八位大臣一饼小团龙茶,欧阳修也分得一小块,“……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得到赐茶后如获至宝之感与感激涕零之情。
如果说散落于各类典籍史册里的赐茶之事为我们研究赐茶历史提供了一份标本的话,那么,赵令畴的《赐茶帖》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溢于纸上的喜悦之情,那么遥远,又那么亲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