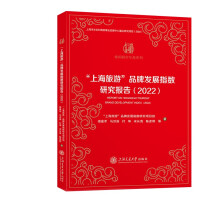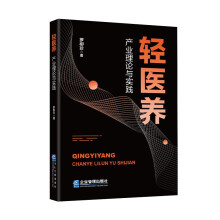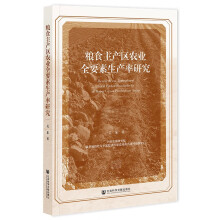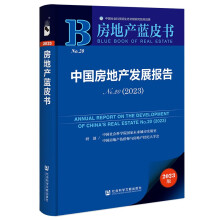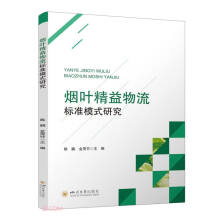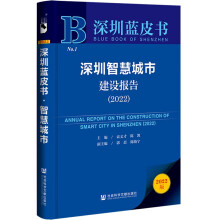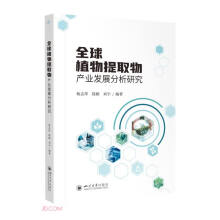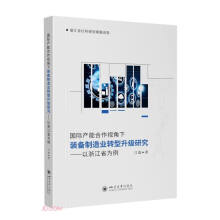第1章基本理论与总体研究概况
创意经济的核心要素是创意,而创意这种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本,更具有非均衡性的特征,极易在某些区域内集聚。集群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创意人才和创意产业的重要发展模式。从全球创意经济来看,以创意、文化、人才等要素为基础的创意集聚区随处可见,如美国奥斯丁的软件园区、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中国北京的798艺术区等。因此,从空间视域来探讨创意人才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当前创意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本章将从地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及创意经济学的理论方面进行回顾,以期为“空间视域下创意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1从产业区到“新”新经济地理学
创意产业集聚(creative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CIA)的理论渊源来自产业经济学、地理科学、传播学、区域创新学等众多学科,目前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创意产业研究理论成果。我们从产业集聚、区域创新、创意经济等方面对相关理论基础展开分析和讨论。
1.1.1产业区理论
产业集聚显现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很早就被人们捕捉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产业集聚理论。马歇尔(Marshall,1920)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是产业集聚理论的基石。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将专业化的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特定地区称为“产业区”,并把“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地方而获得的经济”称为“外部经济”。他认为外部经济、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并指出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是导致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马歇尔还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除了外部经济等自然禀赋的原因外,还包括宫廷奖掖的因素。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理论至今仍然是解释空间经济、城市经济、总部经济等的重要理论基础。不过,由于时代和个人局限性,马歇尔并没有详细阐述外部经济本身的源头。
1.1.2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韦伯(AlfredWeber)和胡佛(Edgar Malone Hoover)。1909年,韦伯在其《论工业区位》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并采用了等费用曲线分析工具,从运输成本与劳动成本两方面讨论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韦伯认为工厂规模的扩大,能给工厂带来收益,或者能为工厂节约成本,或者二者兼得。出于收益增加和成本节约两方面的考虑,工厂对其生产模式具有强烈的集聚愿望(Weber,1929)。相比马歇尔的分析,韦伯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视角,讨论了产业集聚效应及其本源,这无论是在研究视角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了明显的改进。不过,韦伯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制度、文化、历史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创意产业的集聚,其文化根植性和地方嵌入性更加明显。忽视社会制度、文化、历史因素来讨论产业集聚,很容易陷入单一分析视角,从而得到片面的研究结论。尽管后来胡佛在产业集聚理论上又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区位单位的*佳规模、公司的*佳规模及集聚体的*佳规模等概念,并把企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定义为某产业在特定地区在集聚体的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Hoover,1948;Hoover and Giarratani,1985),但是仍然没有走出古典经济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地理空间概念及制度因素等方面的“灰色”境地。
1.1.3新产业区理论
在福特制大批量生产方式的冲击下,马歇尔的产业区开始逐渐萎缩。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继马歇尔、韦伯、胡佛之后,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进展比较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意大利中北部的中小企业集聚区等“新产业区”的出现,以及几乎在同时期理论界波特和克鲁格曼对产业集聚的贡献,才改变了当时产业集聚理论在经济学中处于边缘研究的尴尬状态,也使得产业集聚研究再次回到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同时引发了各学科研究产业集聚的一个热潮(张华和梁进社,2007)。
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理论有两个学派,即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新产业区学派的代表学者有Bagnasco、Piore和Sabel等。Bagnasco(1977)提出了“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的概念;Piore和Sabel(2014)的研究指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对新产业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新产业区学派提出了在产业集聚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本地网络(local network)和根植性(embeddedness)两个重要的因素,这也使得关于产业区的研究延伸到了地理空间的历史文化分析中,不过,由于没有充分讨论区域学习与创新等因素,对产业集聚的作用略显不足。
新产业空间学派的代表学者有Scott(1988,1996)、Storper等(Storper,1989;Storper and Harrison,1991)、Harrison(1992),该学派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交易成本理论来探讨空间地理区域的产业集聚机制。新产业空间学派指出,随着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加,距离较远的企业交易,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成本。因此,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和费用,企业集聚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不过,由于局限于运用交易成本的分析工具,新产业空间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产业集聚区的知识创造与知识空间扩散等因素的分析(王洁,2007)。
1.1.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代表学者有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Krugman,1991;Fujita and Krugman,1995;Fujitaetal.,2001)。克鲁格曼(Krugman,1991)认为空间配置和市场结构对产业格局与贸易具有重要影响,并摆脱了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束缚,构建了劳动要素流动(footloose labor,FL)模型,讨论了在企业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及生产要素流动的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业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由于远距离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如交通成本、通信成本,会阻碍要素回报递增作用的发挥,因此,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现象只在集聚的有限空间领域内才能显现,所以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就可以用于解释现实中可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形成与发展(Krugman,1992;Fujita and Krugman,1995;Fujitaetal.,2001)。关于金融外部性的分析,在Baldwin(1999)的资本要素流动(footloose capital,FC)模型、Forslid和Ottaviano(2003)的企业家要素流动(footloose entrepreneur,FE)模型等研究中,也得到了一定延伸。
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规模的外部经济与运输成本的融合是解释区域产业集中化和形成区域“中心”与“外围”状态的关键(宋德勇和胡宝珠,2005)。不过,克鲁格曼在其研究中较少提及知识溢出和其他类型的外部经济对集聚的作用,这也不失为新经济地理学的遗憾。当然,克鲁格曼也曾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主题选择沉默,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视这种集聚力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完美的关于知识溢出的微观经济模型,也正因为此,他才转而发展基于关联要素的空间经济学的微观模型(梁琦,2005)。
克鲁格曼所忽视的对技术外部性的研究,在Glaeser等(1992)、Audretsch和Feldman(1999)、梁琦(2009)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拓展。Glaeser等(1992)总结了两种技术外部性,即MAR外部性(即专业化和垄断更有利于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和Jacobs(1970)外部性(即多样化和竞争更有利于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并拿出证据支持多样化外部性,但他本人并不认为专业化外部性不重要。Audretsch和Feldman(1999)的证据表明,多样化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创新,地方竞争比地方垄断更有利于技术发明;deLucio等(2002)的证据表明,专业化外部性显著,而多样化外部性不显著。总而言之,由于选择的样本不同,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并不能否认产业集聚的技术扩散及知识外溢效应的客观存在。
1.1.5“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近年来,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开始兴起,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引入,放松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同质性假定,使其更加契合现实中企业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对企业进出口行为和区位选择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企业区位选择方面,Baldwin和Okubo(2005)将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垄断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分析企业的转移行为。他们认为企业异质性的存在对企业空间分布具有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选择效应是指由于高效率企业往往都位于大市场和中心区域,从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也能应对来自大市场或中心区域的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大市场和中心区域能够吸引高效率的企业迁入,同时,高效率的企业也更加倾向迁移至大市场和中心区域。分类效应是指随着高效率企业迁移至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市场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而处于中心区域的低效率企业将被迫选择从中心区域迁出至小市场和外围地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企业选址的变化并不是随机的。换言之,在地理空间范围内*终形成企业的“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在企业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此后,以Okubo(2010)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发展企业异质性理论。Okubo(2010)指出低效率企业更加倾向集聚,而高效率企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更加倾向分散化分布。和Sφrensen((2012)将技术进一步融入Melitz模型中,研究发现企业区位选择是一个动态过程,高效率的企业比低效率和年轻的企业能够生存得更久,同时,贸易自由化会使得低效率企业*先从国外市场退出,甚至可能会丢失国内市场,*终从国内市场退出。Venables(2011)探讨了城市异质性劳动者与企业的匹配机制,认为城市能够为不同类别劳动者和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匹配机制,从而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程度,从而促进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它的具体实现机制在于,在城市落户的高效率企业能够吸引高技能的劳动者,从而促进企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终助推城市生产效率提高。
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提出弥补了新经济地理学无法处理集聚经济理论和企业分布差异之间的鸿沟,对企业选择效应与分类效应、集聚经济外部性、城市经济外部性等理论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李晓萍和江飞涛(2011)指出企业异质性理论主要从三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①微观异质性的假设对新经济地理模型的构建及集聚经济的测度带来新的研究视角(Baldwin and Okubo,2005;季书涵和朱英明,2017);②企业异质性与劳动者异质性为重新思考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带来新视角(Han and Li,2017;陶长琪等,2019);③企业异质性或动能异质性对经济空间结构与布局的研究具有新启发(范剑勇和邵挺,2011)。总之,企业异质性理论不仅推动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向以企业异质性为假设前提的“新”新贸易理论转变,还引发学者借助异质性理论对新经济地理学展开拓展分析,特别是对企业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讨论,该理论成果也被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随着对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选择效应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关于多个产业集聚区协同共生的讨论频繁见于区域科学领域的主流杂志。为研究多个产业集聚区协同共生的原因机制,Ellison等(2010)提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概念,并从经验分析层面指出产业协同集聚有利于解释空间经济差异。此后,出现了大量关于相关产业协同集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