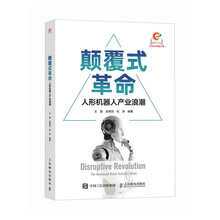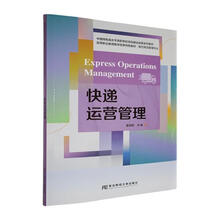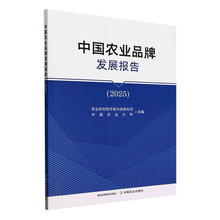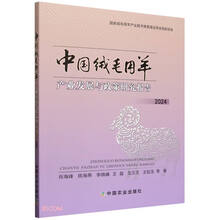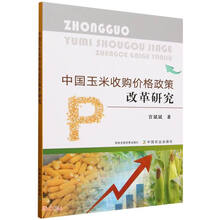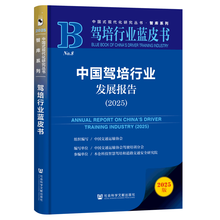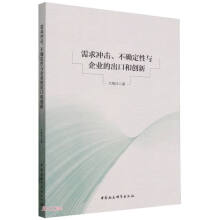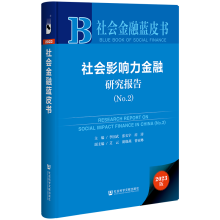第1章 技术经济安全评估——一个新的学科方向
随着时代演进,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包括了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军事安全到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各类安全。随着科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渗透日益广泛,技术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本章从新学科方向视角,提出为什么要开展技术经济安全评估,分析技术经济安全评估的意义及其研究现状。
1.1 国家安全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1.1.1 国家安全的内涵日益丰富
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也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演进,安全问题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产安全、社会安全、人身安全等。国家安全与国家相伴而生。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问题。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美国政治专栏作家Lippmann于1943年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U.S. Foreign Policy : Shield of the Republic )中提出,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牺牲其合法利益就可以避免战争,而一旦国家的合法利益面临挑战,它能够借助战争保护其合法利益。1947年美国率先制定了《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将国家安全定义为“保持美国作为一个基本制度和价值不受损害的自由国家”(肖文韬,2001)。冷战结束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集中在领土不被侵犯,强调政治和军事上的安全。随着国际形势变化,经济安全逐渐从国家安全的边缘走向核心。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中东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意识到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980年《布伦特报告》(The Brandt Report)提出非传统安全,呼吁各国使用非传统方法看待安全问题(朱锋,2004)。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将军事、领土、经济、政治、粮食、能源等领域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各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大幅降低,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转向经济、环境、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虽然传统的军事安全仍是保障主权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国家安全涉及的要素不断扩展,特别是以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重要。
美国于1991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安全不仅涉及美国自身的安全问题,还包括全球和各地区的安全问题。该报告重申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2009年,俄罗斯在《2020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国家安全涵盖内政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学安全、教育安全、国际安全、宗教安全、信息安全、军事安全、国防工业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将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安全首位,文件强调“国家安全状况直接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潜力”,通过经济增长确保国家安全,要集中资源发展国家创新系统,投资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增长(张晶,2010)。2003年,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索拉纳在塞萨洛尼基欧盟首脑会议上,提交了欧盟首份安全战略报告——《欧洲安全战略》。该报告重新界定了安全威胁的定义,对恐怖主义、国家治理失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喻锋,2005)。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世界范围内经济低迷、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我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国家安全上升到新的高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明确定义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并将每年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国家安全体系进一步做出部署,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21年1月13日,教育部将“国家安全学”列为一级学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断深入,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保障国家安全的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安全体系日益健全,提升国家安全的措施不断完善。
1.1.2 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济安全在冷战后期才受到重视,但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5~17世纪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外来产品将会挤占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影响本国新兴产业成长和就业(李孟刚,2015)。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经济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基于当时欧洲大陆欧洲大陆是欧洲的主体大陆,明确地排除岛屿。特别在英式英语中,欧洲大陆的定义上排除英国、马恩岛、海峡群岛、爱尔兰共和国、冰岛、丹麦(日德兰半岛除外,属于欧洲大陆,但首都哥本哈根位于岛上)。国家与英国工商业水平存在差距的现实,如果进行自由贸易将会使欧洲大陆国家转变为英国经济的附庸,并且经济差距会越来越大,*终将导致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汉密尔顿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将会沦为当时欧洲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产品市场,并主张采取禁止制造业原料的出口、关税保护及禁止进口竞争对手工业制成品等措施。这些经济安全的思想从着眼于当前经济利益转向发展安全,一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对国家财富积累、国家独立与国家安全更加重要,而产业技术水平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93年,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罗姆在《对国家安全的重新界定》一书中指出,为了确保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美国除了须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还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深层的意义上讲,这是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也是国家强盛的深厚基础。各国普遍意识到长期优势和竞争力来源于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研发和获取能力(黄琪轩,2011)。
随着时代演进,经济安全的关注重点从产业安全转向资源安全再转向财政金融安全。早期的重商主义认为自由贸易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领域,涉及产业安全。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自由贸易一直是发达国家倡导的经济准则,而20世纪70年代,这一准则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石油危机严重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使其意识到资源安全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因而经济安全研究的重心也转向如何保证一国资源安全,即如何保证战略资源供给的持续性(Yergin,2006)。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将经济安全的研究焦点拉向了金融安全(江涌,2009)。
我国学者对经济安全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有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安全的重要部分——“粮食安全”问题和外资进入后的“产业安全”问题。例如,厉为民(1986,1987)对粮食安全的概念、影响因素、安全储备水平、保障措施等进行了研究探讨;洪银兴和刘欣华(1992)、伍海华(1993)研究了利用外资的安全规模。童志军(1997)、王晓蓉(1996)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东道国某些重要企业或产业被控制,同时造成东道国在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威胁东道国产业安全。1994年,赵英出版了系统研究经济安全的著作《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国内众多经济安全研究集中于金融安全领域,学者们从解读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总结启示教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如成思危(1999)主编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等。进入21世纪,一些专门开展经济安全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0年6月成立了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设立了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们围绕经济安全的定义、理论原理、方法论、监测模型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如《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分析方法》《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年度报告: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展望报告(2018—2019)》等,这些研究使中国在经济安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1.1.3 科技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要素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广泛渗透,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军事领域,国家军事技术水平已成为国防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在政治领域,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公司和群体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在经济领域,科技进步不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还能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强化国家的竞争优势;在社会领域,科技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肯尼迪(1988)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探讨了大国兴替历史,揭示了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逻辑,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盛的原因是经济和科技水平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衰落在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动荡和冲突就在兴起—强盛—衰落的历史演进中轮回交替。Buzan和Hansen(2009)将技术作为驱动安全研究的五种动力之一,认为技术带来的影响使经济能力比军事能力更加重要,信息技术、网络发展与能源安全应受到重视。
从世界科技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看,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18世纪,以蒸汽机、纺织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推动了纺织、钢铁、煤炭、运输的兴起。高峰时期,英国的金属制品、棉织品、铁产量约占世界一半,煤产量约占世界2/3,其他如造船业、铁路修筑等居世界首位,对外贸易占全球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2019)。英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相对份额从1750年的1.9%跃升至1860年的19.9%,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德国等国家出现了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子、化学、汽车、造船、航空等一大批技术密集型产业兴起,人类从机械化时代迈入电气化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国、美国取代英国、法国成为新的世界强国。1870~1913年,德国和美国增长的贸易额分别是英国的1.8倍和1.6倍,英国贸易霸主地位逐步动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2019)。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发明为主要标志,催生出核工业、半导体工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