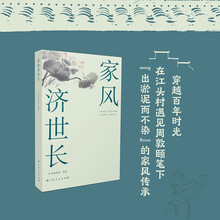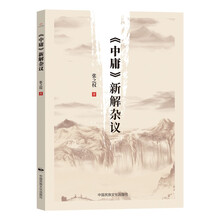第一章按朱熹的说法,是《中庸》全文的纲领,也就是中心思想。这章的核心是一个“道”字,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讲什么叫做道。第二个层次是讲如何修道。第三个层次是讲怎样才算是得道。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法家或佛家都讲“道”,都讲如何修道,怎样才算得道。三教九流各有各的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嘛。那么儒家的道是什么呢?儒家主张如何来修这个道呢? 儒家又是怎么去检验得道气象,怎样才算是得道,什么样的人叫做得道呢?
先看第一段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天”不是指天空的天,而是天然、自然的意思,指不是人类的力量能够改变的东西。《论语》中“吾谁欺?欺天乎?”(《子罕》)和“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的“天”;《孟子?万章》中“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的“天”,指的都是这个天。它与佛教的三十三天不同,与道教的最高之神—天皇大帝、昊天大帝的“天”也不同。它与天主教的天有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都是讲唯一的、至尊无上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天主教的天是宗教的;儒家的天是哲学的,是讲一种不为人类左右的自然力量,是一种哲学范畴,相当于西方哲学里讲的宇宙本体。什么叫“莫之为而为者”?“为者”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存在不是人类可以“为之”,可以摆布的。儒家把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本源叫做“天”。这个“天”相当于《易经》里的“无极”和佛经里的“如来藏”。
“天命”不是《西游记》里玉皇大帝下的命令,是指“天”这个本体的起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然规律。古人常说:天命不可违。你非要说“人定胜天”。那么天就会惩罚你,报复你。春夏秋冬,夏暑冬寒,这是天命,是自然规律。你非要冬暖夏凉,发明空调机,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结果臭氧层就被破坏了,造成地球“温室效应”,引起全球气候反常。自然规律只可以发现,不可违背的。这个“天命”,或叫做自然规律的东西,儒家把它叫做“性”。换言之,性是天生的、自然而然存在的,不是人造的。因此,有时候也叫做“自性”。在英文里“性”翻译成nature, 和自然是同一个单词。按照儒家的说法,天的自性也就是万物的自性、人的自性。“天命”落实到人,人性也和物性一样,和自然界各种现象、各种事物的性质一样,是自然禀赋,不是父母教的,也不是学校教的。我刚才讲到1993年在湖北郭店战国楚墓发现的竹简。郭店楚简上面就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说法。两句话合起来就解释了“天命之谓性”。你有了这条命就有了这个性,你的自性是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命哪里来的?命自天降,生命的来源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讲的是一般的人性,而不是张三李四的个性。
自然赋予的人性,人生下来的本性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染的,是善良的。随著年纪越来越大,受到外界影响,社会经验越多,离开他的本性就越远,个性就出来了。贪欲啊,说谎啊,行贿啊,拍马屁啊,什么都出来了。现在一岁多的小孩就开始懂得拍马屁了,为了要吃糖去讨好大人,慢慢都学会了。这种说法和佛教是相通的。儒家和佛教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同的说法。禅宗六祖慧能开悟时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楞严经》讲:“妙觉明心,清净本然。”人心生下来是清净自然的。这个“心”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儒家讲性命,佛家叫佛心。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佛心在那里。性和心是一回事。“性”字是一个形声字,左面是“心”字,是字义;右边“生”字是它的读音部分。你会说这个“生”字读xing,不读sheng啊。那你就要懂古音韵学。现在的普通话,英文译成mandarin,“满大人”的音译,是最初满洲人讲的汉话。古代的读音完全不是这样的。唐韵就是念“seng”,和“生”的古音一样。这可以从现在的广东话里得到印证。很多古音保留在现在的广东话和福建话当中。用普通话去读唐诗,很多不押韵。因为不押韵,所以难背诵,但用古音读的话,都是押韵的。用广东话读的时候就跟普通话读出来的完全不同。从“性”字的构造,我们知道性就是心,心就是性;人性就是人心。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即心即性”,心性一致,比较符合早期儒家思想。至于宋代程朱理学认为心和性是不同的,那是他们的发挥。至于为什么他们讲心性不同,而陆王心学要讲即心即性?这里就不展开了。
明白了“天”、“天命”、“性”这一系列范畴和“天命之谓性”,再来看“率性之谓道”就容易多了。这句话的关键词是“率”字。“率”是“循”的意思,遵循的循。率性就是循其性,顺应宇宙万物和人的自性。换句话说,顺应自然本性就是“道”。西方哲学强调征服自然,中国哲学强调顺应自然。汉语“道”的解释也很多,本意是道路途径,由途径延伸到方法,方法也叫道。比如“求学之道”,就是指求学的方法。方法相对稳定之后就成了原则,道也可以解释为原则。比如“商道”,做生意的原则;“武士道”,做武士的原则。但这里的“道”则是一个哲学范畴,指事物的根本,原则的原则,最高的原则。这个道和作为本体的天是一体两面的。没有天这个本体,也就无所谓道。天的起用就是道。率性就是道,遵循天命去做,顺应自性,就叫做道。因此,道和天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的率性,是任性,是随心所欲。人们常常会说:“这个人很率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庸》里的“率性”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叫做道。这就大错特错了。有人问:“君子率性谓之道”,和“小人任性所为,随心所欲”,这两者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君子遵循的是人性,人类的本性。小人任性而为的“性”是他的个性,被污染了的人性。前面那个本性是一种没有妄念、没有欲望,本来自得的。后面讲的性,是你生出来、长大后,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有了妄念,有了欲望,形成的个性。
“率性之谓道”,为什么《中庸》要这么讲?这就涉及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告子上》)人性本来善这个道理,就像水永远往低处流一样,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一派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
”,认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才能“化性起偽”,成为好人。由荀子思想发展出后期的法家。他的两个学生,一个韩非子,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另一个李斯,实践法家理论,实行严刑酷法,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专制集权的国家。后来也因为严刑峻法导致陈胜吴广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可以说,成也李斯,败也李斯。
《中庸》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当然是主张性善论的。“天命谓之性”,人的自然禀赋,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会出坏人,会有人干坏事呢?后天的环境影响使然。这种后天的影响造成人的个性被扭曲。用佛教的话,就是良善之心被污染了。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跟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下的,或者跟一百年前生下的婴儿,有什么不同呢 ?在人性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后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环境变了,比如一百年前没电视,现在有了电视。小孩子很小就会看电视了,受到了电视的很多影响。时代不一样,地域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社会经历不一样,都会造成不一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后天的。比如一个老太太在路上摔倒了,你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把她搀扶起来。这就是你的本性,良善之性。但这个念头刚闪过,马上想到她会不会是碰瓷,想敲诈我一下,给我添麻烦啊?我还是不要管闲事吧。这后面的念头,就是环境使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不会这么想,因为那时候没见过“碰瓷”的,也没有南京法院的那个判决。现在环境变了,想法就不一样。这些想法都是后天的。人的第一闪念,我要去搀扶她,这是人性的本来面目。接下来可能有一百个理由叫你不要去做。难的是对付这后面的一百个念头。如果你能够不考虑后面的那些因素,遵循着自己的第一个念头,顺应自己的良善之心去做,那就叫做“道”。所以道说来也没那么复杂,不外乎順應著人人本身具有的良善天性,不加上后天的心思,不加上后天的染污,直道而行。
后面这一句“修道之谓教”,人天生的心性是相同的,但生下来后,成长过程中,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各种影响,会让人心变得龌蹉了,歪了,坏了,不能“率性”了。这就是古人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怎么办呢?圣人教诲天下人要修行,要修道。这里的“修”就是修正、纠正。纠正你自己的行为,回到你那个良善的本性,回到“率性”这个道上来,遵照你的本性去做事。修道并不是要你增加什么新知识。我以前经常讲,佛法是减法。修道是做减法,把很多错误的观念去除掉,把蒙在你心灵上的灰尘扫干净,恢复你的本来面貌。如果你不去行,不去悟,懂得再多的理论也没有用。圣人告诉你如何修道的方法就叫做“教”。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和佛家是很接近的。有很多高僧解读《中庸》。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中庸》跟佛家的很多道理完全一样。南宋禅师大慧宗杲就讲过:“天命之谓性”,就是佛教讲的“清净法身”。佛经上说,法身不生不滅,無相無不相,是佛及眾生各自皆有的法體。因此,这个法身也就是人的天性、本性、自性,都是一个意思。“率性之谓道,便是圆满报身”。報身是指修行圆满,證得了絕對真理,獲得了佛智慧的色身。如果你能遵循天生的良善本性,就符合了儒家的道,就算圆满了。这就相当于佛教的报身。“修道之谓教,便是千百亿化身。”化身也叫应身,指佛為度化眾生而在世間出现的各种形象。“教”就是得道的人再去弘道,把自己的良善之心扩展开去,改变整个社会。这就像大乘佛教提倡的普度众生。佛的法身变成了千百亿化身去弘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