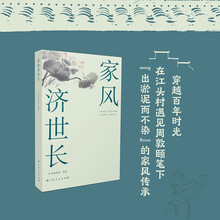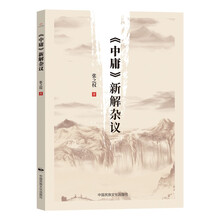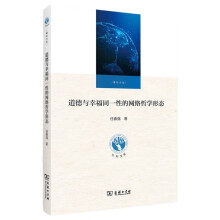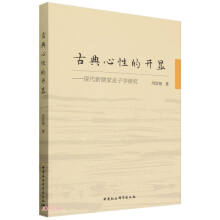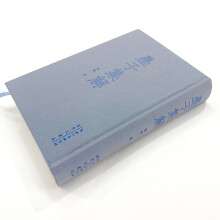《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其晚年的《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遂可以视为易学体系的定论。熊氏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凸显了易学的重要性,以致归宗于易,为其整合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寻求到了坚实的可靠性。熊氏从儒学的角度考证了《周易》经传的作者、年代、地位、思想,并从现代性的话题人手,重写易学史。熊氏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之正统派即儒家”,而易为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他进而引入西方哲学、科学、宗教的视角,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于易学为首的经学中勾勒彰显出科学、民主、平等的内涵。他所构筑的新易学,既不舍传统的精神,希望以易学所表彰的心性修养功夫补充西学的不足,同时又可以解决科学、民主等现代社会主流话语的问题,融入现代价值理念。
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建构形而上的本体论,他们认为对无限本体的追求是人之天性所在。在西学影响下,熊氏也致力于以本体论、宇宙论的方式说明易学的问题。雅斯贝尔斯说:“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海德格尔也以领悟此在之意义作为本体论的根本问题。本体论或形上学的实质,在现代哲学看来亦不只是对宇宙之本源或本体做一追问,以解决宇宙图式构架的问题,做一种近于科学的研究,而是试图要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当人面对世间的偶然与生命的无常,人生之渺小于此无限宇宙的意义不能不成为人所要追寻的问题。人对存在意义的思考,正是基于人生的有限性基础。本体论就是解决这样一种有限达到无限何以可能的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