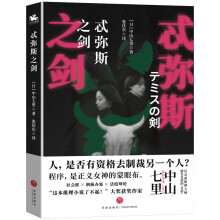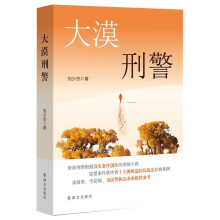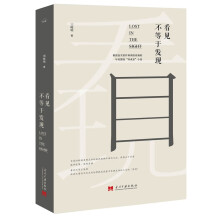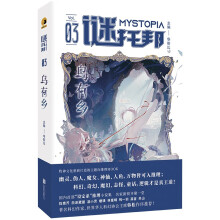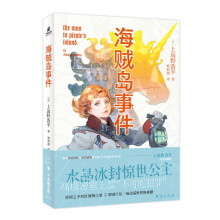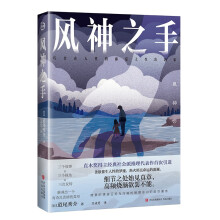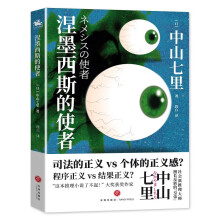清晨,下着小雪,天灰白灰白的。十一月的华北,天本就亮得晚,北风又起,四周静得有些疹人。镇子中央广场前,疾步走过两个挑夫,后面紧跟着一名壮汉。
“哟!这就挂上了?”
“是啊,这女子就是不吃劝,一宿工夫,就没了。”
“别说了,赶紧走。”壮汉轻斥一声,仰头看了下牌楼。在他的目光尽头,广场的牌坊上一具女尸,正随风摇摆。
天亮透了,镇中央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此时人声鼎沸。
人群中央,一人拿着一张纸高声念道:“当天下午死,赔率一赔五百,无人下注;当晚死,一赔三百,仅黄三文下注三文,得九百文,其他人全没押中。”
“干他娘的!”
“黄三文?”那人又喊道,“黄三文是谁?来了没有?”
“来了!我来了!让一让,让一让……”一位四十来岁、中等个子的中年男人,一瘸一拐地费力拨开拥挤的人群,向那人走去,他——就是黄三文。
众人目光不约而同扫向黄三文,这黄三文上身着浅蓝色粗布短棉袄,已经有些发白了,黑色粗布棉裤,脚上却穿着一双旧皮毛靴,这打扮真够怪异的。黄三文拿过钱,笑着拍了拍那人的肩,说:“侯四爷,要不接着赌?”
侯四爷愣道:“还有什么好赌的啊?”
“喏,就赌那个。”黄三文扭头指了指城墙上贴的一告示。
众人一看,通告墙上贴着一张新告示:常山镇征警察事务所所长一名,活人即可,月俸一百大洋。意者直接前往镇公所领取上任文书。
“赌什么啊?”侯四爷有些不耐烦了。
黄三文满脸菊花般地笑着,又说:“赌什么时候有人上任啊。”
侯四略一犹豫,旋即道:“好,就赌这个。今天上任一赔一千,明天上任一赔八百,三天之内上任一赔六百……”
“九百文,外加三文,我押今天有人上任。”黄三文把手上的钱拍在侯四手中,又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三文钱叠了上去:“我押三个大洋,赌一个月。”“三百文押半个月。”
人群炸了锅,黄三文趁乱抽身出来,蹒跚着走向镇公所。
镇公所在常山镇东南面,三年前才建好的。常山镇,位于华北地区,镇上居民有万余人,四周散居的农户也有上万人。虽说常山镇不小,但地理位置太偏,不仅外人极少知道,连历史记载也几乎没有。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对军队进行了改制,几年前一名叫赵建荣的队官手持清政府文书,带着几十号人接管了常山镇,驻扎在东南面。
时值清朝末年,国内局势动荡,这偏远之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虽小,但山贼劫匪逐渐猖獗。原镇长是地方绅士推荐出来的,镇长带着当时还称为巡警局的全体人员去剿匪,结果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地方绅士见赵建荣握有兵权,连忙请他出任镇长。赵建荣问这些乡绅们出资在驻军地里面修建了新的镇公所。
两名手持铳枪的守卫把黄三文拦了下来,他伸手便将枪拨开,说:“我是来应征的。”
守卫见他是一瘸子,有些不齿,其中一人轻慢地说:“走吧,跟我来。”
守卫把黄三文带到一座火砖封砌的小房子里,示意他站在屋里等,然后反身走了。这房子很小,正中间摆着一张极其普通的木头雕花大案台,案台上散乱着一些公文,案台后面是一把二流木匠做的雕花椅子。窗棂、大门虽然也有雕花,却一点也不精致。
这不会就是镇公所吧?黄三文纳闷起来。
片刻,走进来一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常山镇镇长赵建荣。
黄三文暗暗打量着赵建荣,这人高个头,相当魁梧。要说到赵建荣的装束,黄三文心里直发笑。这赵建荣北方人常见的国字脸,五官端正,本是魅力的男性典型,一副金丝小圆眼镜配在这脸上,给人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再看他身穿蓝灰色立领,对襟上衣,蓝灰色裤子,衣裤有明黄色的团蟒图案,这是清朝末年新式陆军军服。腰间挎着佩剑,脚蹬锃亮的马靴,头上戴的是现今北洋军大盘军帽。他这是清朝陆军军服和北洋新军服的混穿。最可笑的是帽子下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赵建荣目不斜视,从黄三文身边走过,坐到了案台后的椅子上,语速缓慢地说:“委任书在这里,章已经盖好了,你填上自己的名字吧。”
“不着急,你得先答应我三个条件,”黄三文毫不停顿,说道,“第一个条件:月俸翻倍,二百个大洋,现场给钱,然后上任;第二你要再给我配三个人,每人月俸三十个大洋,由我代发,也要现给;第三给我弄个住处。”
什么?赵建荣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右手已经按在剑柄上了,对这个不起眼之人,他真想杀之而后快。
黄三文面无惧色,原地站定,接着又说:“昨天上任的女所长还挂在广场上呢,这种送命的活谁会来做呢?我提的条件已经很少了。”
赵建荣自然知道黄三文说的是实话,上任镇长和整个巡警局的人失踪以后,巡警局顺应政局改称警察事务所,但历任所长、警员没一个活过半年的,前期的所长还都是练家子多。警员早就没人敢做了,所长偶尔能招来一个,但一个比一个死得快。上上一任所长半年前上岗一个月就被斩首,他赵建荣随即就发出了招所长的告示,半年来无人问津。无奈之下,他把月俸从十个大洋提到二十大洋,没人;提到三十大洋,没人;四十大洋,还是没人。直到昨天提到了八十大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