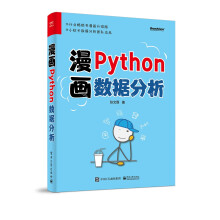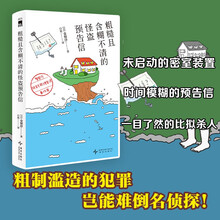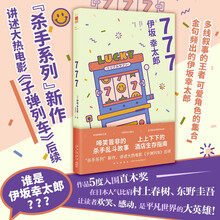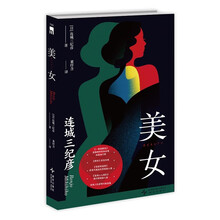自然的有形的素材必定会腐朽。四季变换是如此的分明,走向死亡的白木映照了人的生命,这其中有日本人的情念。悲凉、无常,万物如水泡,走向衰微。所以,日本人借用木的特性,将自己衰死的身姿移至白木衰死时的凄绝美。知道一日的虚无与无常,然后抓住充实的生的瞬间,将一日的生命结晶化。活在一日中,活在日常性中,将如何创造?生存的意义也就出来了。
而木匠被赋予的课题是,阅读一片片不同木材的传奇表情,将自身放置于木材中,思考生存的场所与可能性。砍伐一根圆木,由于砍伐部位的不同,其木理也是不同的,每根圆木都带有鲜明的个性和故事。切割那粗壮的富有表情的圆木,将其裁剪成木片,从中发现和创造出符合心情的形状各异的实体道具。将原木具体化、艺术化,需要木匠眼心脑手并用。而作为专业的木匠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辨别木材的慧眼,要有平和之心、同情之心和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木肌美与清净感、枯淡美与神圣感,才能在木匠的精工琢磨下得以实现。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没有资格对良质木材为所欲为。所以,日本木匠的宿命就是面对被砍伐的树木,如何燃烧起自己的情念。你看,这是多么纤细的感受性,独特的木文化由此生成。在日本人眼中,白木是一首诗。
日本的木工工具也是种类繁多,如锯子、刨子、凿子、锥子、棰子、斧头等。工具是木匠手与体的延长线,是木匠技术和技能的形。日本人在自己喜欢的风土中,与木共生。所以,日本有许多木物。如筷子、木桶、酒樽、柱子、建具、家具、梳子、木屐等。这些生活用具的制造者(木匠),也相继在各地诞生。各种木工技术也应运而生。如曲物、指物、细工、雕物、挽物、象嵌、寄木、大工等。随着技术的分化,制造这些品物的曲物师,指物师、木雕师、建具屋、细物师、木纹师、旋工师等也相继诞生。无疑,这些物品和技术,都带有了日本特色。
青森的丝柏、秋田的杉木、木曾的桧木是日本三大美林,非常有名。这其中,日本人将木曾的桧称之为“本木”,意思是最高境界的“真木”。桧木材质致密,木纹通直,色洁白,清净神圣,对防虫害,防雨水湿气都有很强的功用,故被称之为木中之王。日本木文化学者小原二郎在《支撑法隆寺的木>(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0年)中说,木有不可思议的木味。但这其中的木味,是依据树种的不同,产地的不同而不同。这与人类社会中民族不同,乡土不同而习俗和性格也就不同是一样的。桧是对日本人肌肤最为适合的木,但这也是在很长的历史中形成的。飞鸟时代的木工们已经知道桧木的心情,能够很好地使用它就是一个说明。三重县伊势神宫就是用桧木建造的,生粹的木造建筑至今放着异彩。高野山桧、吉野桧、尾鹫桧虽然也属良质,但不能称之为“本木”。日本人赋予木曾桧以最高地位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木文化中神圣和清净的思想。
(十)弥勒菩萨木雕用材的风波
京都有座广隆寺,广隆寺内有两尊弥勒菩萨雕像:一尊叫微笑的弥勒,一尊叫哭泣的弥勒。这两尊弥勒像用不同的表情,演绎着佛教世界的幸福与苦恼。这两尊弥勒像在以前是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是“日本雕刻”还是从“朝鲜半岛传来”的两种说法上。
认为是朝鲜半岛传来的依据是,哭泣的弥勒表现出幼稚的雕刻方法,这是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原像,根据这个模样,日本用红松木再雕刻,诞生了东洋的弥勒维纳斯——美丽的微笑弥勒。
认为是日本雕刻的依据是,《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623年)记载:从新罗有一尊佛像献上,放置于葛野大秦寺,这尊佛像就被推论为是微笑的弥勒。小原二郎①就认为微笑的弥勒好像是朝鲜风,而且与法隆寺的。玉虫厨子”传说联系在一起,代表飞鸟时代有名的工艺品,因为震撼,所以说是从朝鲜半岛来的就成了定论,但是京都大学昆虫学教研室的山田保治,从装饰中使用的玉虫翅膀着手调查,发现这种玉虫在当时的朝鲜半岛没有生息的可能,为此断定是日本制造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