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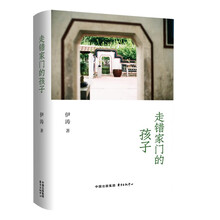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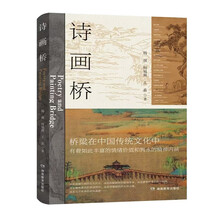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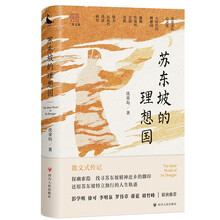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革命历史人物传记,如《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赵一曼》等,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这些作品至今已经畅销数百万册,有的甚至超过千万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值此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我社再版重印此套作品。让我们重温经典,在回顾历史中不忘来时路,听党话、跟党走,让“把一切献给党”成为永恒的主题。
吴运铎同志本来是一个煤矿工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接受了党的教育,参加了革命部队,和同志们一起,刻苦钻研,研制武器,建立兵工厂。他一再冒着生命危险,突击紧急任务,三次负伤。他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来战胜死亡的威胁。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也紧张地学习,坚持写作和科学实验,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童年
我是在矿山上长大的。
听父亲说,我们老家在湖北,家里穷得连瓦也没一片。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父亲从小四处流浪,做过店铺学徒,做过苦工,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当一名记账的小职员,才在这里安下家。
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矿工们都叫它安源山。山上山下,长满茂密的树木。山腰上,烟囱竖立,日夜喷吐着黑烟,炭粉把青山绿树都染黑了。连绵不断的高山,包围着这座矿工城。
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在我童年的心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老人们说,那里藏着宝物,谁能得到宝物,谁就能得到幸福。也有人说,那里暗无天日,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人们就不再受穷受苦。听到这些神奇的传说,我一心想进矿井。虽然母亲不断地嘱咐我说:“煤窑里小孩可不能进去,进去就出不来!”也吓不住我。我像一只初出巢觅食的小鸟,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恨不得找个机会钻进矿井,把听到的一切都弄个明白。
离家门口不远的直井旁,煤车一溜溜地从井口运到洗煤厂。我喜欢学工人们的样子推煤车,弄得满身大汗,有时趁工人不注意,钻进空煤车,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们的勇敢,也想冒险尝试一下,挽着烟囱上的铁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弄得满脸煤灰,刮破了衣服。只是,每次溜近煤窑口,都被大人赶回来……
有一天,父亲买了一只鸭子,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哥哥说鸭子会浮水,不沉底。难道真有这种怪事?趁母亲没看见,我悄悄地解开绳子,抱起鸭子,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的广场上,钻过了栏杆,把鸭子丢进喷水池里。
喷水池是洋灰砌的,池里都是发电厂排出的热水。水流涌过粗大的铁管,喷到半空,又倒泻下来,发出闷雷一样的响声,鸭子在池里吓得乱窜。父亲不问情由,就把我拖回家去,打了一顿。第二天,拿来一个新书包、一本新书,把我叫到跟前说:
“你在家调皮总算调够了,今年六岁啦,该上学了,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书去!”
读书本来是好事。哥哥们都上了小学,我一直很羡慕。谁知父亲偏不让我跟哥哥们一起。父亲对我说:“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既然算是一种“惩罚”,这个“上学”,我根本不感兴趣。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给我换了新衣服,用手帕包了一对蜡烛三支香,还拜托邻家的张大妈送我去后山上学。
胡老先生一看来了新学生,马上换了一件长衫,端端正正坐在上首。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着“天地君亲师”。张大妈忙着点蜡焚香,吩咐我:
“快拜老师!快磕头!”
“又不过年,干吗磕头呀?”
张大妈不回答,硬按着我磕了三个头。
在这里读书很枯燥,整天念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意思一点儿不明白,先生也从不解释。你要问他,他就瞪眼。
每天我路过煤窑直井,听见围墙里的嗡嗡声,就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脑子里时刻想:机器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这样叫唤?……应该去看看!
一天,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一出家门,跑上后山,把书包挂在树叶稠密的树枝上,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围墙门口,背着警察,溜了进去。
随着机器的响声,轻手轻脚走进了打风房。那庞大的空气压缩机整齐地排列在厂房里,巨大的飞轮飞快地旋转着,白光闪闪。这庞然大物,不息地旋转,发出隆隆的吼叫。真叫人害怕。说什么好呢?可是一见机器就叫人走不开了。我走近围着机器的铜栏杆,两眼盯着机器出神。
背后有只粗大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小家伙,你跑来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司机工人何叔叔,正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叔叔,那个推机器的人,躲在哪里?”
他用棉纱擦了一下油手,摸着我的头问道。
“什么推机器?”
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你这小傻瓜,这哪里是人推的,是汽,懂吗?”
也许是不忍叫我失望,他又安慰我说:
“不要紧,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要人推还算什么机器!机器是人造的,你要它怎么着,它就怎么着。”
从那时候起,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它不吃饭,也不休息,老是轰轰隆隆地忙碌着。可是最了不起的还是工人,他能让机器听话,还能造机器!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
我再不愿坐在冰冷的书房里,读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书本了。每天早晨,我照例把书包挂到树枝上,到处跑个够,天黑才回家。机器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甚至夜里做梦也全是机器。这个秘密很快被母亲发觉了,她又托张大妈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
“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先生问我。
“看机器去了。”
“我叫你去!我叫你去!”
他一手死死拧着我的耳朵,挣也挣不脱,疼得我抱住先生的大腿直转圈子。
“看机器有什么不好?偏要拧耳朵!”我想。
晚上回家,父亲问:
“你的耳朵怎么啦?”
“老师拧的!”
“为什么?”
“逃学!”母亲在旁边说。
“看机器去了,不是逃学。”我觉得母亲不公平。
“咳!你逃学去看机器,拧耳朵不冤枉!”父亲说。
这一夜,耳朵疼得要命,母亲用凉手巾给我捂着。我侧着身子睡,真想大喊大叫。到底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去找胡老先生。
“胡老师,我这孩子太调皮,你要好好管教他。不过,拧耳朵要两只都拧,拧完这个,再拧那个。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多难看!”
“好吧,叫他明天别来就算了!”先生冷冰冰地板着面孔,不教我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私塾。学校半路也进不去。母亲常为这事发愁:
“你这样下去,怎么是好啊!”
“不要紧,妈妈。将来我要当工人,造机器、开机器!”
我跑遍了整个矿山。电车厂、煤车厂、发电厂、打风房、锅炉房、升降机房,都是我经常拜访的地方。我成天在车间里混,常常连饭也顾不得回去吃。
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是修理厂的老车工,我再三请求他带我去玩。他说:
“你听话不听话?”
“带我去吧,一定听话!”
我们走进了修理厂。几百部加工机械——车床、刨床、钻床,还有许多特别的工作母机,都整齐地排列着。头顶上的起重机,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这里能修理全矿山的机器,也制造机器。这里的机器和我以前看见过的完全不同,以前看见过的打风机、发电机,都不太了解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旋转。可是这里的刨床、旋床,却能看见它们工作的结果。成块的钢料卡在床子上,机器一动,一剥一层皮,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在锻造间里,起重机从炉里拖出通红的钢铁,送到了蒸汽锤的铁砧上,蒸汽锤猛烈地打击大铁块,火花四射,光彩夺目,比烟火还美。在工人手里,不管多坚硬的钢铁,都变得非常驯服。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站在车床旁边干活呢?我真盼望自己快长大,做个工人!
在那一边,工人们拿着钢的工具刀,在旋转的砂轮上一碰,便喷射出五彩的火花,刀子立时锋利无比。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玩具枪,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惹得母亲天天埋怨。这回可好了,把菜刀拿来磨快,让母亲欢喜欢喜。
第二天,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进了车间。趁大家不注意,拿出菜刀就往砂轮上碰,不料,火花一闪,菜刀脱手飞出,几乎砍在脚上,我右手震得发木,瞪着眼直发愣。
毛师傅发觉了,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替我磨好,责备我说:
“你再乱动手,就不许你来了。这是好玩的吗?”
他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说:
“孩子,你还小哩!”
我非常尊敬毛师傅。心想,像毛师傅那样的人,都是些特别的人,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
跟工人们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些小锤子、小凿子、小锉刀,我很爱这些礼物,心想,他们送我这些东西,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
到秋天,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念“大狗叫小狗跳”。但是心里老记挂着机器,放了学,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
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早晨的第一课,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许多孩子受不了,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祷告一开始,就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等上课钟响了,再爬进来。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日子一长,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了,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堵在洞口,每人给了五板。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
大考结束后,成绩单送到家里。哥哥们都升了级,我的功课不好,留级一年。
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
“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
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在我面前摆来摆去。他们一走过来,我就闭上眼睛。可是心里难过,觉得丢人。
这年冬天,我约束自己,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虽然还是想念车间,到底没出过家门。
第二年,我升级了,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二年级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我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拾来一些碎铁片、洋钉和铁丝,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头盒口上,两头钉上小洋钉,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栏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势打上水来,谁知两脚腾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刚张口叫喊,一股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还照我头上打了两巴掌,说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顶着肚子,一手按头,控出许多黄水。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
夏天,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大孩子洗澡,我心里又痒痒起来。想下去,又怕再挨淹。一时拿不定主意,愣愣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两手在水里扒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连忙脱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我使劲地打水,一高兴忘记了危险,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两手一使劲儿,划出了水面,刚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脸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抱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到底学会浮水了。
童年
劳动的开端
在矿井里
觉悟
我们的工厂
入党
转移
反“扫荡”
第二次负伤
新任务
制造枪榴弹
拆定时炸弹
我们的平射炮
第三次负伤
永远前进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