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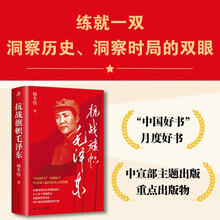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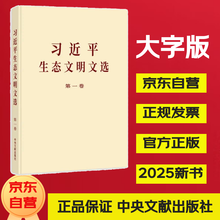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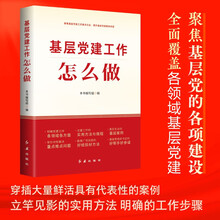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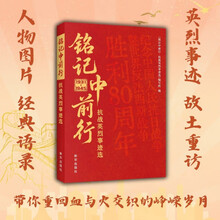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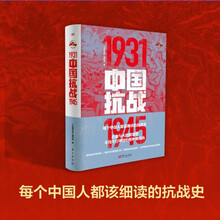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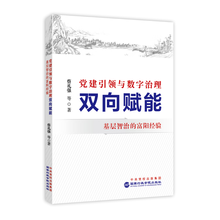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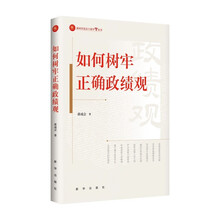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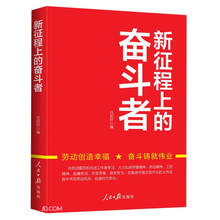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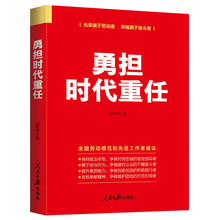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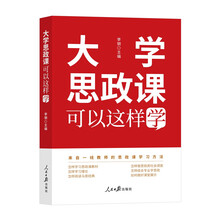
故事发生在1927年至1936年间的海岛小城厦门。“九一八”事变后,《鹭江日报》副刊编辑吴坚在斗争中加入了共产党。生长在农村的石匠儿子何剑平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春,组织决定派吴坚到漳州任《漳声日报》主编。何剑平与党组织负责人、排字工人李悦,在厦门搞地下印刷所,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女学生丁秀苇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闽东游击区来的陈四敏也以数员身份为掩护,组织领导了“厦联社”,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因叛徒出卖,四敏、李悦、剑平先后被捕入狱,吴坚也被捕押到厦门。主管审讯的是吴坚当年的“结拜兄弟”、“蓝衣社” 特派员、侦察处长赵难。他一方面软化吴坚,另一方面又利用因政治无知误入侦察处当小书记员的林书茵与吴坚的旧情打动吴坚,结果均遭失败。林书茵在吴坚的教育下觉醒,成了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联络人。为了营教狱中的同志,党组织领导了越狱斗争。在越狱中,四敏献出了生命。吴坚、剑平、秀苇安全脱险。林书茵也逃出“魔窟”。
第一章
从我们祖先口里,我们常听到:福建内地常年累月闹着兵祸、官灾、绑票、械斗。
常常有逃荒落难的人,从四路八方,投奔来厦门。于是,这一个近百年前就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海岛城市,又增加了不少流浪汉、强盗、妓女、小偷、叫花子……。旧的一批死在路旁,新的一批又在街头出现。
一九二四年,何剑平十岁,正是内地同安乡里,何族和李族械斗最剧烈的一个年头。
过去,这两族的祖祖代代,不知流过多少次血。这一次,据说又是为了何族的乡镇流行鼠疫,死了不少人,迁怒到李族新建的祠堂,说它伤了何族祖宅的龙脉。两族的头子都是世袭的地主豪绅,利用乡民迷信风水,故意扩大纠纷,挑起械斗。于是,姓何的族头子勾结官厅,组织“保安队”;姓李的族头子也勾结土匪头,组织“民团”。——官也罢,匪也罢,反正都是一帮子货,趁机会拉丁、抽饷、派黑单,跟地主手勾手。这么着,恶龙相斗,小鱼小虾就得遭殃了。
何剑平的父亲何大赐,在乡里是出名傈悍的一个石匠,被派当敢死队。一场搏杀以后,何大赐胸口吃了李木一刀,被抬回来。他流血过多,快断气了,还咬着牙根叫:
“不能死!不能死!我还没报仇……”
何大赐的三弟何大雷,二十来岁,一个鹰嘴鼻子的庄稼汉,当晚赶来看大赐。这时候,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
“李木!……李——木!……”大赐喘着气说不出话,手脚已经冰凉,眼睛却圆睁得可怕。
……
国家的文本
国家的文本
——高云览《小城春秋》新读
路文彬
无可否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作为一个崭新主权国家公民的中国人民,其国家主权意识即刻获得空前增强,“共和国情结”开始普遍深入人心,人们无不怀着无比崇敬和自豪的情感来认同这个得之不易的共和国。依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国家主权的膨胀意味着属民在某种意义上——从模糊到越来越明确——知道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知道这种成员身份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1)于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的国家主人公姿态,在此刻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人人秉持的统一姿态;广大作家也正是操着这种姿态投入写作的。此时的写作于某种程度上成了作家对自我“成员身份”的一种自觉认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使作家同政府之间不仅在文学观念上,而且在现实乃至历史观念上均暂时达成了共识,并进一步使之合法化。
哈贝马斯“合法化”这一语汇,在杰姆逊那里“指的是在某种有组织的社会秩序中总是含有一定的国家化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部分地建立在对人身侵犯的基础上的”(2)。因此,这种共识的合法化也就意味着其受到了国家暴力的保护,谁若对它加以违抗就必然会遭罹国家暴力的干涉,只是量罚轻重上的不同而已。此外,我们还不难看出,作家与政府之间在此刻所拥有的默契使文学极其自然而然地变换成“国家的文学”,广大作家自动遗忘了个人化的写作意愿,转而由国家化的立场来重新对待写作;这一时期的文本无不是以“国家的文本”的面目在国家这一公共空间里全新登场的。
高云览《小城春秋》这部完成于五十年代、书写中共地下组织成功策划发动1930年厦门大劫狱历史事件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因而从国家理论的视角对这个“国家的文本”进行切入或许不啻是种十分恰当的选择。而且,在如此读解《小城春秋》的思路上,我们也会很容易使寓于其中的“国家性”品质得到验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家的文学”所具有的品质特征在相当程度上是国家本身品质特征的自然反映,并不是由政府借借外力强加于它的。但是,国家本身的品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却又不能不取决于政府或者说政党对于国家的理解和认定,因为某个国家的建立正是某个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实现,相对于其他政党,它的意识形态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故所创建的国家自然也会表现出自己的这种独特性。譬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存有质的差异,其品质特征当然不可能雷同,因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文本,它所体现出来的品质特征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品质特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小城春秋》所蕴涵的“国家性”品质理所当然地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范畴。
首先,由《小城春秋》的创作缘起来看,它就是一个有组织行为运作的公共性事件,而并不是作者出于个人文学情趣的私人性写作。据作家本人交代,该书的写作是因为“党派人来和我联系,并把劫狱的全部材料交给我,鼓励我写出来”(3)。作家自己也一直是将其作为“在我心里悬了二十多年”的“党交给我的任务”(4)来完成的。其次,从作品的创作主题观之,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小城春秋》,也应当被看作是对国家/政府行为的一次积极回应。原因在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面临着一个“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写”(5)的任务。这个任务从根本上说来,可以理解为借以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手段。在安东尼·吉登斯的眼里,“历史”的书写所具备的恰恰就是这种作用。他曾说:“出于文本所描述的是一定社会情境中‘已经发生的’和‘应该发生的’事情,被书写的‘历史’也就能成为权力的强化工具。”(6)另一方面,像这一时期其它许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小城春秋》的历史感是由这场创立起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赋予的。而按照卢卡契的观点,历史感在西方的出现归结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他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进行严肃的彻底的考察——就是民族的思想浸透到最广泛的群众中去。在法国,民族的感情只有在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最终地变成农民、较低级的小市民阶层等等的体验,成为他们的感情。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体会到法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创造的祖国”(7)。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关联的民族运动“确实地把真正的、群众运动对历史的感情、历史的体验带到广泛的人民阶层中去”(8)的。然而,在中国情形却有所不同,市民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资产阶级天生“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的“软弱性”(9)都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使中国民众普遍地获得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历史感;唯有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方能够真正履行这一使命。所以我们有理由认定,《小城春秋》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历史动机是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情感分不开的,而这种情感必然会促使作家在写作时,自觉地选取为国家书写的立场,主动与政府的意志达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