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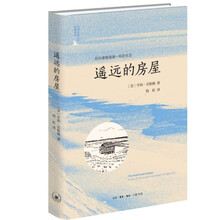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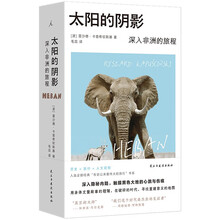
"阿莱克斯,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有勇气和尊严;意味着相信人性;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去战斗,并赢得胜利。差不多就是吉卜林在他的诗《如果》中所写的那样。你呢,你认为应该男人是什么样?"
"我想说,一个男人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人,阿莱克斯。"
这是一个单打独斗、孤身搏击、遭迫害、受欺凌、不被人们理解的英雄的故事。这是一个拒绝向任何教会、恐吓、潮流、思想教条和所谓的绝对原则妥协的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不随波逐流、不听天由命、有独立思想的,并因此被人杀害的男子汉的悲剧故事。
意大利首版发行100万册以上,其后再印达25次,被翻译为20多种语言,风靡全世界;并获得意大利总统亲自颁发的维亚雷焦文学奖。
1968年,帕纳古里斯因暗杀希腊军政府领导人被捕入狱,1973年被特赦。两天后,享誉世界的"采访女王"法拉奇前往雅典对他进行采访,两人迅速坠入爱河。1976年5月1日,帕纳古里斯在一场神秘的车祸中丧生。为了纪念爱人,法拉奇隐居三年,专心写了《男人》一书。书名源于法拉奇第一次与帕纳古里斯会面时的一段对话:
"阿莱克斯,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有勇气和尊严;意味着相信人性;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去战斗,并赢得胜利。差不多就是吉卜林在他的诗《如果》中所写的那样。你呢,你认为男人应该是什么样?"
"我想说,一个男人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人,阿莱克斯。"
你曾经说过,在任何一种压迫性的制度中,在任何一种专制集权的暴政下,无论它是右的还是左的,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昨天的、今天的还是明天的,高明的审讯就像一出戏,戏中的人物根据事先设计的情节进场出场,并受幕后导演--负责调查的审讯官--支使。你曾经说过,尽管这些人物扮演的角色彼此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迫使犯人招供。为了使他们成功,审讯官赋予他们特权,给他们充分行动的自由,而他则在幕后静观结果。反正他手里拥有一件颇具杀伤力的武器,这就是时间。他知道如果自己有耐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囚犯自然会屈服。所以,为了免于失败,囚犯就应该让这种武器失效,就应该进行反抗,让这场戏无法正常演下去。绝食,禁水,动粗,用暴力反对暴力,逼他们更凶狠地打你,打得你失去知觉。当受害者被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时,或因绝食而处于昏迷状态中,审讯自然就会告一段落。这样,受害者就可以得到休息,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去面对下一轮的拷打折磨,并且有利于他去了解、熟悉那些台词、场景,以及导演的风格。这些事情你事先并不了解,是在马里奥斯和巴巴里斯开始一唱一和时,你才意识到的。也就是说,你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的举动,才开始怀疑,他们是在背台词,扮演剧中的人物,是按照幕后一位高明导演的意图在进行表演。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耗你的精力,扰乱你的心绪,而你的情绪早已被那个怯生生的可笑上尉给打乱了。于是,与其说是依靠理智,还不如说是凭借本能,你就明白了:你必须保护自己,想办法让他们马上打你一顿。因为你被打昏以后,身体和脑子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就不至于乱中出错了。重要的是选择时机,而这个时机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给你提供了。他闯进屋子,对他们叫嚷道:"你们对他太客气了,知道吗?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太幼稚了,难道不知道,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与他打交道吗?"接着,他对你说:"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这个凶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调查清楚了!你是个潜逃到以色列的逃兵,是个从轮船上逃跑的叛徒!你这个该死的搞同性恋的混蛋!"
时机到了,赶快!你像一头豹子一样从床上一跃而起,像豹子一样抓住他的手,扳过他的头,大声怒吼:"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你这个穿少校制服的同性恋混蛋!"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正中下怀:就仿佛直到那时都一直把他们紧紧套住的弹簧突然脱钩了,马里奥斯和巴巴里斯失去了控制,三个腰间挂着警棍的中士失去了忍耐,他们一窝蜂扑到你身上,为塞奥菲洛亚纳科斯解围。于是,你的攻击就成了一场一对六的搏斗,而且这六个男人比你强壮,比你生猛。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两个在旁边,拳头、警棍、皮靴像冰雹一样落在你身上,你踉跄地摔倒在地上。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你用脚乱踹,用胳膊肘乱顶,用脑袋乱撞,宛如一头深陷罗网,想摆脱困境的豹子。桌子四脚朝天,椅子飞起来撞在巴巴里斯身上。他惊恐地跑到门口,不顾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劝阻,呼喊救兵。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命令不叫救兵是因为不想让其他人看到他的狼狈相。他怒吼道:"干吗还要叫其他人?"可是一名手持冲锋枪的下士已经赶来了,这是你最期待的事。你冲开人群,扑向冲锋枪,想把它夺过来。你紧紧地抓住冲锋枪,下士却死也不放。你只顾拼命夺枪,连警棍打在你头上、肩上、胳膊上都毫无知觉。你只听得见他们的吼叫声,以及与吼叫声混杂在一起的警棍乱打的闷响声。场面确实混乱,连马里奥斯的额头上也挨了一下。马里奥斯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朝误打他的人飞起就是一脚,但这一脚却踢在了巴巴里斯身上。巴巴里斯火冒三丈,对准马里奥斯的嘴巴就是一巴掌。于是,他俩就干开了,其他人也相互厮打起来。真是愚蠢,真是荒唐,他们一边相互厮打,一边相互劝说不要再打了。"住手!你是不是中邪了?快住手!够了!你没有发现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吗?我们需要对付的是他呀!"在这段时间里,你一直在与那个下士争夺冲锋枪,在争夺的过程中,你觉得他的手指松动了,慢慢松开了,瞧,你很快就要成功了:你猛然用力一拉,枪就到了你手里!你举枪瞄准。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天旋地转,你眼前一片漆黑。仿佛有一千只魔爪抓住了你,一万根绳索套住了你。
很遗憾,你并没有失去知觉。警棍只是把你打得晕头转向。你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想弄明白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使你无法动弹。你又躺在了床上。这一次,他们用绳子捆住你的脚脖与手腕。一个中士坐在你胸上,另一个坐在你腿上。塞奥菲洛亚纳科斯俯下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要把你揍成肉泥,畜生!揍成肉泥!"你盯着他的眼睛。你真想朝他脸上吐口唾沫。要是嘴里有唾沫的话,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吐他一脸。你把口里残存的一点点唾沫送到嘴边。他明白了你意思,顿时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棍棒!"巴巴里斯拧着棍棒,走上前来。"现在让你瞧瞧我的厉害,你这个叛徒!"他朝着你的脚掌猛打下去。一下,两下,几十下。这种击打脚掌的刑罚被称为"钉木桩"。真痛,痛得根本无法让人忍受。不仅痛,而且还像触电一样,电流从脚流到大脑,从大脑流到耳朵。然后流到胃,流到腹部,最后在膝盖处集中形成剧烈的痉挛。一个声音在机械地重复:"接招,给你一棍,又给你一棍,还给你一棍,再给你一棍,"你在心中默默祈祷:"昏过去吧,我的上帝!让我昏过去。别喊!让我昏过去。"但怎么能不喊呢?你开始叫喊起来。接下来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为了不让你喊,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封住你的嘴。嘴和鼻子全堵上了,他用拇指与食指捏住你的鼻子,用手掌捂住你的嘴巴。不,不能让他闷死我。不行,这我可受不了。你们可以用全世界的棍棒来打我,但不能让我无法呼吸。发发慈悲吧,我只需要一点空气,仅仅需要一点点空气。上帝啊!要是我能咬他一口就好了!要是我能露出牙齿,咬他的手指就好了!这样,他就会把手缩回去,我就可以呼吸。你把残存的所有力气都集中在下巴颏上。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张开嘴,使劲咬住他的右手小指,咬得指骨咯咯作响。一声凄惨的号叫突然爆发,这是塞奥菲洛亚纳科斯的声音。他举起血淋淋的手,小拇指被咬成了两截。接踵而来的又是一阵疯狂的暴打。"叛徒,烂货,婊子养的!混蛋!杂种!叛徒!"这几个穿制服的家伙齐声号叫着,像一首大合唱。有人扇你的耳光,有人把你的头往床上猛撞,有人挥舞拳头朝你的身上乱打,直到你身体的各部分毫无反应。床上的钢丝扎进肉里,疼痛被麻木代替。"快昏过去吧,我的上帝。让我昏过去,让我休息。让我昏死过去吧,哪怕一会儿也行。"终于眼前出现了一片黑暗,一片漫无边际的黑暗,仿佛你掉进了一个自由的深渊。四下悄然无声,寂静中似有一群黄蜂在你耳际振翅嗡响。你的嘴里全是血,太阳穴疼痛欲裂。你的意识湮灭在失去知觉和昏死片刻的轻松之中,如愿以偿。
当你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不仅手脚被绑着,腰间还捆着根粗皮带,使你无法动弹。你的大腿、胳膊、身体都失去了知觉,只是脸上还有感觉。仿佛你已身首分离,但脑袋仍然活着。你伸出舌头,舔舔嘴唇。觉得嘴唇很厚很厚,心想,它们肯定肿得吓人。你试着抬起眼皮,但眼皮粘在了一起,心想,它们也肿得令人恐惧。透过粘满眼屎的睫毛,你看到几个模模糊糊的身影,他们正喘着粗气。其中一个人笑着说:"真累!"一个呼吸正常的人的身影移了过来。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对他说:"就在这儿,是他吗?"这个身影走到你跟前,朝你俯下身子,像一片乌云遮住了你。他犹豫不决地问你:"你认识我吗?"你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回答说:"不认识。""撒谎!你们一起在军官学校待过,你会不认识他吗?"塞奥菲洛亚纳科斯插话说。那个身影又弯下腰来。也许他已发现你不是乔治了,但又不敢肯定。"怎么样?"塞奥菲洛亚纳科斯追问道。身影沉默不语,他的汗珠一滴滴落在你身上。"你快说呀,究竟是不是他?"塞奥菲洛亚纳科斯又问了一句。"我不敢肯定,应该是他,但我觉得他变了样子,也许是你们把他弄成这副模样的吧。""好吧,你明天再来。"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三天、第四天,他也来了。但他每天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因为你变得愈来愈难以辨认,因为他们愈来愈凶残地拷打你。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军官、士官、士兵,也就是说,都是人民的儿子。正是这个人民,我们为之流泪、痛苦、奋斗,总是宽恕、开脱,为它的罪孽辩解,因为这不能归错于他们。五年后,当我带你去拍X光照片,以弄清你为什么呼吸困难时,医生拿起底片,神色紧张,无比惊讶地说:"他们对这个人干了些什么呀?他没有一根肋骨是完整无损的!"
"一个充满激情的文本……绝对地引人入胜。" --《纽约时报》
和所有优秀的故事一样,这是一部极富思想性的作品……同时它还描述了一段发生在两个情感激烈的人之间的爱情,这爱情痛苦、狂喜、荒唐,但却卓越、崇高。
--《费城问询报》
"引人入胜……令人震撼……一本真正重要的书。"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