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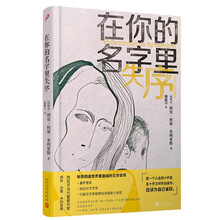



《木精》是日本芥川龙之介奖得主、著名作家北杜夫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被视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幽灵》之续篇。
一位在德国进修的日本精神科医生,为了同过往的一段恋情诀别,来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他游走于多瑙河流域、蒂罗尔群山和北欧的城镇,内心却带着对旧日恋情的甜美追忆。旅途中,他以托马斯?曼为榜样,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然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不安和彷徨仍旧萦绕心头,那位叫伦子的情人依旧一路跟随……
北杜夫以昆虫爱好者的敏锐观察力、精神科医生的审慎和作家清新幽默的笔法撰写了一部富于温情的成长日记。
第一章
走出神经研究所那古旧的大门,户外暮色浓浓。从早晨到现在,天色一直是阴沉的。眼下,阴沉的天色和暮色糅合,化为一份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寒意,直抵人心。
神经研究所建在小山丘上,站在门前俯瞰,小城风景尽收眼底。四层的山形墙小楼密密匝匝,房瓦的红色被低垂的夜幕所覆盖。
五月末,城中的栗树绽放出或白或粉的花朵,芬芳扑鼻。现如今,栗树已经挂上了褐色的小小的果子。这里的秋天很短,此后将迎来漫长的冬季,一连好几个月,都是寒冷阴郁的天气。
放眼望去,家家户户亮起灯火。我匆匆赶路,就像身后有人追赶似的,心里反复念着一句话:
“今天晚上可得饱餐一顿热气腾腾的大米饭。”
今天是我来德国蒂宾根正好两年的日子,心里却没有什么感慨,占据我头脑的,是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并非偶见于研究所食堂或者大学食堂的细长粒米饭。那种米饭,米粒干巴巴的,而我向往的,是圆粒米饭的微微黏牙的口感。
我匆匆赶路。
我所寄宿的那户人家,只住着房东玛雅寡妇(寄宿的大学生都叫她“赫尔加大婶”)和她那离婚后回到娘家的老闺女。房东只收留了连我在内四个大学生,在底楼开了一间日用杂货铺。
赫尔加大婶一头灰发,褐色眼睛,脸颊肉乎乎的。她完全不干涉寄宿者的生活,对于我这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好奇。老实说,我求之不得。我还拥有两项特权:其一,一周能用上一次房东的浴缸,其二,获准使用房东的厨房。
起初,房东拒绝了我用浴缸泡澡的要求:
“走五分钟就到澡堂了。去那儿洗。”
“哪怕是洗一次也行啊。”
“不行。再说了,研究所里有浴室吧。”
研究所的确有浴室。初来乍到时,我发现那儿总有热水可用,便每天去泡澡,结果遭到护士长呵斥,说除非是特殊情况,只有每周六才能使用。
“像你这样成天把泡澡挂在嘴边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赫尔加大婶说。
“日本人习惯每天泡澡。”我的话带些夸张。
“你去澡堂吧。房客不能用浴缸,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过了一阵,大婶的闺女患了伤风,高烧不退。我把从日本带来的药品给她,服用后转眼就退烧了。从那以后,赫尔加大婶便准许我一周用一次她家的浴缸。
今天不是泡澡的日子。我先去地下室,从墙角的箱子里取出一些我专用的煤块,带往四楼的房间。我揭开小小煤炉下边的盖子,点着旧报纸和小木片,总算是引燃了煤块。这种行为总是伴随着忧郁——尤其是封冻的冬日,煤块迟迟点不着的时候。
我随后去了澡堂。这家店以诗人乌兰德冠名,蒂宾根仅此一家澡堂。我在账台买了浴票,淋浴耗资五十芬尼,大池泡澡一马克。除了夏季,我几乎每次都是来泡澡。
往下走一层,一位长相酷似鸡的尖脸老太婆为我打开洗浴房的门。我平均每周来这里两次,按理说是熟得不能再熟,老太婆却总是爱答不理的,冷淡得很。我的态度和她是一样的。
洗浴房五平方米大小,墙上砌着瓷砖,镜子一面,椅子一张,洁净却了无生趣。我拧开水龙头,在椅子上脱去衣服,望着镜子里的裸体,觉得自己又瘦了。话说回来,我大体上就是这个体型,所以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有时候,我会回想起以前母亲房间里的那面大镜子。在年少的我的心目中,它总是板着脸,仔细打量房间的陈设和走进房间的人物。相形之下,这间狭小浴室的镜子就像数学方程式一般枯燥无味,就只是一块玻璃。不过在我疲劳的时候,在我阴郁忧闷的时候,它便格外鲜明地勾勒出我的形象。
毛巾和肥皂是我从住处带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三件打底衣物。我习惯在泡澡的时候洗衣服。德国人把肥皂塞进小袋里擦洗身体,我则是在内衣裤上涂满肥皂,用它们来擦身。
浴室的使用时间规定是三十分钟。我既泡澡又洗衣,时间吃紧,悠闲地泡个舒坦是做不到的。即便如此,当我把脑袋搁在浴池边仰面朝天,有时也会想起二战结束时的那个混乱年代——我那时上高中,住校生一个月只能泡上三次澡。现在算是幸福的。
今天的我,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安详闲适。浴池中,我的思绪被一种指向将来的不安所牵引。深思良久,恍然回神,我匆忙离开浴池,站在镜前擦拭身体,视线掠过镜面——三十一岁的镜中人,比入浴前更加憔悴、疲惫和阴沉。
先吃顿饱饭再说。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我像个傻子似的思考着,就好像吃饭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都说留学生至少会抑郁上一回,我却时常受到抑郁情绪的侵扰,情况最坏是来德国一年多的时候。我对将来彻底绝望,甚至想到了死。我求助于德国同事,服药治疗。
回到住处时,厨房已经整理干净了。我把米放进大锅里,以手指测量深浅后加水,点燃煤气。之后我走到地下室二层(这间奇妙地窖我迟早会详细写一写的),取来自备的鸡蛋和盛在塑料袋里的生乌贼肉。乌贼在附近斯图加特的超市有售,来德国打工的意大利劳工爱吃。昨天一位日本留学生去了斯图加特,我托他带回四条细小的乌贼,今天放进小锅红烧了吃。
起初劲头很足,不知怎的,忽然泄了气,心里空落落的。这种失落感常在夜晚造访我,最近,就连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也会蓦然袭来。
我机械地张罗起晚饭,就像是受人摆布的提线木偶。米饭总算熟了,红烧乌贼也做好了,把它们带回四楼房间,揭开锅盖,期待已久的蒸汽扑面而来。因为没有花时间好好焖一焖,米饭不够松软,气味倒跟偶尔尝到的日本米饭相似。在德国这边,这种圆粒米不受待见,属于最劣等的米。
我把米饭盛进特地从日本带来的饭碗里,浇上生鸡蛋和酱油,搅拌后大口咽下。三碗下肚,再来一碗。红烧乌贼只有酱油的味道,咸得很。我没嚼几口就囫囵吞下,仿佛这么做能弥补内心的空虚。
“简直跟饿死鬼一样。”我缓了缓,心想,“跟刚打完仗闹饥荒那会儿没什么两样。”
说到鸡蛋,毫不关心房客的赫尔加大婶得知我吃生鸡蛋时,着实吃惊不小:
“哎呀,真是生吃吗?不觉得恶心?”
我回答说,有一半日本人爱吃生鸡蛋。大婶便说:
“难怪日本人这么能生娃。”
吃撑了。先前一直折磨我的焦虑感散去,但那份深深扎根在自闭的我心底的孤独(恐怕会伴随我一辈子吧),却一点点地渗出意识表面。
说到孤独,回想起来,从我的高中时代——不对,是从孩提时代起,便与我如影随形。有时它是肃杀的,戕得我嗓子疼;有时是甜美的,是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孤独。
“人为何讲述回忆?”
很久以前,我在记录灵感的册子上写下这句话。
这时,一个女童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