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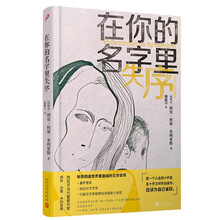



《幽灵》是芥川奖得主、著名作家北杜夫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青年的“我”身处成长边界,过去的不安和希望在心中渐渐苏醒。曾经痴迷于昆虫的少年时光、逝去的父亲和突然离去的母亲、第一次拨动“我”心弦的美丽少女、穿插在回忆中的优美旋律……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鲜明的细节渐渐淡去,但在记忆的角落里,它们似乎在向“我”提示着什么重要的线索。
探寻埋藏在脑海深处的幼年记忆,探明它们为何被淡忘,也许是揭开心灵秘密的重要钥匙。
人为何讲述回忆?
正如每个民族都有神话,每个人的心中也有神话。这份心中的神话逐渐淡去,不久便在时间的深处隐没形姿。然而,人总在不知不觉间,反刍着朦胧的昔时潜入心房、在那里悄然留下划痕的些许往事,年复一年皆如此,直至生命终结。这反刍常在无意识中进行,有时却也会被反刍者发觉,就像悠闲啃食桑叶的蚕,觉察咀嚼时的微响,不安地抬起头来看看。此时此刻的蚕,是什么心情呢?
母亲在国外度过她的少女时代。我不知道她怎么跟父亲走到了一起。
她的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如纸隔扇门一般大。玻璃表面澄明透净,雕花的木镜框色泽昏沉,和日式的房间很不协调。由于没有地方可以镶嵌它,便把它靠在一面墙上。大镜子冷冰冰地板着脸,细细审度室内陈设。母亲想必是想讨好镜子吧,她尽己所能,将房间精心装饰成西洋风格。地
板上铺了浅灰色的地毯,以遮蔽日式的榻榻米。衣柜和床的陈设恰到好处。在年幼的我眼中,童话世界般的华丽色彩充盈整个房间。色彩斑斓的衣裳随意搁置在椅子上,它们或柔软,或厚实,有的袖子上带褶子。一面墙上覆着哥白林挂毯,别处也铺盖着许多布艺制品,以此遮掩粗陋和陈腐的东西。
年幼的我钟爱那个房间,一方面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更多是出于一种对异类事物的向往和对新奇事物的眷恋。就说那张敦实的红木梳妆台吧,它包藏着诱惑我稚嫩心灵的复杂阴影。抽屉中的梳子、发卡、指甲油都让我惊叹,乃至忘却自身的存在,就像少年时代的我在森林中发现的珍奇昆虫或者蘑菇。台面上,化妆水、香水的小瓶子很是新奇,散发出甜腻的香气,闻一闻,我浑身酥痒,不禁缩起身体。特别是那个雕花玻璃的香水喷壶,有一个可爱的橡胶球,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拥有一个。我双手捧住香水喷壶,久久注视它那致密锐利的光泽,时常忘了时间的流逝。然而有时,我会突然意识到一旁大镜子那冷峻的表情,它凝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直想逃跑。不过,胆怯很快消散,我甚至怯生生地期待着:那面镜子里,会不会显现出别人的面容和身影呢?
不知为什么,我对各种形状很感兴趣,因此我常常蹲下,研究地毯上白色的花纹。有的是枝叶的形状,有的是人的各种体态,稍稍离得远一些,只见枝叶和人形拼凑到一起,构成一张人脸,像是挂毯上斯芬克斯的面容。忽然间,视线错乱了,人脸消失了,空留一堆混乱而无趣的花纹。我跟地毯玩对眼游戏,一玩就是好久,试图掌握它那变化万端的表情——那张脸最终变得暧昧模糊,我每每都会感到失望,觉得自己又上当受骗了。
“那张脸是什么呀?”
我只向母亲发问过一次。本想随口问问的,不料气息竟急匆匆地冲出我的嗓门,就像是突发咳嗽一样。
“脸?在哪呢?这是鸟儿吧?这是树叶。没有脸呀。”
经母亲这么一说,“脸”果然不见了,就连先前我认定是人形的纹样,如今看上去,也有了鸟的形状。我只觉得母亲施了魔法。抬眼看,母亲微笑着,她的额际很白,给我的感觉很陌生。我低下脑袋,抚摸地毯,感觉像是摸着动物的毛。
父亲似乎是那种叫“学者”的人。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我初谙世事。
现在想想,父亲是一位优秀的业余艺术家,生来便洞悉了“创造”的尊严和卑劣,而对另一个凡庸的、浅显的世界的憧憬,使得他没有深入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他冷静地沉醉着,留给后世的,只有几册游记和随笔,以及一本青色封面的诗集。书上介绍他是美术评论家和随笔作家,有的还给他添了“旅行家”的名号。
我幼年时,父亲的头发就发了白,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戴上一副无框的四方眼镜。父亲老是忘记眼镜放在哪里。每当他寻找眼镜,家中便乱作一团,母亲、女佣、阿婆都被动员起来,挨个房间寻找。在我看来,她们匆匆忙忙地东奔西走,并不是为了找眼镜,而仅仅是为了跑动而跑动。我随她们一道跑来跑去,但中途常常被墙壁上的污迹,或是院中树木投在檐廊地板上的影子吸引住,忘了自己正在找东西……不久,眼镜找到了。它或在碗橱上,或在坐垫边,有时竟在厕房里。父亲“嗨呀”一声叹,接过眼镜,十分不悦。大家的脸上现出各异的笑容,尤其是阿婆,她竭力屏住闯到嘴边的笑,结果噎着了,呛个不停。
父亲几乎不说话,偶尔发声时总令我惊慌,仿佛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他常把一只手捂在嘴边,摆出忍住咳嗽的姿势,却总也咳不出来。我能隐约回忆起他的举止体态,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面容。我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我试着将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与我记忆中暧昧不清的父亲形象相叠,感觉总归是不搭配。倒是对他周身的静谧,我记忆犹新。确切地说,那种静谧带着忧郁和颓废,和隐者或者科学家身上的安静截然不同。或许,安详离世的病人周身荡漾的,就是这种气氛吧。
北杜夫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小说家,他的文字富有诗意,像乐曲一般从书中流淌出来。
——《洛杉矶时报》
这本小说带着甜蜜的忧愁,偶尔闪现出一丝幽默,展现出一段已经永远消逝了的美好时光。
——《哈佛书评》
北杜夫23岁开始写《幽灵》,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展现出一种还未完全远离少年时期的天真和纯粹的感性。……能够写出《幽灵》这样的长篇小说,他确实是善用了生命中这一特别时期的体验。无论在之后的文学道路上如何走向成熟,可能他也再写不出《幽灵》这样的作品了。
——奥野健男(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