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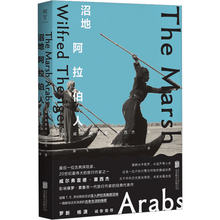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原是德拉克洛瓦作于1832年的一幅名画,那时阿尔及利亚刚被法国征服不久;而一个半世纪后,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已二十年,那些在独立战争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她们尚需作出哪些努力去扩宽自由度?阿西娅·吉巴尔向我们讲述女性的生存经验和困境,反抗与服从,法律对女性的严苛以及动荡不定的女性地位,这使得此书受到广泛的注目,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这部短篇集初版于1980年,现增添了新的篇目。
后记
受禁的目光,戛然而止的声音一
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德拉克洛瓦 德拉克洛瓦:法国浪漫派画家,《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是其代表作之一。抵达阿尔及尔进行短期停留。他刚刚在摩洛哥住了一个月,浸淫在视觉极度丰富的世界里(华丽的服装,狂热的幻象,奢华的宫廷,优美的犹太婚礼或流浪音乐家,高贵的王室动物:狮子,老虎,等等)。
这个与他近在咫尺且处于同一时代的东方带给他完完全全极度的新奇。他在《沙尔丹那帕勒之死》 《沙尔丹那帕勒之死》:德拉克洛瓦于1827—1828年间创作的油画,现藏于法国卢浮宫,描写阿尔及利亚第一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沙尔丹那帕勒在行将覆灭时,将后妃宫女及其爱马统统杀死,然后纵火同归于尽的场景。中所梦想的东方——只是这里洗净了一切罪恶的念头。而且是一个自从《希阿岛的屠杀》 《希阿岛的屠杀》:德拉克洛瓦于1824年创作的油画,描写1822年土耳其侵略军在希阿岛上大肆屠杀希腊贫民的场景。以来就脱离了可恶的土耳其统治的东方,只在摩洛哥。
就这样摩洛哥成为梦想与现实审美理想相遇的地点,一个发生视觉革命的地点。德拉克洛瓦恰好可以晚一些写上:“自我旅行以来,人和事在我眼里变得不同。”
在阿尔及尔,德拉克洛瓦只待了三天。首都不久前刚被占领,多亏了一个幸福的巧合,在那儿的短暂停留为他指引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方向,当他在摩洛哥旅行时这个世界对他还是那么陌生。生平第一次,他得以进入一个禁区:阿尔及利亚女人的世界。
他在摩洛哥发现的世界,被他用素描定格在画板上的,主要是个男性的、武力的世界,充满阳刚气。现在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场持久的盛宴,满眼皆是奢华,喧闹,车水马龙,飞快地掠过。然而从摩洛哥到阿尔及利亚,德拉克洛瓦同时也越过了一道难以觉察的边界,它将颠覆一切记号,后人记忆中的“东方之旅”都起源于此。故事已经很出名了:阿尔及尔港口的总工程师普瓦莱尔先生,是绘画爱好者,他的客人中有一位大人物,原来是小型赛艇的老板——一八三〇年以前被称为“首领”——在长时间讨论之后,他同意让德拉克洛瓦进入他的府邸。
一个朋友的朋友,顾尔诺,对我们讲述了这次探访的细节。宅院位于杜克斯那街的尽头。德拉克洛瓦,在这家的丈夫应该还有普瓦莱尔的陪同下,穿过一条“阴暗的走廊”,走廊尽头却豁然开朗,不经意,在近乎不真实的光线照耀下,所谓的后宫出现在眼前。那里,女人和小孩在“成堆的丝绸和黄金中”等着他。前首领的妻子,年轻美丽,坐在一个水烟筒前;普瓦莱尔告诉顾尔诺,德拉克洛瓦“仿佛陶醉在眼前的景象里”。
交谈中,由丈夫即席充当翻译,他希望了解这“对他而言既新鲜又神秘的生活”的一切。在他动手画的多幅速写中——妇女们呈不同的坐姿——他记录下在他眼中最为重要不能遗忘的内容:明确的色彩(“黑色金线,亮紫色,深印度红”,等等)以及服装的细节,复杂而新奇的搭配迷了他的眼。
简洁的图像或文字注解,可见他仿佛手舞热情,眼含醉意:转瞬即逝的刹那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游移。顾尔诺记录:“这股热情只怕连冰糕和水果都难以令其冷却。”
焕然一新的视觉,成为纯粹的影像。怕这许多的新奇事物混淆起来,德拉克洛瓦强迫自己在素描上标注每一个女子的姓和名。素雅的水彩画上有芭伊雅、慕妮和左拉·本·索尔坦,左拉和卡杜雅·塔波丽吉。铅笔勾勒出不知名的异域的身体。
罕见的丰富色彩,发音新奇的名字,是这些撩动了画家的心绪,激发了他的热情吗?是这些令他写下:“美哉!仿若回到荷马时代!”吗?
在那里,对隐居的女人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拜访,画家经历了怎样的震撼,或者怎样迷惘的困惑?这半开的后宫深闺,真如他所见一般吗?
从这个物品琳琅满目的地方,德拉克洛瓦带回了:拖鞋,围巾,衬衫,短裤。它们不是游客平淡无奇的战利品,而是一段独一无二、昙花一现的经历的明证。梦中的痕迹。
他需要触碰他的梦境,延长回忆以外的生命,将记事本中的素描和图画补充完整。这里有一种类似恋物癖的强迫情结,更加确定了度过的这段时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它永远也不会再出现。
回到巴黎,画家花了两年描绘他回忆中的影像,尽管有文字记录以及当地物品的支撑,回忆仍是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不确定。他靠这回忆绘制了一副杰作,它让我们不断提出新的疑问。《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三个女人中有两个坐在水烟筒前。第三个,位于前景,半卧着,臂肘倚着靠垫。一名女佣,展示出四分之三的背面,举着一边手臂,仿佛要掀开重重的帷幔,它们罩住这个封闭的世界;作为一个几乎是装饰性的人物,她的作用就是延展其他三个女人身上闪耀的色彩光芒。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三名女人与她们的身体,以及与她们幽禁的地方之间的关系。顺从的囚徒待在封闭的空间里,闪耀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梦幻般的光——或许是暖房或玻璃鱼缸反射的光,德拉克洛瓦的妙笔让我们觉得她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谜一般令人难以捉摸。
十五年后,德拉克洛瓦重又回忆起在阿尔及尔渡过的这些日子,他重提画笔,为一八四九年的沙龙绘制了《阿尔及尔女人》的第二个版本。
构图几乎是一样的,但几处改动通过递推更好地表现了画作的潜在含义。
第二幅画中,人物线条没那么清晰,装饰元素没那么琐碎,视角也更广了。这样的定位造成多个效果:——让三个女人离我们更远,更深地融入背景——完整地暴露出房间的一面墙壁,让它加重这些女人的孤独感——最后强调了光线的不真实性。这样的光线突出了阴影隐藏的看不见的无处不在的威胁,通过女佣的存在表现出来,我们几乎看不见她,然而她就在那儿,专注地站在那儿。
女人依然在等待。蓦然显得更像囚犯而不是后妃。与我们观众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既不任人观赏也不拒绝旁人的目光。置身事外而又真真切切地存在于与世隔绝的稀薄空气里。
艾丽·弗尔说,年老的雷诺阿在谈到《阿尔及尔的女人》中的光线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们会像老雷诺阿那样哭泣吗,为了艺术之外的原因?一个半世纪以后,想起芭雅、左拉、慕妮和卡杜雅。这些女人,曾经被德拉克洛瓦——或许是不自觉的——以前人不曾有过的目光审视过,从那以后,她们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些让人无法忍受却又确实存在的事情。德拉克洛瓦的画被当作一个对东方女性的研究视角——应该是欧洲绘画史上的第一次,以往的欧洲画作惯于从文学角度处理后宫姬妾的主题,或者仅仅表现后宫的残酷和裸体。
三个阿尔及尔女人迷惘的眼中有遥远的也有眼前的梦想,如果我们试着捕捉梦想的实质:是思乡情结或隐约的温柔,她们显而易见的分神,反令我们对情欲起了向往。仿佛在女佣还没放下她们身后的窗帘,而她们还未坐下让我们观赏之前,她们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一直生活下去。
因为的确,我们在看。在现实中,是禁止我们这样去看的。德拉克洛瓦的这幅作品不自觉地令人着迷,并不是因为他笔下这个东方的表象,半明半暗里的奢华与宁静,而是因为,将这些女人置于眼前观看,他是在提醒我们,原本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这幅画本身就是一次偷看。
我想,德拉克洛瓦,十五年后,对这段“阴暗的走廊”尽头,一个没有出口的空间里,那群端庄神秘的女囚徒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只能通过被定格在画板上的出乎意料的场景来猜测远方的她们的不幸。
这些女人,是因为她们装作不看我们,又或者是因为,被绝望地禁锢着,她们甚至无法看见我们?这些坐在那里的不幸的人儿,从她们的灵魂什么也猜不出,她们仿佛被周遭的环境吞没。她们自己,她们的身体,她们的情欲,她们的幸福,一切都与她们无关。
在她们和我们观众之间,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跨越了内心深处的屏障,像小偷、间谍、窥视者匆匆的一瞥。仅仅两年之前,这位法国画家差点赔了性命……
于是,禁戒,在这些阿尔及尔女人和我们之间,漂浮。中立,不知名,无处不在。这目光,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它是偷来的,因为它来自外国,后宫和阿尔及尔城以外的地方。
数十年来——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在各处获得胜利——,人们可以看出,在这个自我放任的东方,女人的形象并无两样:在父亲,丈夫,还有比较困扰的,兄弟和儿子的眼中看来。
原则上,只有他们可以看女人。对于部落的其他男子(童年一起玩耍的表兄弟变成了潜在的偷窥者),当严厉的习俗最初有所松动的时候,女人展示的就算不是整个身体,至少是她的脸和手。
这种松动的第二步反而要依赖头纱。头纱将身体和四肢完全包住,让戴着它的女人能够出门走动,这么一来女人也成了男性世界里可能的偷窥者。在那里她像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当她用一只眼睛看的时候像个独眼的人。在某些情况和场合,“自由主义”的宽容将另一只眼还给她,让她的观看得以完整:两只眼睛,借着面纱的掩蔽,现在睁大了看外面的世界。
另一只眼也在,女性的眼光。可是这只被解放了的眼,本可以成为赢得外界光明的信号,幽禁之外的光明,现在它却被看作一种威胁;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昨天,艺术大师透过他孤独的目光对女性幽禁场所的观察,表现出他的权威,令其他画家黯然失色。而女性的目光,当它移动时,似乎,令男人感到害怕,他们呆坐在摩尔人的咖啡馆里,今天那里已成伊斯兰教区,而白色的幽灵飘过,不真实而又令人迷惑。
在投射到女人的眼睛和身体上的合法的(即父亲、兄弟、儿子或丈夫的)目光里——因为看的人首先寻找被看者的眼睛,然后才转向身体——有一种危险,它的原因越是出乎意料,危险就越无法预料。
无论什么——突然的发泄、轻率、不寻常的举止,被隐蔽角落撩起的窗帘分割的空间——都能让身体的其他眼睛(胸、性器和肚脐)有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危险。对男人而言这一切已经结束,这些脆弱的守卫者:这是他们的黑夜,他们的不幸,他们的耻辱。
受禁的目光:因为女性的身体当然是禁止被观看的,从十岁开始直到四十岁或四十五岁,她们都被监禁着,在围墙中,就算再自由也是在头纱下。然而同样危险的还有女人的目光,她们被解放可以到外界行走,却随时可能暴露她在行走中向他人投去的目光。仿佛忽然之间整个身体都在看,在“挑战”,男人如是说……一个女人——在走动中,也即是“裸体”的——在看,这对他们的窥视权,这一男性特权,岂不是一种新的威胁?阿拉伯女性最明显的变化,至少在城市里,是摘除了头纱。许多女性,往往在度过被幽禁的青少年时期甚或整个青年时代后,真正体会了揭去面纱的生活。
身体在房子外面走着,这是第一次它仿佛被“暴露”在所有目光下:于是变得姿态僵硬,脚步仓促,眼神紧张。
目录
开篇
法蒂玛述说之夜
今天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
哭泣的女人
昨天
无所谓放逐
死人说话
斋戒日
思乡
后记
禁止的目光,中断的声音
一种精彩绝伦的语言,一位伟大的作家。
——塔哈尔•本•杰伦
阿西娅•吉巴尔占据着我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们,她将我们放在她们的沉默之墙前加以比照,而此沉默正在成为我们的沉默……阿西娅•吉巴尔在写作中、因而也在历史中触发女人,重新安排女人的位置,她为此而写作。
——《摇滚怪客》
吉巴尔的小说扰乱了对立面的严格逻辑,不是作为抗议文学,而是为了寻求超越宏大叙事的空间。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她的小说刻意将人物与实践混淆,借此强调小说主题的无时代性,尤其是女性需要面对的困境、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语言和写作的救赎力量。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