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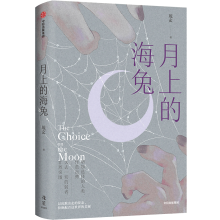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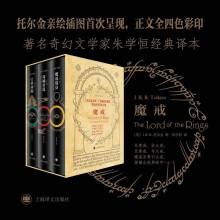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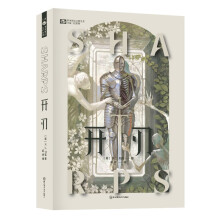
《白猿客栈》是一部原创的系列长篇小说三部曲,分别为《白猿客栈.黄河龙宫》《白猿客栈.诡戏金陵》《白猿客栈.敦煌沙窟》:
白猿客栈,是南京城深处琵琶巷31号的一家客栈,也是一家已经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江湖组织。客栈代代相传,每一代都有六个人——鬼手、佛烟、张三眼,水袖、蓑衣、不老生。初代掌灯、创始人为汉代的留侯——张良张子房。客栈的每一代掌灯均为张良后裔。每一代的掌灯除了具有和张良一样极高的智商、是运筹帷幄、“做局”的高手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天生的重瞳(书中称为三眼),可以堪破世间的一切幻术,且视夜如昼。
《白猿客栈.黄河龙宫》“白猿客栈”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民国初年,白猿客栈第五十六代掌灯带着客栈其他五人突然失踪,只留下儿子张寒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客栈。金陵冬天的年夜,一位年轻的女子带着一张蛇皮古画敲开了客栈的大门: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渐次展开,上代人失踪的秘密也抽丝剥茧一般地被揭露出来……通过这张蛇皮古画,张寒无意中涉入了一件奇诡绝伦的事件——乌衣巷墨家命案,也随后卷入了蛟族长生的漩涡——诡异绝伦的乌衣巷、长白山的囚龙之地、洛阳的龙门石窟、黄河源上的申家古楼、天下气宗的全真魁门……一桩桩谜案被破后,张寒也逐渐地接近了真相.....
第一章 琵琶巷三十一号
民国十七年,秋……
我叫张寒,今年三十岁,家住南京城,也就是古金陵。城东三十里,秦淮河畔有一条青石铺路的小巷,南京人雨天出行,多穿皮革雨靴,走过石板小路,叮咚作响,犹如拨弄琵琶,故而称为琵琶巷。
巷口北侧,有一间两层高的旧式小楼,破败的木门两边刻着一副对子——上联是:佛烟鬼手张三眼;下联是:水袖蓑衣不老生。阴刻的篆字,歪歪扭扭,只有“张三眼”和“蓑衣”这五个字被人上了朱红色的油漆。门楣上是一块匾额,白底黑字,上书“白猿客栈”四个大字。
我——张寒,就是这间客栈的掌柜。
白猿客栈,起于战国,兴于秦汉,源流虽已不可考,但是老江湖里的人都知道,如果一旦遇到了自己办不到的事情,或者解不开的难题,就去金陵琵琶巷找白猿客栈;只要出得起掌柜要的代价,白猿客栈就可以为你搞定任何事情。
这个季节,阴雨连绵。睡眼惺忪的我,窝在柜台后头昏昏欲睡……
一阵踌躇又细密的脚步声,在客栈门前的青石板上时断时续,搅扰得我不得安生。隐忍了很久,再也憋不住火的我猛地从椅子上蹿了起来,将那扇破旧的木门推开一个小缝,探出头去,沉着脸吼道:“能找到这里的,应当是懂规矩的江湖人,要么进来谈生意,要么转身离开,走走停停地绕圈子,你烦不烦?”
话音未落,眼前那把朱笔描白的油纸伞悠悠一转,一个有着火红色头发的女子缓缓地抬起头来,黛眉斜挑,满眼焦灼地看着我。一瞬间,我把后半截话噎了回去。
那女子身量高挑,着一件墨黑的衬衫,短发齐耳,虽生得一副江南眉眼,骨子里却带着北国佳人的英挺。女子的身后背着一个长条的锦盒,黑金镶玉,琥珀为钮,看样子价值不菲。
“您是?”那女子张口问道。
“我是这儿的掌柜,姓张,名寒。”我尴尬地撇了撇嘴。
“白猿客栈的掌柜,不应该是张九陵么?”那女子满脸疑惑地说道。
“张九陵是我的父亲,十二年前,把客栈传给了我。我,是这一代的张三眼!”
那女子闻言,下意识地瞟了一眼门边的对联,指着那五个描红的篆字,试探地问道:“只有三眼和蓑衣吗?”
这女子的话戳到了我内心的痛处。
“要谈就进来谈,不谈可以走!不送!”我冷哼了一声,正要关门,那女子猛地伸手抵住了门板。
我回头瞥了她一眼。冷雨寒风吹打得她有些轻微的颤抖,我长吁了一口气,将她带进了屋子,用柜台上烧着的热水,给她冲了一杯花茶。
暖气弥漫,她苍白的指节也泛起了一丝红晕。
“云绕江河月绕山,君臣龙虎入平川。提梁架海长安燕,特为解难访白猿。义气恩长……”
我一摆手,打断了那女子的话,那女子尴尬地把藏在手心里的那张字条藏在了袖子里。
“大掌灯……我……”那女子涨红了脸,局促不安得不知该说些什么。
“现在都民国了,大清朝切口盘根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不说也罢!有什么事,你就直说,也不用叫我大掌灯,我姓张名寒,叫我名字就好。”
我摇头一笑,给她的杯子里续了些水。
“我姓鲁,名绛,我想让您帮我查一件案子,白猿客栈的规矩我知道,这个盒子,就是我能付出的代价!”
鲁绛话一说完,便伸出手,解下了后背背着的那个长条匣子,将它推到了我的面前。
我放下了手里的茶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打,瞥了一眼桌上的匣子,犹豫着要不要打开。
民国五年,也就是公历1916年,我的父亲张九陵连同客栈里的所有人在年三十的晚上一起失踪不见,没有留下一丝的线索。我依然记得那是一个弥漫着爆竹味的除夕夜,父亲就端坐在客栈的大厅里,架了一桌火锅,摆上了碗筷。原本冷冷清清的客栈突然来了许多我从未见过的叔伯,父亲喊我去对街的酒坊沽酒,待到我回来的时候,客栈里已经空无一人:我的父亲就这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不见了踪影。仿佛身处梦境中的我,只能凭借火锅里仍旧沸腾的汤汁找回现实的影子……
“张先生,可是这东西您不满意吗?我还有一些积蓄,您开个价?”
鲁绛的话,将我从回忆的沉思中带了出来。
“对了,张掌灯,这匣子里有一幅古画,单论年份,最晚也是先秦时的古物,价值千万也不为过。”
话音未落,鲁绛伸手打开了匣子,取出了一卷佛经纸色的东西,铺在桌面上,看材质应当是某种动物的皮毛,经秘法鞣制而成,上面画着一幅诡异绝伦的图画。
在看到这幅画的一瞬间,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一股热血涌上了头顶,激得我几乎要从凳子上跳起来!
我见过这幅画!
是的!我见过!
十三岁那年,在我爹的笔记本里,我看到过这幅画……
一座弯弯曲曲的石桥上,盘踞着一只吐着猩红色舌头的大蛇,那大蛇眉眼如霜,着一身褐色长袍,自袖口里伸出了一条鳞甲森然的利爪,爪上捧着三支竹简。自桥下走来一只鬼目妖瞳的白猿,身着一身灰白儒衫,在那大蛇身前拜倒,伸出双手,欲接过那三支竹简……
此刻,我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真迹,只见这画的画风简练有力,笔法张扬雄奇,色彩丹朱如血,仿佛历经千年而不褪色……
“这幅画,你从哪里得来的?”我强行平复下内心的躁动,不紧不慢地问道。
“这幅画是我爹留给我的,至于他从哪里得来的,我也不得而知,张先生……”
“你的事,白猿客栈接了!”我将茶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真的?”鲁绛喜出望外地问道。
“当然。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的事了。”
我站起身来,拢了拢炉底的炭火,接过了鲁绛递给我的三个压着火漆印的牛皮纸信封……
小说中人物塑造,往往是将人生的贪嗔痴妄写到了极致。这也是文学史上,很多能让人记住的人物形象的特点。《白猿客栈》中的很多人物同样是按着“极致”的路子,奔着不朽的目标,“杀将”而去。同样是写痴,有白猿客栈的佛烟对阴阳家家主须弥的一往情深,也有公输家的鲁胥对初恋情人的念念不忘;同样是写贪,写妄,有苍梧道人对长生的执着,也有大秦洋行和天师会对财富的不择手段;同样是写嗔,有窦夫人姜氏在得知真相后的决绝,也有朱元璋在面对沈万三时骨子里的自卑……在放诞不羁中,敏贝勒是大起大落、大收大放,李龟年则是插科打诨、且看今朝;在人物性格变化中,鲁绛是因为身份的转换,杨惊雷则是历经世事后的沉迷……他们被作者“驱使”于笔端,展现于读者,丰满,真实,甚至让人一声长叹。
——蒋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