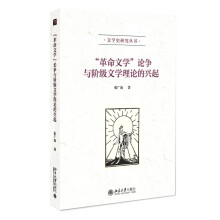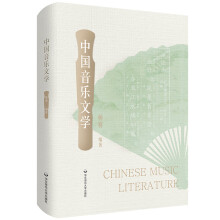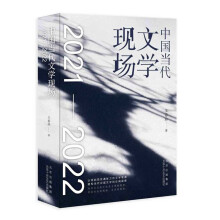《新世纪丁玲研究述评(2001-2018)》:
秦林芳①指出,与《在医院中时》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情况不同,构成《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触发点的不是观念,而是生活,它有其真实的故事原型——萧军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从侮辱中逃出的女人”。作为话语主体的丁玲在这个故事梗概中为“自身隐秘的思绪和情感”找到了具有同构性质的“客观对应物”,为了放大、强化这种体验以更多地“寄托”自己的“感情”,丁玲对故事和人物做出了进一步的想象、生发,从而在作品中创造出了主人公贞贞这一“比陆萍更傲岸,更强悍”的艺术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融注了作者生命体验、投射了作者的生命意识。在描写人物和情节时,丁玲通过对主人公贞贞生命流程中接踵而至的三个困境和三次出走的重点刻画,有层次地揭示出了贞贞生命的困境和其奋起突围的过程,其中寄寓了作者自己对生命价值的哲学思考:个体生命的实存状态是远不圆满的,漫长的生命之路充满了困境;而个体生命的价值,也正表现在这种正视困境的勇气和从困境中突围的当下之行中。另外,丁玲还通过环境描写对生命体验做出象征性的表达:“枯枝的树”隐喻的是个体生命,“灰色的天”是威压个体生命的象征性存在,二者对立性的关系则隐喻着个体生命的困境并尽显出了个体生命的伟大、崇高和庄严。
车凯旋②认为,《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两部短篇小说都是以妓女为主体对自身身体进行言说,它们都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张扬背后的男性构建的权利话语以及女性的艰难处境。《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中男性几乎是作为“抽象”的存在,成了女性需要的执行者,然而丁玲在努力刻画阿英这一形象从而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时并没有将男性置于与女性平等的地位上,男性始终处于弱化的地位。这种一味地压抑男性的行为其实正表明了女性在追求自主独立时不敢面对男性,不敢与之平等对话导致的尴尬局面,阿英并未真正地从精神上肯定自己的女性价值,从而实现自我的主体意识。《我在霞村的时候》充斥着霞村人对贞贞的议论,丁玲的女性解放启蒙运动在这里显得无比微弱,而叙述者“我”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歌颂贞贞的奉献精神,这种大义凛然的举动在革命话语之下遮蔽了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主义被充斥在以男性为代表的国家民族主体身份里,反映了女性的自身利益和民族革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体制在女性解放上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完善。这体现了女性话语在与政治话语相结合下,丁玲更多地倾向于国家话语,表现出某种暧昧的话语立场,游曳于两种话语立场之间,想要化解这种困境却又暴露了矛盾之下的焦虑。
《我在霞村的时候》与《金宝娘》有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相似性,在相似性中又有诸多相异处,呈现出异质同构、同质异构的复杂局面,形成一种互文效应。李明彦①从三个方面比较了两部作品:一、在故事样本的来源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听”来的故事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的作品,成为熔铸自己生命体验带有强烈个性特征的文本;《金宝娘》则是一个以写实的笔法真实地再现出来的“看到”的故事,情感渗透的程度要弱一些。二、就人物形象而言,视角的多元与分裂,造成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女主人公贞贞的形象丰富而多元,她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金宝娘》中的翠翠则是作者为了突显“翻身道情”这一主题需要而设立的一个单纯的指称对象,呈现出“扁平人物”的特点。三、在话语冲突方面,两部作品都写到了民间伦理和政治话语之间的矛盾。《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民间伦理塑造了政治话语,突显了民间道德伦理的无形力量;《金宝娘》中政治话语则成了前景和主旋律,民间伦理变成了背景和伴奏,后者的存在无非是印证前者的正确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