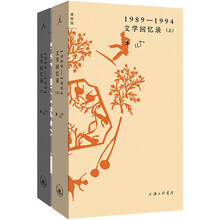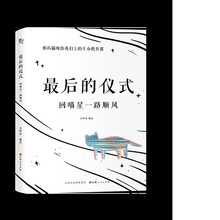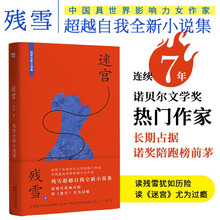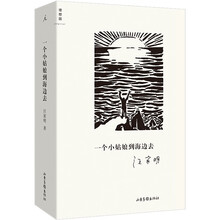套用你的话:多高兴的事儿啊!我们通过报纸这个中间媒介,相互信笔撰文沟通。我思量着你写在《新观察家》上,我写在《费加罗报》上,为的就是互相通信往来这一唯一的乐趣。
当然,我们还时不时地装出一副过问其他事情的样子。但是我们到头来总会回到彼此身上来。人们是怎么说希拉克①和若斯潘②的?互相铲球铲了整整一个星期。部长们焦躁不安。股市震荡起伏。郊区车辆被烧毁。财政大臣紧急会面。代表大会与会者们有些骚动,西雅图或热那亚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者。这都无所谓。我们在人们的惊叹声中和欢呼声中互相寄出的这些公开信件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我们的先辈也这样做过。
得意洋洋的你是福楼拜。总是谦虚平凡的我——在谦逊方面我不输任何人——甘当马克西姆·迪康①,又或许是路易·布耶②,随便哪个。
这件事我是不会对你讲的:马克西姆·迪康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福楼拜,祝贺他某本书的成功,是《包法利夫人》还是《萨朗波》,还是《情感教育》?我不记得了。他还给福楼拜提了一些文章删节方面的建议。在那封信的信封上,福楼拜大笔一挥,只写了一个单词:“伟大”。
我想起战后一些人发表的一些义愤填膺的言论:莫里亚克③在《费加罗报》上为慈善辩护,加缪在《斗争》上呼唤公平正义,第三个小伙子,是个共产党员,人们对他更没什么印象,他天赋过人,名叫皮埃尔·埃尔韦④,发表于《行动》上。我们稍微抬下头:这跟我们已经是一模一样的了。而在《近代》上,萨特则将不公的矛头指向加缪:“您怎么想?加缪?……”或是在《法兰西新杂志》上指向莫里亚克。你会想起这样一段话:“上帝不是艺术家。
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这登在某一期的报纸上,发表于一个糟糕的时间:1939年9月,如果我的记性够好的话。莫里亚克对此感到非常恼火,至于小说方面,他已经默默无闻好长一段时间了。
随后,我想,克洛德.朗兹曼①和阿兰·凡基尔克劳②,抑或是贝尔纳.亨利.列维③和与波斯尼亚④的一家匹萨店有关系的雷吉斯.德布雷⑤,他们已经重新接过火炬,并以些许的亲切取代了冲动。而贝尔纳.亨利则抛弃了他的名气:“再见,雷吉斯”或是我深表怀疑的更冷酷的说法:“再见,德布雷。我寻思着他们是不是见过面。
仅仅几天前,若斯亚娜·萨维诺⑥在《世界报》上写了封内容相当刺激并且利害相关的信给刚刚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安吉洛‘里纳尔迪⑦以及曾经推选过他的院士们。天哪!他们要怎样处理!里纳尔迪曾经推翻了我们光辉的文学理论,而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们最终暴露了他们真正的反动性与仇恨性。
安吉洛的的确确是毫无顾忌。他曾这样写过我很尊重的一位同行也是朋友之一,大概是这样说的:“在他小说的末尾,他将傻瓜和混蛋区分开来了。是不是应该提醒他,这两者是可以合并的?”而你知道他是怎么说我的吗?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他出版了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吧,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在安吉洛上任后,若斯亚娜·萨维诺关心孔蒂码头①的未来乃是一番好意。上帝啊!我很有信心打赌她改变不了什么,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她就像那个无耻而又高尚的老妇人②一样步伐缓慢而庄重,是见过世面的人。
而你,我亲爱的贝尔纳,你令我多么痛苦啊!简直和那些我深爱的却拒绝我的女孩一样残忍,甚至比她们更残忍。
长时间以来,我脱下帽子一直跑在你的后面,因为我欣赏你。而你,在我经过的路上,在两段长长的休止符间,只丢下一个残忍的字眼。我,总是殷勤、谦恭的。你,总是无情的。我时不时也会反抗,会放任自己发脾气。有一次——你还记得吗?——我在你自己的报纸上大发脾气,我就像是一个希望得到疼爱的孤儿,而这家报纸同情我便将我收养了。当然,是嫉妒,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嫉妒让我说了一些恶劣的话。代翁③欣赏你,贝松④欣赏你,埃里克·纽霍夫⑤也欣赏你。你是右派和左派的偶像。所有的年轻人都把你捧上了天。而我,我是如此狂热地喜欢着你,难道是他们无意间忽视了我吗?这几乎叫人无法忍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