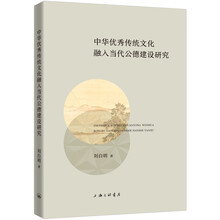卷上 文化真相
金庸的黄昏恋
金大侠加入作协了,文坛骚然。人们像突然发现了一场黄昏恋,开始为这貌似悬殊的婚姻担忧起来。
其实这本没什么稀奇的,金老以武侠起家,哪个主角到头来不都归属名门望派。有个令狐冲自由散漫,被逐出华山派师门,立刻就做了恒山派掌门,有段时间实在无法在正派立足,便归了日月神教,成了三教九流的盟主。一天也没闲着。就连杨过这样的孤儿,不也拜了古墓派小龙女为师,而且演绎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吗?至于郭靖、萧峰更是离不开丐帮。最不济的韦小宝,天天混吃混喝,最后还是弃暗投明做了天地会的香主,俨然一个卧底。
凭啥只让小说主角放火,不让小说¨乍者点灯?这么些年来,金庸老先生一直在寻找回归正统的路,从十多年前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到荣获大紫荆勋章,再到八十。高龄攻读剑桥博士,一直想从过去的神坛走下来,食点人间烟火。不能算错。错就错在我们原都把金老当成了神,一直以为他视功名如粪土、金钱如草芥。
笔者有幸几次和金老见过面,陪他老人家吃过饭,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和老爷子交换过书,感觉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老头,虽然感觉和当年夜读金文时的想像有大不同,但一个陌生的神和一个熟悉的人比起来,我还是喜欢这个人。
很多人都在计算金老和作协之间,究竟是谁先向对方抛了媚眼,究竟是谁占了便宜,各执一端的人们,都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论点增加论据,但都忘了一点,每个人都只能是自己,而不会是另一个人。
当然,换句话说,如果我是金大侠,我肯定不会加入作协。不但不加入这个协会,连所有的协会都不参加。以此证明我是牛人。
正因为如此,我不是金大侠,我做不成金大侠。我们都做不成金大侠。
依我对金大侠作浅薄地推断的逻辑,再来揣测一下中国作协,也挺有意思。
有很多人愤然指出,作协中有宋祖德和郭敬明之类,言下之意,金老一不小心掉进的作协是个泥潭。实际上中国作协是一个组织,只要是一个组织,就要发展会员,天经地义。发展的会员中当然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男有女,有丑有俊,但不能因为组织内成色有异,就认为组织不纯洁了。过去我们一直是以“纯洁”来衡量组织的,因此我们习惯于一个组织只讲一种语言,一个组织只做一个动作,一个组织只有一种思维,像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那样,最后只有一头叫“拿破仑同志”的猪是正确的。那种纯洁的组织现在看来,倒是怪异的。
有次和同伴在街上走路,看见对面走过一对男女,女人脸部扭曲,五官几乎挪位,而亲热地挽着她的男子是个标准的帅哥,同伴对我说,那个女的太可怕了,怎么偏偏就钓上个俊男?我看了一眼,确实有点不太协调,但我对同伴说,你对他们并不了解,他们之间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他们在一起不是为了别人看的。正如一把锁和一把钥匙,不是摆设,是为了开启的。
所以金庸尽可以选择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也尽可以选择金庸,只要没有谁逼着谁就好。更何况这跟婚姻一样,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离婚。童话大王郑渊洁不正闹着退出北京作协吗?
进进退退,退退进进,有进有退,有退有进。作协还是一潭活水。假如哪天彻底进不去,或者进去退不出来,那才不好玩呢。
拒绝戴套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让人误以为涉黄,其实这里说的“套”,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个,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虽然外形有些像,但实在是两码事。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去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这边在签,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2000本书签完,200,0个“套子”和“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评论家、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丁点好处,但塑封一拆,就没有一点用处了,“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雨披’的理由”。
其实,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环保”问题上做文章,我只是就书论书。
读书人都知道,买书的时候东翻翻、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质感”,才让他们走进书店,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段文字打动了你,你买下了它。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就没有买书的结果,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掉了脑袋,但留下诗句。可见古人是把“翻书”当作“读书”的代名词在用。
现在的书店里,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凭着感觉买书,除了重版书和名著以外,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起印一万册”而发愁,他们算计了一切,却越算丢得越多。因为他们以“社”为本,却始终不肯以“读者”为本。他们的理由是,读者会把书翻旧,破损率会高。其实自古以来,书都是这么翻的,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据我所知,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八成是很畅销的书,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吗?
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创造过“豪华书”,创造过“家装书”,现在又创造出“套中书”。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折腾读者,恐怕离自我消灭不远了。
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到那时候,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而是消极适应蒙昧,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
我做“星期五”
前日去“尚书吧”,见到吧里著名的“店小二”扫红,刚坐下,她走过来劈头问一句,你来啦,今天是星期五吗?我一愣,然后与她一起笑。
扫红之所以把我和星期五这么紧密地联系起来,主要是缘于我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要在中心书城主持一档“深圳晚八点”的文学对话,和深圳内内外外的作家们对话。所谓对话,其实也就是聊天,相当于扯闲谈,当然都是围绕文学扯开来。
而每次“晚八点”之前,又往往陪着作家们逛逛书城,逛着逛着,就到了24小时书店,累了就到尚书吧坐下来喝茶。以至于我的生物钟和星期五对上节律了。
想想这段周五时光,确实挺开心,每周都和一位作家对谈,仿佛古人等待远方友人来访。我想,在这个忙忙碌碌的城市,如此闲淡却频繁地会友,好像除我以外,怕也不多。
作家中有些熟识多年,有些神交已久,有些素未谋面,但基本上都是一见如故,三两句话就对上“暗号”。
星期五的对话虽然不热闹,但也不冷清,恰好是文学应有的氛围。我和作家坐于茶几两侧,对面还有一两百文学爱好者,足矣。大家谈论写作、阅读、生活,反正是始终有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