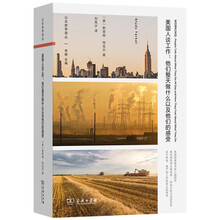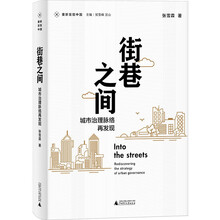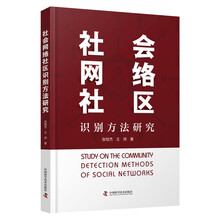我们要从事的社会科学,是一门实在的科学。我们要理解我们侧身于其中的且围绕我们生活的实在的特点——我们一方面理解它现在形态的个别现象的联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理解它们在历史上如此而非如彼地形成的根据。一旦我们试图思考生活直接面临我们的方式,生活便给我们呈现了“在”我们“之中”或“在”我们“之外”、依次或同时出现和消失的种种事物的绝对无限的多样性。一旦我们想要同样严肃地尝试详尽描述“单个现象”的所有个别的成分,那么在我们孤立地注意一个“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交换活动——时,且不必说想从因果制约性上来把握它,这个多样性的绝对无限性依然绝对丝毫无损地保存着。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实在的所有思想认识都潜在地依赖于下面的前提:每次只是这个无限实在的一个有限部分才构成科学探讨的对象,唯有它才应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性的”。但是,这个部分是根据什么原则被选择出来的呢?人们一再认为,文化科学中决定性的标志可能也在于某些因果联接“合乎规律的”重复。我们在现象的无限多样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到的“规律”在自身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必定——根据这种见解——只是实在里面合乎科学的“本质内容”:一旦我们无论是运用广博的历史归纳法证明一种因果联接的“规律性”乃系毫无例外地有效的,还是按照内在的经验使它当下澄明,它们自身或无数类似的情况就都将从属于以这种方式找到的公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