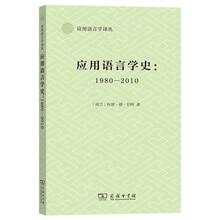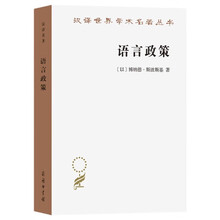第六版作者序:致中国读者<br><br> 我希望读者一开始就了解与本书相关的三个要点:一是符号学和符号论的区别;二是符号学探索的范围;三是参考文献如何区分历史层次,以消除传统格式的一个盲点,其根据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没有人在去世后还能继续写作。<br> (一)将符号学与符号论等同的谬说<br> 词语承载着人类理解力的历史。我们虽然发明了词语,却从未做到完全控制“词语的含义”或“意指”。因为一个词一经某人首次提出,随即不是成为无人理会的过眼烟云,就是被接受和应用。然而,应用的方式永远取决于语境,而语境总是不断变化的。<br> 因此,我们必须把设定的符号和惯用的符号区别开来。前者是只有人类语言沟通活动才有的,而且是这种沟通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后者是设定好的符号经过语言群体的运用所变成的东西——或迟或早,然而不可避免。经过设定的词语是象征性符号;正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观察到的,在使用过程中“象征会生长”,而且不可避免。 <br> 本书读者需要心中有数的是,自20世纪以来,有两个这样的象征在生长中已经不再受个别作者使用时的主观设定的支配。其中一个是“符号论”(semiology),另一个是“符号学”(semiotics)。设定活动虽然可以纠正习惯,可是从长远看,习惯却是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即使把这两个词在20世纪的用法当成一回事,二者之间的清楚界限也不难看到。这一点对于本书的任何读者来说都十分重要。<br> 在当今有关符号的讨论当中,“符号论”是一个有影响的术语,最早见于1916年出版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 de linguistiqne géuérale)。索绪尔认为,符号本身完全而且仅仅出现在人类文化的范围内,而且其中主要是语言符号。<br> “符号学”是这场讨论中的另一个有影响的术语,出现在1963年前后。当时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提出,符号绝不限于人类文化的范围,在动物的生命世界里同样随处可见。于是,他把“人类指号过程”(anthroposemiosis)与“动物指号过程”(zosemiosis)对举,前者指人类物种所特有的部分,后者泛指动物界的符号作用,从而使人类动物的意识与许多其他动物的意识发生交集。1981年,西比奥克时任主编的国际符号学研究会(IASS)的《符号学刊》(Semiotica)发表了马丁·克朗蓬(Martin Krampen)的《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一文。这篇论文首次提出,植物世界也有符号作用。通过这篇论文的发表,西比奥克为著名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r>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进展当中,在美国,皮尔斯的工作既有核心意义,又被边缘化。拥戴者们多年来以为皮尔斯的首选用语不是“semiotics”,而是“semeiotic”。后来这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对符号学的总体发展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直到20世纪末,西比奥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担当了组织、辑刊和撰著的主要角色,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如此。<br> 20世纪末期,“符号学”与“符号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指通过充分研究符号作用所获得的知识,后者顶多指对于在人类文化内部起作用的符号的研究,在最糟的情形下则仅表示符号作用只限于人类文化——这本来是索绪尔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时也使他成为现代哲学传统中的一位“观念论者”,即认为人类心智终究只能认识产生于心智本身的东西。<br> 西比奥克很早就用“以偏概全的谬说”的提法来说明符号论与符号学之别,意思是把仅限于人类语言和文化的符号作用错误地等同于全部符号作用。继西比奥克对这个谬说做出有效和明白无误的揭露之后,已经有不少试图消除其影响的努力。值此《符号学基础》汉译本出版之际,一个也许需要读者有明确意识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西比奥克揭露的这个“以偏概全的谬说”在当前思想文化界远未绝迹。 <br><br> 下面不妨以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的《符号学:基础概念》(Semiotics:the Basics)(基于名为Semiotics for Beginners的网站)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形。同类著作还有一些,可是也许都没有这一本如此离谱。这本书只谈符号学里索绪尔的追随者从事的符号论部分,所以书名本应直称《符号论:基础概念》。 如此错误地设想“符号学”是与现代唯名论的“观念之道” 一脉相承的,这就像皮尔斯所指出的,詹姆斯(WJames)和杜威(Dewey)以后的“实用主义”与唯名论一脉相承一样。与约翰·班索特(John Poinsot)的符号观相同,皮尔斯本人则以“经院哲学实在论”作为其“实效主义”观点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完整意义上承认存在的可知性:既包括不依赖心智的现实的范畴,也包括现实在人类指号过程内部的社会建构的维面。符号学之所以确定无疑地是后现代的,正是因为它超越了现代哲学在“认识论”当中(以及索绪尔在“符号论”当中)规定的限度:有关万物自身的知识,包括其存在的既先于又独立于人类文化的侧面。 <br> 如果文化内部的符号作用可以纳入更广泛的符号作用——后者把文化本身呈现为广阔得多的自然界当中的一个部分,为人类物种所特有——那么,眼下把文化符号学当成 “符号学本身”来谈论,便有使西比奥克所揭露的“以偏概全的谬说”接近“以偏概全的骗局”之嫌。钱德勒的书只是一例,任何一本这样的书其实都不单是书名究竟何谓的问题,而是事关如何在更广泛的“符号作用”——这是充分意义上的符号学主题——的内部,界定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领域。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符号作用”,而不是一个文化所创造的、作用也局囿于文化的有限的部分,规定着整个符号学探索,构成了符号学名下的广阔领域。<br> (二)物理指号过程:一种先于和不依赖于生命的符号作用<br> 符号作用的最奇怪的特点是涉及非存在(nonbeing)。在物理的因果互动当中,参与者必须都存在于当时当地。符号却无需如此。说谎和欺骗活动脱离了指号过程就无法实现,任何未来的发展也是如此,没有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就无从预见。意指作用必须有一个载体,通常叫做“符号”(sign)或者(皮尔斯所说的)“代现物”(representamen),才能把意指对象传达给一个第三方(无论是否某个人)。可是,被传达之物不一定实际存在;它传至的“第三方”也不一定实际存在。<br> <br> 这很奇怪,不过也正是指号过程的特别之处,是符号特有的作用或其“因果性”的特别之处。例如,大路左侧有一条通往树林的岔路,路牌上写着“前方有桥”。可是岔路上也许根本没有桥,或者真有一座桥,却无法通行。当我们把这些考虑转用于思考宇宙的时候,尽管我们知道宇宙在生命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然而我们很难不去考虑某种作用于引起宇宙变化的互动过程的“未来的影响”,这些互动过程将“仅仅是”无生命的苍茫大地逐步变成拥有一些先是能够支持生命,进而切实支持生命的区域。这样看来,就我们对于宇宙和生物的进化过程的理解而言,指号过程(即符号作用)正好补上了其中“缺失的环节”。<br> 这个“物理指号过程”(physiosemiosis)的理念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论证。它不仅伴随着生命物的指号过程(即“生物指号过程”),而且在宇宙中先于生命。 一些重要的变化将一个原本无生命的宇宙从“仅仅是”变成“多了点什么”,逐步接近生命登上宇宙舞台的起始点(见本书第六章的论述);这些变化当中已经包含了这种特殊的符号作用,从而大大改变了过去事件对于未来事件的相关性。不妨重申:这样看待指号过程为充分理解进化的宇宙提供了“缺失的环节”。<br> 在本书以前,这种充分意义的符号作用只有皮尔斯一人揣想过。直接导致本书写作的皮尔斯身后的学术研究证明,皮尔斯的核心主张——符号是一种不可简约的三价关系,在任何特定的指号作用发生时,每个价项无需独立存在——实际上早就提出来了,这个主张原是从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的著作到约翰·班索特(Poinsot,1589—1644)的符号学之间,有关符号的学说在拉丁时期取得的最高成就。<br> 在新近的文献里,符号学的这种最初的发展被称为“早期符号学说”(protosemiotics),它始于正式提出超越自然和文化之别去理解符号的思想家4世纪后期的奥古斯丁,并且在17世纪初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约翰·班索特1632年出版的《论符号》(Tractatus de Signis)。这部论著阐述了符号的三价关系的存在如何不仅超越自然与文化的分野,而且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内外之分。班索特在书中还阐明了符号的存在如何超越物理和心理两方面的主体性。可是,借用休谟(David Hume)的一个说法,班索特的符号学“被出版界当成死婴”,在拉丁语内被遗忘,在拉丁语以外也无人知晓,直至1985年才在双语版里除本文脚注提到的两篇以外,作者本人的著作均列于本书末的“参考文献”当中。——译者注重获刊行。<br> 本书不以历史为重点,而是从理论上把握完整意义上的符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符号学” 的专门知识[特别是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西比奥克身后]究竟是什么。理论上,符号学有别于符号论之处,不单是不限于人类物种所特有的文化,它同样从经验方面考察符号的作用,以便通过分析(而不是通过设定,如索绪尔学派所做的那样)确定符号的存在的形式内涵。<br> (三)消除文献来源的时间盲点<br>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参考文献的格式,即所谓“区分来源的历史层次”,它消除了思想文化界至今仍然容忍的一个有弊无益的“盲点”。这种格式在中国的第一次完整运用无疑是《符号学共时观:2010年景象》一文,载于2010年12月的《中国符号学研究》第4卷第2期9~113页。 <br> 基于“没有人在死后还能继续写作”这个简单的事实,美国符号学会(SSA)在第二届年会论文集《符号学1981》(Semiotics 1981)的“前言”里宣布了一种新的编辑格式。这种“美国符号学会格式” 在其后五年当中完成了所有细节, 1986年正式发表在《美国符号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上。这种格式与现有的标准格式——例如美国心理学会(APA)格式等——区别不是很大,除了关键的一点:它要求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被征引者的实际寿命和实际的时间位置。<br> 区分历史层次要求把“来源日期”和“访取日期”区别开来,前者必须而且只能是文本作者在世时的某一时间,后者是用来访取来源的译文或者出版日期。这两个日期可能是同一个,但当二者不同时,来源日期用于文本当中的征引,文末或书后的参考文献表则随后对来源日期和访取日期的关系做出解释。<br> 与例如美国心理学会格式等其他文献格式相比,参考文献已经区分了历史层次,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时期在文本内的作用,好比地质学家通过岩层能够看出地球的历史。区分历史层次的好处颇多,绝无弊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迫使作者和读者对历史语境具有或逐渐具有明确的意识,因为它在被利用的任何文本里都起作用。读者手中的这本书和上面提到的“符号学共时观:2010年景象” 一文都采纳了这种简单而具有根本性的文献格式的调整。<br> 继《符号学基础》之后,我又写过几部书,其中三部专门梳理了历史记录,回顾了符号学如何认识到三价关系在超主体性的符号的存在当中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得未来能够通过现在不断地重组过去事件与现时发展的相关性。<br> 其一是名为《奥古斯丁与班索特:早期符号学的发展》(Augustine & Poinst:the protosemiotic development)的研究著作。这本书涵盖了符号意识从4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在拉丁语中的最初的繁荣景象[我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纪哲学再定义:通观科学从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到班索特1644年逝世之间的发展》(Medieval Philosophy Redefined:The development of cenoscopic Science from the birth of Augustine in 354 AD to the 1644 death of Poinsot)篇幅要长得多,涵盖时期虽然相同,但是在完整的拉丁哲学的格局内勾勒了符号学的线索;我在此前2001年撰写的《理解力的四个纪元:对于从古代直到20世纪开端的哲学的第一次后现代主义考察》(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一书,也根据从公元前7世纪到21世纪开端的整个哲学史的格局,追溯了符号学的线索]。<br> 其二是《笛卡儿与班索特:符号与理念的抉择》(Descartes & Poinsot:the crossroad of signs and ideas),它论证了 “符号之道”如何被现代哲学的“观念之道”所遮蔽,直到皮尔斯那里才重见天日,再到西比奥克才获得普遍的承认,进而变成哲学的符号学发展的主流,为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思想文化做出贡献。<br> <br> 其三是篇幅不长的一部专著:《符号学共时观:2010年景象》John Deely,Semiotics Seen Synchronically:the View from 2010,Ottawa:Legas,2010,它以上文两次提到的发表于《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同名文章为基础[最后这部专著(或专文)特别梳理了20世纪创立的符号学的史实,符号学成为从现代民族语的思想文化界向后现代全球思想文化界转变当中的一门不可或缺的专题研究]。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书提供了一部符号学如何在20世纪“创立”的全面记录,苏珊·彼得里利(Susan Petrili)在“2008年度西比奥克研究员演讲” 中,把它正确地称为“一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多地属于‘我们的时代’的现象”[见《符号伦理学与责任》,载《美国符号学杂志》244(2008),148]。<br> 上述三点中的第一点充分展开之后就是索绪尔的“符号论”最初促成了20世纪对于符号的热烈讨论,这个现代时期的最富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规定了符号的研究范围,它既直截了当地附和文化与自然之分,又毫不妥协地局限于文化方面。因此,西比奥克才能把索绪尔的观点称为“以偏概全的谬说”。迪利、布鲁克·威廉姆斯(Brooke Williams)作者的夫人,也是符号学者。——译者注和费利西娅·克鲁兹(Felicia Kruse)1986年合编的名为《符号学前沿》(Frontiers in Semiotics)的论文集(布鲁明顿市: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充分论证了西比奥克的指责的完整含义;从自足的文化指号过程转入兼顾文化和自然的发展的指号过程之间,这部论文集被证明是一个分水岭。<br> 最后,我要向推荐本书的李幼蒸先生,特别要向愿意把它译成中文的张祖建先生,表达深切的谢意。身为哲学家,能够把这项研究介绍给中国人民,是我在生活中从未有过的荣幸。在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当中,中国人的重要性远非词语所能够表达的。符号学越是被人们理解,就越会蓬勃发展,从而使我们能够跨越文化的分野,实现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拥抱整个地球的人类的生存状态。<br> <br> 约翰·迪利<br> 美国艾奥瓦州迪比克市园景山庄<br> 2011年10月7日<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