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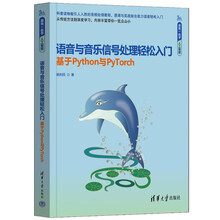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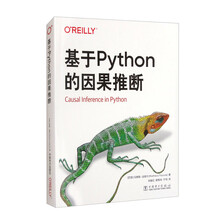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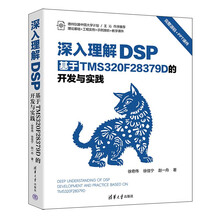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温州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温州市文史馆成立于2020年5月,目标是立足传统,面向未来,拓展学术研究视野。一年两集的馆刊,旨在通过研究和借鉴文史,讲好温州文化故事和发展故事,成为展示东瓯优秀文史成果的窗口。
浙学中坚:论永嘉学派在浙学中的历史地位
王 宇
重估永嘉学派在浙学中的历史地位,以下两个问题不可回避:永嘉学派在宋代浙学体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定位?在元明清三代,浙学主流已变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永嘉学派是否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呢?
本文认为,从浙学的形成历史看,宋代是浙学实现思想自觉的关键时期,而永嘉学派是宋代浙学的主力军,叶适是宋代浙学的最后一位领袖,也是宋代浙学的集大成者。南宋灭亡后,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成为思想主流,但永嘉学派仍保持了生命力,并在近代中国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浙学和宋代浙学
宋代,是浙学演进历史上分水岭式的关键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在宋以前没有人使用“浙学”一语。以宋代为界,浙学先后经历了从“自在的浙学”到“自为的浙学”两个阶段。自良渚文化以来,浙江大地上产生的所有文化现象和精神产品,固然可以统称为“浙学”,但此种观念的浙学只是强调了浙江这一地理属性,譬如东汉王充《论衡》这样的巨作虽诞生于浙江,但仍属于中原文化南传的产物,浙江这一地理属性与这些文化现象、精神产品内在的思想逻辑缺乏联系,名之为“自在的浙学”。
进入宋代,尤其是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浙学”这一术语批评两浙地区所流行的一种思想学术,斥之为“浙学尤更丑陋”“浙学却专是功利”。从朱熹的批评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浙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只有到了宋代,浙学才内生出了一种全国性影响的思想学术,浙学之“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观念,而是一种原创的、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瞩目。第二,“浙学”之“学”的灵魂是儒学,由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学术体系,浙学只有在儒学体系内发展出一整套独立的思想观点,它才真正获得自身稳定的内涵和清晰的边界。在宋以前浙江大地虽然出现了道教魏伯阳、天台宗智者大师等人,但没有人称其为“浙学”。
由此可见只有到了宋代,浙学才迎来了思想自觉的复兴,而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原创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浙学从“自在”走向“自为”的主力军。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宋代浙学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问题意识。
首先是在北宋中期,新儒学运动影响迅速扩大,全国各地“学统四起”,一些地域特色鲜明的思想学术传统和学者群体次第崛起。仁宗庆历二年(1042),新儒学运动的重要人物胡瑗(993—1059)受邀来到湖州讲学,将这股清新的变革之风吹到了两浙地区。全祖望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此时的浙学尚处于萌芽期,北宋哲宗朝所流行的几种区域思想学术主要是二程兄弟洛学、三苏兄弟蜀学、司马光朔学、王安石新学,竞相角逐,最终在徽宗朝以王安石新学胜出、垄断“道统”为结局。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与洛学(此时已经成为“程学”)竞争中节节败退,程学获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认可。但进入孝宗朝,朱熹、张栻、吕祖谦勠力同心,在隆兴至淳熙初年掀起了开展传播、研究程学的高潮。但是,随着程学复振运动的深入,在程学内部出现了自我改革的呼声,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程学的思想批评力量的问题上,吕祖谦与朱熹出现了微妙的分歧。吕祖谦更加重视程学北宋、南宋过渡之际缺乏“经世应务”能力的缺陷,并试图加以弥补;朱熹则更加强调在“内圣”的方向上完善程学的术语体系、逻辑体系。正是这一思想矛盾的萌芽和充分展开,导致朱熹形成了“浙学却专是功利”的价值判断,从而宣告了“自为的浙学”诞生。
二、永嘉学派是宋代浙学的中坚力量
(一)永嘉学派推动了吕祖谦为“宗主”的宋代浙学之定型。
当吕祖谦思考程学不能经世致用时,他发现了永嘉学派的奠基人薛季宣(1134—1174)正在实践改革二程理学的工作。吕氏在为薛季宣所撰写的《墓志铭》中,高度肯定他治学“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既有别于王安石一类的功利刑名之学,又避免了单纯内倾化所导致的“不足以涉事耦变”的弊端。同时,“公之学既有所授”,薛季宣是程颐再传;薛季宣早年在武昌为官的实践经验支撑了其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他的地理之学不仅是为了解经训说,更是为南宋当代军事斗争服务的兵要地志之学。薛氏对本朝制度律法极为娴熟,以至于同僚和下属不敢相信“其为儒者”,从而暗示南宋“儒者”普遍地不擅长制度之学。吕祖谦还指出,薛季宣并不认为佛教是理学面临的大敌,理学在南宋社会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如何从“道揆”走向“法守”、从“成己”走向“成物”。薛季宣的实践和主张,都给吕祖谦很大的启发,鼓舞他继续为改造二程理学而努力。薛季宣卒于孝宗乾道九年(1173),此时浙学尚在酝酿阶段,可以说薛季宣对吕祖谦的启发推动了浙学的最终成熟。
(二)永嘉学派用学理论证、经典阐释的方式,明晰了浙学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要旨。
认识到北宋新儒学不能经世致用,只是提出了问题和任务,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通过学术研究的实践去解决这个问题。吕祖谦去世后,浙学与程朱理学的矛盾公开化,而程朱理学又构建了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典体系,并对经典进行全新阐释,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浙学与理学对话论辩时,必须以学术研究的形式阐明浙学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要旨。而陈亮与朱熹虽然展开了精彩的“王霸义利之辩”,但他对经典阐释的路径兴趣淡薄,因此没能将浙学的基本思想用学术研究、经典阐释的形式加以展开论证,也没能将浙学的基本立场在学术辩论中固定下来。这一伟大的工作,是由永嘉学派,尤其是叶适完成的。
从薛季宣开始,永嘉学派就高度重视通过经典阐释、传播、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薛季宣对《尚书》《论语》《春秋》《礼记•中庸》等经典都有训释,并在《中庸解》中旗帜鲜明地强调学习客观知识的“自明诚”,否定了“自诚明”的直观顿悟的认识方式;陈傅良更是通过《周礼说》系统阐明了浙学改造南宋各种制度所要实现的“三代”制度典范,还通过《左传》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更是一部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专著,他通过对儒家经典、历史要籍、诸子百家的评点,提出了批评程朱理学心性思想、解构理学道统论的一系列全新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锐气和原创性方面与陈亮不相上下,而在学理阐释和经典引证方面更胜陈亮一筹。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浙学”自吕祖谦以后就分化成永嘉、陈亮、吕祖俭三支,相互之间没有思想上的共通性。在这三支中,功利倾向最严重的自然是陈亮:“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所谓陈亮“更粗莽”就是批评他没有学理化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全祖望还说,叶适做出了专业的学术贡献: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叶适通过经典阐释的论证方式,将浙学发展过程产生的“功利”思想进行合理的阐释,使之符合儒家经典的规范,只有这样,叶适才有资格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三,成为南宋思想学术界的第三极。
(三)永嘉学派代表了浙学思想的原创性和革命性的一面。
吕祖谦虽然是“浙学宗主”,但他的总体思想背景仍然是理学。他一方面致力于在理学内部改造理学、提升理学的思想冒险;另一方面又与朱熹通力合作,弘扬推广理学。理学的改造者与弘扬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思想创新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永嘉学派,尤其叶适,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探索,最终意识到了与朱熹在理论上难以调和(朱熹也是这样认为的),浙学的历史使命不是从理学内部发掘经世致用的因素,也不是补齐理学所缺失的经世致用的本领,而是要在理论预设层面上驳正理学,即理学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心性论思想。
永嘉学派早在薛季宣那里就注意批驳理学的核心思想——心性论思想。薛季宣撰写了论文《知性辨示君举》,提出了“性不可知论”,反对将“天命之谓性”作为儒学的功夫对象(认识对象);陈傅良(字君举)在继承“性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提出“道法不相离”,并批评理学视为圭臬的《尚书•大禹谟》“十六字箴言”受到了老庄思想的“污染”,其谬误在于否定以制度建设改造客观世界是“道”的主要实践形式。
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总述讲学大旨》中否定了理学“心包万理”的预设,指出“心”并不先天地具有真理,而只是一种认识真理、探索真理的能力;叶适批评理学以《太极图说》为中心所构建的宇宙论体系,是一个超出人的感官经验、违背常识、超越历史时空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佛教思想所“污染”;他断然否认了理学道统论谱系中曾子的传道者地位。这些批判和反思都直击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和要害,引起了理学派的不满。程朱理学的重要学者真德秀就批评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属于“放言”,这恰反映了永嘉学派探索真理的勇气。故此元代学者黄溍(1277—1357)认为陈傅良、陈亮、叶适虽受益于吕祖谦,但吕氏去世之后,“人自为书,角立竞起”,而叶适之学“无一合于吕氏”,就反映了这一点。叶适虽曾多次向吕祖谦问学,特别是孝宗淳熙五年(1178),他为了备考省试而在临安逗留了半年之久,其间向同在临安任官的吕祖谦问学,吕氏向他传授了关于《皇朝文鉴》的构思和逻辑,指出应该通过研究宋代的本朝史,揭示儒家的“治道”。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去世时,陈亮和一批吕祖谦门人恳请叶适继承吕学,被他拒绝。一方面是因为叶适顾虑吕祖谦门人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叶适感觉到吕祖谦对程学的反思和批判还不够彻底。
(四)叶适是宋代浙学最后一位领袖和集大成者。
吕祖谦开创浙学之后,永嘉学派、陈亮在他的指引下丰富和壮大了浙学。朱熹指出:“其学(指吕祖谦)合陈君举、陈同父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举为有所长,若正则则涣无统纪。同父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父之所长。”陈傅良(君举)、叶适(正则)和陈亮(同父)都是吕祖谦学术的继承者,但各自从不同方向发展了“浙学”,陈傅良主要研究制度,开创了“制度新学”,陈亮则在历史哲学领域与朱熹开展了“王霸义利之辩”,叶适被朱熹贬低为“涣无统纪”,乃是因为朱熹去世之前,叶适尚未完成对浙学的思想总结。
但是,吕祖谦于淳熙八年(1181)去世后,陈亮、陈傅良成为浙学的代表人物;绍熙五年(1194)陈亮去世,浙学的代表人物已经变为陈傅良、叶适;嘉泰四年(1204)陈傅良去世,此后二十年间,叶适成为浙学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利用晚年闲居的机会,系统总结了浙学的理论思考,进行了学理化的论证,整理了《水心外稿》《后总》,撰写了《习学记言序目》,同时继续讲学收徒,获得了广泛的思想影响。正是看到了叶适的这一巨大影响力,南宋末期著名学者黄震(1213—1281,字东发)在他的《日抄》中对《水心文集》进行了逐篇点评。他认为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确认为南宋思想学术的四大家,而叶适“混然四者之间”,遂为五大家:
愚按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即心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拄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则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尝明言统绪果为何物,令人晓然易知如诸儒者。
黄震明白地指出,所谓“独水心混然四者之间”,是说叶适虽然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却与朱熹、陆九渊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集,这是因为他对南宋思想学术所有重要的命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朱子学、象山心学、浙东学派都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重构。
三、元明清浙学充分吸收了永嘉学派思想和学术
叶适去世(1223)后,程朱理学成为官学,逐渐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永嘉学派乃至朱熹所批评的“专是功利”的浙学也在师徒授受的系统中逐渐失去了传承,元明清浙学的主流已经成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永嘉学派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印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永嘉学派被永远定格于南宋,那么它对元明清浙学乃至近现代浙江,岂非毫无影响?
实际上,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元明清浙学的发展历史,永嘉学派的思想观点、学术方法已经融入了浙学之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传承。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程朱理学对永嘉学派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
永嘉学派以“制度新学”“事求可、功求成”为号召,但是程朱理学并不完全排斥制度研究和对“事功”的追求。黄榦就曾说:“君举陈丈(陈傅良),于大经大本固难责以尽合,然闻其于制度考证亦颇有过人处,善取人者,亦资其长以益己而已。” “大经大本”是朱子学理论的核心——心性学,但永嘉学派的“制度考证”也是值得朱子学借鉴汲取、丰富自我的有益成分。作为朱子学在宁宗、理宗朝的代表人物,魏了翁早年与叶适有一定的交往,全祖望推测:“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所谓“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反映了魏了翁在早年对“道学”的接受,是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进行的。如传承陆学的“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1144—1224)也曾问学陈傅良:“永嘉陈公傅良,明旧章、达世变,公与从容考订,细大靡遗,其志以扶持世道为己责。然自始学,于义利取舍之辨甚严。”所谓“然自始学,于义利取舍之辨甚严”,指袁燮学问虽然从陈傅良那里吸收了“制度新学”的营养,但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与之大异其趣。朱熹的弟子滕璘(1154—1233)也曾问学于陈傅良:“公既从朱子,得为学大方,异时至永嘉,又从故中书舍人陈公傅良,问《左氏》要义,陈公告语甚悉,大略谓:‘左氏本依经为传,纵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驳经义,非自为书。’且告以六经之义,兢业为本,公佩服焉。”魏了翁、袁燮、滕璘虽然最终都归本于朱子学或象山心学,但陈傅良的“制度新学”也成为他们吸收的思想养分。以上事实证明朱子学与永嘉学派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南宋末年福建朱子学者林希逸(1193—1271,福清县人)说:“自薛常州、陈止斋以周官六典参之诸史,讲求古今,损益异同之故。又考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欲正体统,联上下,使内朝外廷必别,大纲小纪必严,与夫取民、制兵、足国、厚下之法,随事条理,期为长久,以今准昔,而不为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林氏指出薛季宣、陈傅良不但善于考证三代名物、舆地、制度,且注意总结吸取北宋立国以来制度变迁的得失;这些研究不仅是为了复原历史的原貌(“好古之迂”),而是要在复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整理出足以解决南宋当代财政、政治、军事、社会危机的制度安排,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元代朱子学者程端礼(1271—1345)曾这样评价薛季宣:“余谓士之谈诗书而略事功,其来已久,遂使俗吏嗤儒为不足用……余少读薛常州《行述》,窃欣慕之,盖其学本濂洛,其自得之实,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莅官文武,应机处变,政无巨细,靡不曲当。”
程端礼批评从南宋后期开始,读书人中流行的“谈诗书而略事功”的偏向,削弱了朱子学改革客观世界、经世致用的功能;而他注意到薛季宣“学本濂洛”,担任过多个军政职务,政绩卓著,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可以纠正朱子学末流蹈空好高之弊。
一些明代学者虽然承认 “浙学”是与朱、陆鼎足而三的,但认为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特征。如浙江学者章懋(1436—1521)说:
为学之道,居敬、穷理不可偏废。浙中多是事功,如陈同父、陈君举、薛士龙辈,只去理会天下国家事,有末而无本;江西之学多主静,如陆象山兄弟专务存心,不务讲学,有本而无末。惟朱子之学知行本末兼尽,至正而无弊也。
章懋将浙学和陆学整合到了朱子学体系之中,即朱子学是全面的、自洽的,而前二者是片面的、不自洽的,但浙学、陆学之片面并非他者,而是朱子学的多面性中的一面,因此朱子学的丰富性和普遍适用性,也需要浙学和陆学彰显。
由上可知,叶适去世后漫长的六百年间,永嘉学派虽然已经停止了发展,也不再产生新的领袖人物,但它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就仍然受到了程朱理学的重视,虽然这种重视是以批判为前提的,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永嘉学派已经融入了元明清浙学的发展进程之中,由此得到了部分的传承。
(二)永嘉学派通过近代复兴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永嘉学派主张“事求可,功求成”,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将儒学的价值观运用实践于现实生活,实实在在地增进人民福祉,改革社会弊端,起到了纠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末流流于空疏清谈弊端的积极作用,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永嘉学派的独特价值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重视。在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为代表的一批晚清知识群体的努力下,在晚清掀起了复兴永嘉学派的高潮,由于这次近代复兴,永嘉学派的文化基因被人为地激活了,实现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和创新性表现为:晚清温州知识群体大量刊刻传播永嘉学派文献,为研究永嘉学派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并大力宣传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秉承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宗旨,积极发展近代实业、创办新式学校、设立各种新式社会事业,对温州乃至浙江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孙诒让等学术大师的倡导和呼吁,永嘉学派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重视和瞩目,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南宋中期的辉煌。更重要的是,这次近代复兴直接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温州人精神的孕育和定型,是赓续永嘉学脉的中继线和里程碑,应该得到高度肯定。二〇一九年七月,时任省长袁家军同志来温考察调研期间,肯定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明确指出应加强永嘉学派研究。
四、 结语
今天我们重估永嘉学派在浙学中的历史地位,绝非出于乡梓情深的羁绊,为古代乡贤争地位、抢功劳,而是力图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学理论证,恢复永嘉学派在浙学发展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事实证明,永嘉学派是宋代浙学的中坚力量,叶适是宋代浙学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明确了这两个关键的历史地位,才能正本清源地研究浙学历史,追溯当代温州人精神的源头活水,从而为建设新时代文化温州注入精神动力。
专题
纪念叶适诞辰八百七十周年
王宇 浙学中坚:论永嘉学派在浙学中的历史地位
陈增杰 叶适与永嘉四灵诗派
洪振宁 永嘉学派的重振复兴
孙邦金 永嘉学派和新时代温州人精神
孙金波 叶适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 雷 等 永嘉学派思想核心要义及其启示
前辈风雅
章方松 感怀恩师杨勇先生
卢礼阳 一份未兑现的汇款单
——纪念百岁长者黄鸿森先生
刘时觉 随师二载 受益一生
——忆陆芷青师
张思聪 东瓯代有才人出 长领风骚七十年
——新中国温州剧作家群掠影
章震天 张红薇郑曼青章左平往事
方韶毅 王服周事迹
东瓯史谭
王长明 温州三次抗击日军的国际国内背景初探
叶 建 五四时期温州进步期刊三种
张声和 永嘉学人群体的一次受挫
谢作拳 林从炯与《承德府志》
文化纵横
俞为民 南戏研究与“温州学”
钱志熙 谢客去后的永嘉山水
——谢灵运山水诗风及其在温州诗风中的传承
丁俊清 温州古民居建筑的“理水”文化
艺术天地
戴宏海 《十里红妆》创作谈
何元龙 书法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