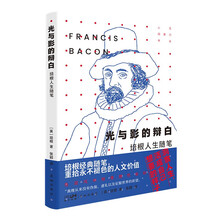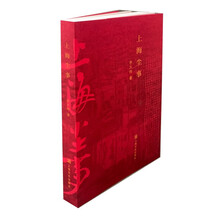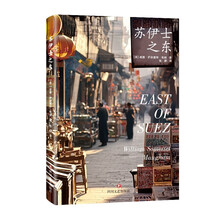忆杭州
九年前的这些日子——
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行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嫌避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惯用的对象。
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的,浮动着水蒸气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
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温热是什么呢?
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
我曾徘徊于桥头,曾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
就在那时,我开始读了屠格涅夫,而且也爱上了屠格涅夫。
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我如今依然很清楚的记忆到,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落下了冰冷的眼泪。
杭州是可咒诅的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了杭州。想起它时,只是充满了懊丧与埋怨。
大海的浪,冲去了我心中的那种结郁,旅行给我以对于世俗的忘怀。
我所住的不再是那中世纪式的城市:机械与人群的永不休止的呼嚷,使我忘却了孤独,生活影响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审美的观念,我开始使自己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我能用鲜明的对照的彩色来涂抹我的画册了。
几年后,我曾几度在旅行中经过杭州,每次经过时,也不知由于畏惧呢还是由于憎厌,心底里像有一种隐微的声音催促着我:“不要停留呵,不要停留呵……”就像我是从它那里逃亡了似的。
今年九月,我又在杭州住下了。
它仍是使我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
我仍是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
西湖没有什么变化——迷蒙,飘忽,柔软。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
战争并不曾惊动他们,他们——杭州的市民,有多少曾为民族的命运顾虑过呢?
我的绘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西湖,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
十一月,敌人已从金山卫登陆,杭州在军事上已极重要,但除了单纯的军事的调防之外,负责当局仍不曾在民众运动上开放过——个人的地位与荣禄使他们忘却了整个民族的厄运。
*后,我教书的学校,没有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就借了盘费,离开杭州。
不久,听说杭州的居民已逃走,省政府与省党部都早已迁至金华,而那在临走前两天还劝人们“高枕而卧”的《东南日报》,也改在金华出版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上遇见了一个背了包袱的警察,他说是从杭州逃出来的——他走时,城里已三四里路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那时,敌军还不曾攻嘉兴。
今天,我在想念着杭州……
我不能违心的说我爱杭州,它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挤满了偏窄的、自私的市民,与自满的卑俗的小职员,以及惯于谄媚的小官僚,和专事奉迎的文化人,他们常以为自己生活在无比的幸福里,就像母亲似的安谧。在他们,从不曾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祸患,真实的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恐怖着灾难,但他们不会反抗,而且也不想反抗,*后,他们逃跑了——却仍旧不曾放弃掉偏窄,自私,自满,谄媚与奉迎;所放弃的是农人们给他们耕植的土地,和工人们给他们建筑在土地上的房屋。
今天,敌人已迫近了杭州,明天或后天,我们的英勇士兵,将以温热的血与肉,作着保卫杭州的防御战了。
杭州,从来迷漫着和平的烟雾的西湖,将要迷漫着战争的烟火了。
或许,敌人的残暴的脚步,很快就踏遍了整个的杭州;或许,敌人的兽性会把西湖的一切摧毁;或许,西湖的血会染成紫红的颜色……
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杭州欣喜,因它愈为怯懦的、无耻的人们所弃,却愈为英勇的、坚强的战士们所爱,它将在敌人与我们间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
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我以安慰自己的心情,默诵着这为我*近所爱的话:“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