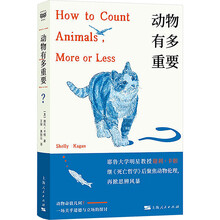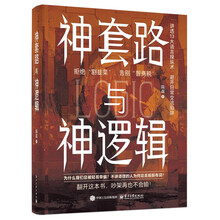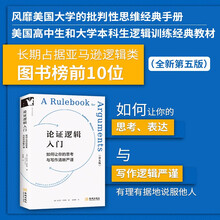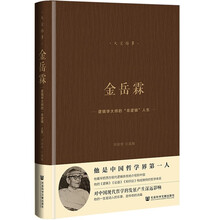《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杜威承认实在的人化,但是没有否认主体经验以外的自在存在,并不“否认人类在世界中进化以前的地质的和宇宙的世界”,他称之为“死的存在”:“这些死的存在既不等于境况的客观内容,即思想由以产生的工艺的、艺术的或社会的境况的客观内容,也不等于待认识的事物,即作为知识对象的事物。”这种直接的存在由于与人隔绝,是不可言传的,既未知又不可知,“我们既无庸对自己说些什么,也无法对别人说些什么”。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一个逻辑假设。因为主体之外的实体是否存在,在杜威看来,是一个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死的存在”也就没有实质性意义。它起一种消极的逻辑限制作用:有了这个逻辑前提,才可说明人与世界的互动和生成。换言之,“死的存在”是人们用外推法推出来的,是合逻辑的。“从逻辑上讲来,我不必对那些年代进行任何宇宙论上的玄想,因为根据我的理论讲来,任何关于这些年代的命题都是属于本特雷所谓外推法(extrapolation)性质的……这种外推法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是一种外推法。”这与皮尔士理论内可知的、独立的实在概念是有差异的。杜威对实在作如此规定,既避免了皮尔士实在观的前后矛盾之处,又稍稍矫正了詹姆士意识流中的心理主义偏向。
杜威如上对实在的解释,对胡适产生不小的影响。和杜威一样,胡适也在人化的意义上讨论实在:“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和人处于一定关系中的对象,人和实在正是在实践、活动中贯串、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主体的能力(本质力量)在实在中展开和充实;另一方面,实在又在主体的活动中被改造。和杜威的思路类似,胡适在讲宇宙时,也把它看作是生成的、进化的,“是一篇未完的草稿,正在修改之中,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但是永永没有完篇的时期。理性主义的宇宙是绝对平安无事的,实验主义的宇宙是还在冒险进行的”,“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用一句古语来概述,即人能弘道(实在),非道弘人。
所以宇宙或实在可以说是由主体创造的,并留有主体的印迹,这印迹当中自然夹带着不同主体的目的和计划。因而对各个主体来说,根据他们自己的期望和认知结构,实在在他们眼里就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意义和内涵。胡适说:“感觉之来,就同大水汹涌,是不由我们自主的。但是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轻,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是大不相同的。”这里“心目中的实在”乃是就意义世界而言,客观对象诚然不会随个人意志的变化而转移,但是对象(实在)所呈现的意义却与每个主体(诗人和植物学者)的感觉、兴趣、意向有着紧密的关联。对象的意义对能欣赏此对象的人才敞开,它也正有待主体去发掘,而主体的认知背景(结构)、目的和期望,又制约着认知实在(对象)的深度和广度。这表明观念中的实在(意义世界)具有个性特点:各人看到的宇宙大不相同,实在在不同的认知主体那里展现出各异的意义与个性。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化,实在的意义也会因之而日益丰富起来。胡适的“实在一个性”说,可以视为对杜威的“实在一意义世界”说的一种发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