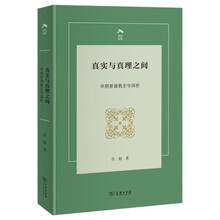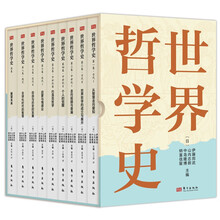“功”“利”乃墨家哲学之根本意思。《墨子·非命上》云:“子墨子言日:‘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此三表中,最重要者乃其第三,“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凡事物必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者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此估定。<br> 人民之富庶,即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故凡对之无直接用处或对之有害者,皆当废弃。所以吾人应尚节俭,反对奢侈。故墨子主张节用,节葬,短丧,非乐。<br> 一切奢侈文饰,固皆不中国家人民之利,然犹非其大害。国家人民之大害,在于国家人民之互相争斗,无有宁息;而其所以互相争斗之原因,则起于人之不相爱。故墨子以兼爱之说救之。以为兼爱之道不惟于他人有利,且于行兼爱之道者亦有利;不惟“利他”,亦且“利自”。墨子之《兼爱篇》纯就功利方面证兼爱之必要。此墨家兼爱之说所以与儒家之主张仁不同也。<br> 天下之大利,在于人之兼爱;天下之大害,在于人之互争;故吾人应非攻。墨子非攻;孟子亦日:“善战者服上刑。”但墨子之非攻,因其不利。孟子之反对战争,则因其不义。观孟子与宋烃辩论之言可见矣。(《孟子·告子下》)宋烃欲见秦楚之王,说构兵之“不利”,而使之“罢之”。孟子则主张以仁义说秦楚之王。宋烃不必即一墨者,但此点实亦孟子与墨子所以不同也。<br> 墨子虽以为兼爱之道乃惟一救世之法,而却未以为人本能相爱。墨子以人性为素丝,其善恶全在“所染”(《墨子·所染》)。吾人固应以兼爱之道染人,使交相利而不交相害;然普通人民,所见甚近,不易使其皆有见于兼爱之利,“交别”之害。故墨子注重种种制裁,以使人交相爱。墨子书中有《天志》、《明鬼》、《非命》诸篇。以为有上帝鬼神之存在,赏兼爱者而罚交别者。上帝神鬼及国家之赏罚,乃人之行为所自招,非命定也。若以此为命定,则诸种赏罚,皆失其效力矣。故墨子“非命”。<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