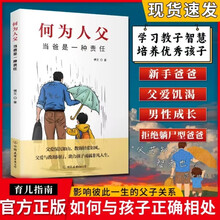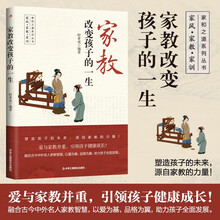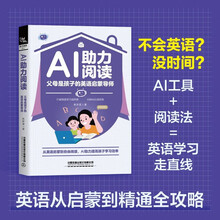第一章 教育的目的
本章导读
蒙台梭利在本章针对新教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以及具有批判精神的思考。首先蒙台梭利评论了现代科学对新教育学,也就是对科学教育学的诞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意大利学者在缔造科学教育学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以圣方济各重建天主教的心路历程为例,阐明了建立科学教育学不仅仅需要科学技能也需要科学精神。其次,蒙台梭利表明,如果要建立科学教育学,那么我们必须培养培养新教师的科学精神,而不仅仅是培养他们的科学技能。最后,蒙台梭利进一步论述了如果科学教育学要在学校诞生,那么必须允许儿童在学校自发表现,这样新教师才能通过观察学生以孕育科学教育学。藉此,她抨击了旧式学校对儿童的肉体和精神残害。其中,蒙台梭利尤其指出奖励和惩罚都是对儿童精神的压制,因为人类的一切胜利和一切进步都源自人类内心的力量。
一、现代科学对教育学的影响
我并不打算把本书写成一本关于科学教育学的著作。我计划呈现的这些并不完整的记录只是提供了一个教育实验的结果。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实验结果为把那些新的科学原则付诸实践开辟了道路。近年来,这些新的科学原则正在革新教育工作。
过去十年来,针对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可谓众说纷纭。随着医学的进步,这些讨论已经超越了纯理论猜测的阶段,而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实证性结果上。从韦伯 (Weber)、费希纳 (Fechner)到冯特 (Wundt),生理心理学或者实验心理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新科学。生理心理学或者实验心理学似乎注定为新教育学提供奠基性的准备,这正如过去形而上学心理学为哲学教育学奠定了基础一样。形态人类学(morphological anthropology)已经应用到儿童的身体研究中,这也是新教育学成长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几年前,一位著名的医生在意大利创办了一所“科学教育学学校”(School of Scientific Pedagogy),目的在于为新教育运动培养教师,使之能投身于这场业已被教育界意识到的教育运动 中。这所学校在两三年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所学校之所以大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得到了杰出的人类学家塞吉 (Giuseppe Sergi)的热情支持。塞吉30多年来一直都在意大利教师中诚挚的、不遗余力的传播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文明。他曾经说过:“今天,人类的社会世界迫切需要重建教育方法。我们为此而奋斗也就是为人类的复兴而奋斗。”塞吉的教育著作已经汇集成卷,命名为《教育与训练》(Eduzacione ed Instruzione, Pensieri)。他在本书诸多讲演的摘要中都鼓励这个新教育运动,同时他表示自己相信:我们所渴望的人类复兴之路在于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导,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塞吉表示:“多年以来,我都在为一种关于人类训练和人类教育的理念而奋斗。我对这种理念思考得越深刻,就越觉得这种理念是正义的和有用的。我的理念就是:为了建立自然的和合理的教育方法,根本之道就是把人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从而进行大量正确的和合理的观察。我们主要是在幼年时期对人进行这种观察,这是奠定个体教育基础和文化基础的时期。”
塞吉的威望足以让很多人确信:如果我们拥有了关于人类个体的知识,那么教育人类的艺术就会自然而然得到发展。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导致了塞吉追随者之间的思想混乱:他们对于塞吉思想的理解,有些人囿于咬文嚼字,而另外一些人则夸大其词。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塞吉的追随者混淆了对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和对学生进行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既然对学生进行实验研究这条道路是对学生进行自然和合理教育的通途,那么通过实验研究,我们对学生所进行的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了。因此塞吉的追随者直言不讳地把教育人类学命名为科学教育学。因此,这所所谓的“科学教育学学校”只教会自己的老师掌握人类学的测量工具、掌握使用触觉测量器以及学会收集心理学的数据资料,认为如此一来,一支新科学教师的队伍就装备完毕了。
二、教育学的现状
应该说,意大利在这场新教育运动中可谓与时俱进。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各国在人类学和心理教育学的基础上,都在小学开展了诸多的实验研究,希望籍此从人类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中找到学校复兴的道路。然而进行上述这些实验研究的种种努力鲜有教师参与其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实验研究是医生来主持,他们的兴趣往往是在自身的医学领域而不是在教育领域。他们通常企图通过实验得到一些对于心理学或者人类学发展有贡献的内容,而非试图把他们的工作和研究结果导向形成一个我们长期以来致力探索的科学教育学。简而言之,人类学和心理学从来也没有致力于学校的儿童教育问题,也从来没有致力于科学地培养出达到真正的科学家水平的教师。
事实情况就是如此,学校的实际进步需要从实践上和理论上真正融合这些现代发展趋势。这种融合应当把科学家直接导向学校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提高教师水平,把他们从较低的智力水平提高到时代所界定的科学家水平。克里达洛(Credaro)在意大利创办的教育大学(University School of Pedagogy),为了实现这个特别具有实践意义的理想正在发挥作用。这所教育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教育学较低的地位,使教育学从哲学分支的从属地位中脱离出来,从而成为一门有着显赫地位的独立科学。教育应该像医学那样,具有广泛以及多样的比较研究的领域。
毫无疑问,最有可能成为教育学分支的学科就是教育卫生学、教育人类学以及实验心理学。
坦白说,意大利作为龙勃罗梭 (Lombroso)、德·乔瓦尼(De Giovanni)和塞吉的祖国,在这场运动的组织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三位科学家看作是人类学发展新趋势的奠基人。龙勃罗梭开辟了研究犯罪人类学的发展道路,德·乔瓦尼拓展了医学人类学的发展道路,而塞吉则在教育人类学中独辟蹊径。非常幸运的是,这三位科学家都是他们各自领域内公认的权威,他们都在科学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他们不仅仅培养了一大批有勇有谋的追随者,而且他们还为启蒙大众思想,使其接受所倡导的科学复兴做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请参看我的《教育人类学》一书)。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我们祖国当之无愧的骄傲。
然而,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以及文明的利益。那么在如此伟大的事业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全世界。同时,在一个如此重要的伟大事业中,无论谁,哪怕只是做了一点点的贡献,甚至哪怕他们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都值得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人类对他们致敬。因此,在意大利通过小学教师和督学的齐心协力,众多“科学教育学学校”以及人类学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个城市涌现出来。尽管这些学校和实验室如“昙花一现”,还没有成形就夭折,但是它们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些学校和实验室不仅仅高举了它们所宣传信念的旗帜,而且为那些有思想的人们打开了探索之门。
我们毫不讳言,这些尝试都是不成熟的,而且源自人们对仍在发展过程中的新科学的浅薄认识。然而,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都诞生于反复的失败和不完美的成就之中。当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St. Francis of Assisi)在幻觉中见到“主”,并听到主的召唤——“方济各,重建我的教堂吧!”方济各认为:上帝所说的正是他身跪其中的这座小教堂。因此,他立刻开始了重建这座小教堂的工作,手扛肩挑石块打算重建那些已经倒塌的残垣败瓦。直到后来他终于领悟了上帝的启示——他的使命就是要用劳苦大众的精神重振天主教。但是,无论是一开始如此天真地认为上帝仅仅是让他重建小教堂的方济各,还是后来成为一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的方济各——他如此奇迹般地领导人们获得了精神胜利,都不过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个人。所以,我们朝着一个伟大目标而努力,我们是这个集体和整体中的“沧海一粟”。我们的追随者将会修成正果,因为这些追随者的前辈曾信奉这个目标并且为此付出努力。那么,就像方济各认为上帝就是让他重建小教堂而搬运石块一样,我们也曾经相信:只要把实验室这些硬梆梆、笨重的石块搬到破败、残垣断壁的学校,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建学校。我们曾经指望唯物论和机械论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就像方济各指望他肩上的花岗岩石块能够帮助他重振天主教一样。
如此一来,我们被引入歧途狭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生机勃勃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的后代,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自己从这样的歧途困境中解放出来。
三、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
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来培养教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就算我们已经尽最大可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教导教师掌握人类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那么我们也不过是造就了一些“机器”,其用处极其让人怀疑。
比如,真正的科学家并不是那些在物理实验室知道如何去操作里面所有实验仪器的人,科学家也不是那些在化学实验室知道如何敏捷娴熟地以及小心翼翼地控制各种化学反应的人,科学家更不是那些知道如何在显微镜下制作观察标本的人。事实上,很多实验室助手在实验技能中的动手能力要比那些科学名家强,但是这些助手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家。我们把科学家这顶桂冠授予那些把实验视为发现生命真谛和解释生命奥秘手段的人。在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们对大自然的神奇奥秘满怀着热爱和忘我的激情。真正的科学家并不是动作灵巧熟练的仪器操纵者,而是自然的崇拜者。真正的科学家的外在特征就是类似于笃守宗教教规的虔诚的教徒。真正的科学家就像是中世纪的苦行僧,他们忘掉了红尘俗世,天天“浸泡”在实验室里面废寝忘食,因为他们不再考虑自己,完全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在这些真正的科学家中,有的人由于长年累月使用显微镜而致盲,有的人由于狂热喜爱科学试验而给自己接种肺结核病菌,有的人为了弄清楚霍乱的传播途径而去接触患者的粪便,有的人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而冒着生命危险去试验那些易爆的化学剂。这就是人类科学家的精神。大自然也受到这些真正科学家艰苦卓越工作的感召,乐意向这些科学家坦露自己的秘密,向他们的辛勤劳动赋予科学发现的桂冠。
在此,的确存在一种远远高于科学家“机械技能”的科学家“精神”。当“精神”统帅“机械技能”的时候,科学家就达到了他成就的高峰。当科学家达到这个高峰的时候,他不仅仅能收获自然的新启示(revelation),而且也会得出纯理论的哲学概括。
我相信,我们要培养的更多是让教师具备科学家的科学精神而不是具备科学家的机械技能。也就是说,教师教育的方向应该是培养具备科学精神的教师,而非培养仅仅具备机械技能的教师。例如,当我们在考虑如何科学地培养教师时,我们就希望能够引导教师尝试和特定领域以及学校建立联系,我们还希望能够唤醒他们,让他们意识到科学精神为他们打开了通向更广泛、更大可能性之门。换言之,我希望能够唤醒教师的心灵和智慧,唤醒教师灵魂深处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兴趣,从而使教师热爱自然。那么他们就能够理解一个人在准备好实验并等待大自然给他启示时,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了!
实验仪器就好比字母表,如果我们要解读自然的话,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去操纵这些实验仪器。正如一本揭示了作者最伟大思想的书籍,它用字母符号组成了书籍的外表或者文字,那么自然也是如此。自然通过各种实验仪器给予了我们无限的启示,向我们揭示了自然的奥妙之处。
实际上,我们必须使教师成为自然精神的崇拜者和阐释者。正如那些学会了拼读所有字母,而且有一天发现自己还能读懂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的思想。由此看来,两者之间有着天渊之别,而且从前者到后者要经历漫长的学习过程。
然而,我们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我们似乎认为,那些掌握了拼写课本中所有单词的儿童已经知道如何去阅读。实际上,这些儿童是能说出商店门口的招牌以及报纸的名称,也能读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个字。如果这些儿童走进图书馆,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认为他们也能读懂他所看到的那里面所有书籍的含义。如果我们真的让儿童尝试一下的话,那么儿童很快就会发现“只会进行机械阅读是一点都不管用的,必须回到学校重新学习”。那么原先我们通过教授教师掌握人类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来进行教师培养,道理也正是如此。
四、真正的教育者善于向儿童学习
这么说吧,让我们设想一下下面的情形:教师不经过科学训练就可以使其观察自然现象的这种兴趣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这样一种教师培养还是不够的。实际上,教师的特殊使命并不是观察昆虫或者细菌,而是观察人。教师并不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研究人,也就是说,教师并不像昆虫学家研究昆虫那样,在昆虫早上醒来以后就追踪它们的活动。教师是在唤醒人的智力生命中研究人。
我们希望培养教师研究人性的兴趣,而这种研究人性的兴趣必须具备下面的特点:那就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并不存在于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以及其研究对象之间。如果一个科学家没有作出部分的自我牺牲,那么他也不会爱上自己所研究的昆虫或者化学反应。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似乎是指那些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他们几乎就是殉道者。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远不止是温情脉脉,它是如此简单而又无处不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具备这种爱,这种爱并不是那些受过专门教育的阶层的专利。
为了说明第二种培养教师的方式,也就是教师的精神培养,让我们不妨这样来设想一下:当耶稣基督的第一批信徒听到他谈到还有一个比世间任何王国都要伟大得多的天国时,虽然这些信徒是如此虔诚,但是他们仍然天真地向基督发问:“主啊,请告诉我们吧!谁是天国里最伟大的人呢?”基督听到了这个发问,他慈爱地抚摸着一个孩子的脑袋,这个孩子以虔诚和好奇的目光看着他,基督回答道:“谁能够变得像这些孩子一样,那么谁就是天国最伟大的人。”那么现在让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假设听到了基督的回答的人当中,有一个信徒满怀着激动和崇拜的心情把这个回答牢记在心。他怀着一颗充满着尊敬、爱戴、庄严的好奇和渴望之情的心灵,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伟大的精神境界。他开始细心观察孩子的种种表现。即使是让这名信徒在挤满小孩的教室里面进行观察,他也不会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新教师。但是如果我们设法把科学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基督徒的虔诚及热忱都植入到教师的心灵中,那么我们就会培养出教师精神。教师就会向儿童学习以完善自我,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者。
让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例子来审视教师的态度。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位精通观察技术和实验技术的植物学家或者动物学家,他为了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研究“某种真菌”而要出去旅行。这位科学家先在野外进行了观察,然后又借助显微镜和所有实验设备进行研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以最细致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工作。实际上,这位科学家就不仅仅理解如何去研究自然,而且还精通于所有现代实验科学为他的研究所提供的一切方式。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吧!如果这样一位科学家因为个人原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被指派到某所大学来主持科学研究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对膜翅目昆虫做进一步的开创性研究。假设当这位科学家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玻璃盖子的盒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美丽的蝴蝶,这些蝴蝶被大头钉钉住,一动不动,而翅膀是展开的。那么这位研究人员会说,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但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素材。这些装在盒子里面的昆虫是小男孩玩扑蝶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到处追逐蝴蝶,并且用网把蝴蝶抓住。这样一些材料对于实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而言毫无用处。
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科学方法培养教师,然后把他派遣到某所公立学校去工作,那么可能会出现和上述科学家非常类似的情况。因为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儿童就像是那些被大头钉死死钉住的蝴蝶,他们个性的自发性表达受到压制,就好像是行尸走肉。他们被钉在各自的座位上、各自的课桌旁,伸展着他们无用的翅膀,这双翅膀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无聊乏味以及毫无意义的知识。
那么,这也就是说仅仅培养我们的教师仅仅具备科学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准备那些可供他们进行观察的学校。只有这些学校必须允许儿童自由和自然的表现自己,科学教育学才能诞生在这样的学校。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五、学校必须允许儿童自然地表现自己
谁也不能妄下定论说,这样的原则已经存在于教育学中和我们的学校中。事实上,卢梭引导下的某些教育工作者曾经为儿童的自由振臂高呼,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原则和含糊不清的愿望。但是实际上教育工作者并不了解关于儿童自由的真正含义。教育工作者往往把自由的概念等同于鼓励人民反抗奴隶制的这种自由概念,或者说把自由的概念等同于“社会自由”的概念。尽管“社会自由”是一个更高位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总是受到限制。“社会自由”总是意味着“雅各布的天梯” (Jacob’s ladder)中的一个阶梯。换句话说,“社会自由”意味着部分的解放,这是一个国家的解放、一个阶层的解放或者说是思想的解放。
然而,必须注入教育学中的自由概念则带有普遍性。当19世纪的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生命的诸多手段时,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自由。因此,如果旧式教育学预见了或者模糊地表达了在教育学生之前要对学生进行研究、要让学生在自发性活动中自由表现的原则,那么实际上旧式教育学可以获得这样一种不明确的以及难以表达的直觉,这还是要归功于上个世纪实验科学的贡献。这并不是一个进行诡辩或者辩论的案例,但足以说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如果谁说自由的原则已经融入了今天的教育学,那么我们一定会笑话他:他就像一个小孩子,站在一个装着被死死钉住的蝴蝶的盒子前,却坚持说“蝴蝶是活的,而且它们还会飞呢!”这种作茧自缚的原则仍然充斥在教育学中,而且,同样的原则也充斥在学校中。我只要给出一个明显的例证就可以了——学校中那固定的桌椅就是明证。这是我们今天仍然继续着早期唯物主义科学教育学的错误的一个典型例证,我们错误地试图把热情和精力都用于搬运那些无益的科学石块,我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搬运这些科学石块就可以重建我们那些破败不堪的学校。
六、固定的桌椅:作茧自缚
一切都是如此安排的!当儿童非常合适的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桌椅本身就迫使他误以为这样的座位设计是既卫生又舒适的。凳子的搁脚板和桌子的安排,使儿童在学习时绝不能随意地站立起来,因为分配给儿童的空间只够他直挺挺的坐着。教室里面的桌椅板凳按照这样方式日臻完善。这就是所谓科学教育学的崇拜者所设计出来的、具有示范意义的科学桌子。不少国家还为他们的“国家书桌”而自豪骄傲。如此一来,在激烈竞争当中,形形色色的机械成为专利。
毫无疑问,这些板凳构造的诸多之处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人们借助于人类学来测量人体和判断年龄;借助于生理学来研究肌肉动作;借助于心理学来考察本能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借助于卫生学来防止儿童的脊椎变形。这些书桌的确是科学的,它们是根据人类学对儿童的研究成果设计出的。正如上述所说,这是人们把科学机械地运用到学校的一个案例。
这些科学板凳的发展史说明了学生一直以来都受到一种管理制度的压迫,在这种制度的支配下,学生即使天生健硕和腰杆笔直,也有可能会变成驼背!从生物学的视角看,脊椎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和最古老的骨骼组成部分,是我们身体中最强韧的部分。经过原始人时期和大地雄狮、和猛犸殊死搏斗,继而又在采石炼铁中经受沉重劳动考验的脊椎,竟然在学校的压迫之下弯曲了!
我们难以了解的是,所谓的“科学”竟然会致力于帮助学校完善各种奴役学生的工具,而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日益高涨的社会解放运动的曙光,竟然没有一丝一缕照耀到学校。
七、学校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教室中的儿童在毫无卫生保障的条件下学习,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身体发育,甚至迫使他们的脊椎都变形了。而我们对此的反应却是为他们的板凳提供“外科整形手术”。这就好比我们为矿工提供腹带或者说是为饥肠辘辘的工人提供砒霜。
前不久,一位自认为在学校的所有科学革新运动中与我志同道合的女性,洋洋自得地向我推荐一件学生穿的矫形衣或者说是紧身衣。她发明了这个玩意儿并以为藉此可以解决板凳的问题。
医学外科还有其它治疗方法可以解决脊椎变形问题,据我所知还有“器械矫正”和“定期悬挂法”。所谓“定期悬挂法”就是把学生的头部或者肩膀定时吊起来,用人体的体重帮助他慢慢把脊椎拉直。在学校里面,以桌子形式出现的“器械矫正”得到了极大的赞同,更进一步的是,如今还有人提出了通过紧身衣来把学生的脊椎拉直。难道这不是在提醒我们,何不给学生开设一门关于悬挂疗法的课程吗?
上述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人们把科学方法机械地运用于日益衰落的学校产生的必然结果。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解决学生的脊椎变形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他们不必被迫整天长时间地保持一种有害的姿势。学校需要争取的是这种自由,而不是着眼于板凳的构造。
八、儿童的精神受到的伤害
我们应该想到,孩子在这样一个就像是囚禁犯人的人造环境中学习,导致了他们的脊椎可能发生变形,那么这对他们精神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呢?当我们谈论到要拯救工人时,人们总是认为首先要解决那些工人最明显表现出来的痛苦,例如贫血和疝气。但是人们却没有想到那些遭受任何形式奴役的人们都要承受内心折磨的痛苦。如果我们所说的通过自由来拯救工人阶级,仅仅是指解除工人外在形式的痛苦,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相当明白,当一个人因为劳动而使心血消耗殆尽或者使肠组织日益衰弱,那么他的精神也必然受到压抑,他会变得麻木不仁或者有可能被扼杀其中。奴隶的道德堕落是人类进步的沉重负担,如果人类要奋勇前进,那么人类首先要解除这个精神负担。所以拯救人类的精神比拯救人类的肉体更加重要。
那么面对如何教育儿童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我们太理解教师所面临的困境了。在普通课堂中,教师必须通过“满堂灌”的方式才能把那些支离破碎、干巴巴的知识硬塞到学生的脑袋里。为了成功完成这个枯燥乏味的任务,她发现自己必须用纪律约束学生,让他们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以迫使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是,奖励和惩罚就成为教师的“家常便饭”,这有效地帮助教师迫使那些被判为听众的学生的身心都处于一种受限制的状态。
九、奖励和惩罚对精神的压制
的确,今天人们已经认为废除鞭笞和习惯性打骂是有用,正如奖励变得随随便便而不那么郑重其事了。这种局部的改良是我们科学所提供的另外一种支持,它支撑了日益衰落的学校在苟延残喘。如果大家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么这种奖励和处罚简直就是灵魂的“板凳”,这是对人类精神的奴役。然而,这些科学所提供的支持并没有减少“畸形”,而是制造“畸形”。奖励和惩罚所激发的努力都是被迫的或者说是不自然的,所以我们当然无法谈及奖励和惩罚会带来学生的自然发展。赛马骑师在跳上马鞍之前会塞给马一块糖,马夫用鞭子抽打马匹、通过缰绳的张弛使马对他所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但是,这两种情况都绝不会让马像在草原上自由奔驰时那样壮观!
那么在教育中,人类应该给人类戴上枷锁吗?
坦白说,我们可以认为,文明人就是指戴上了社会枷锁的自然人。但是如果我们放眼眺望人类社会的道德进步,我们会看到如下情形:枷锁总是在一点一点的松开。换句话说,我们会看到自然或者生命在逐渐走向胜利。奴隶的枷锁让位给仆人的枷锁,而仆人的枷锁让位给工人的枷锁。
一切形式的奴役都在渐渐地趋于颓败和灭亡,甚至连对女性的性奴役也是如此。文明的历史就是征服史和解放史。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到底处于哪个文明发展阶段?如果奖励和惩罚真的有好处的话,那么这种好处对于我们人类进步而言是否必要?如果我们的确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那么采用这种形式的教育可能就会把我们的下一代拉回到更低级的发展水平,而不是引导我们的下一代继续进步。
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府各个部门与其大量雇员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类似于学校的这种情况。政府雇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了国家的普遍利益而工作,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或者看到他们的工作能“立竿见影”地回报国家,为国家带来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使国家能够维持伟大的事业,而且使整个民族都因此获益。对政府公务员而言,直接的回报就是步步高升,正如孩子在学校里面升级一样。一旦个人看不见自己工作的伟大目标,那么他就像孩子在学校里面被留级一样——被降到低于自己实际水平的班级。他就像是一个奴隶,他的某些权利被欺骗剥夺了!他作为人类的尊严被降格了,他被降格为一台必须要加油才能继续运转的机器,因为机器本身并没有生命的活力。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例如追求华服或者奖章,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刺激,只不过是照亮其脚下这条黑暗荒凉的小路的一道短暂的亮光而已。
我们在学校里面采用同样的方式奖励儿童。政府公务员因为害怕不能获得升迁,而被迫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法逃脱,被迫从事单调无聊的工作。这和学生因为害怕不能升级而被迫读书的情形如出一辙。上司对雇员的斥责和老师对学生的责骂非常类似,上司更正雇员马马虎虎起草的文件和教师给学生做的很糟糕的作业打分数也是雷同的。总而言之,这种比较的结果就是两者非常相仿。
但是如果政府部门不按照符合国家的伟大事业这种方式进行工作,贪污腐败就会滋生。这就是人类的伟大事业在雇员内心消失的结果,是雇员只顾眼前利益的鼠目寸光和急功近利的结果,这都是他们想方设法谋取奖励和逃避惩罚的结果。而国家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系,这是因为更大部分的政府雇员都能保持公正廉明,抵制滥用惩罚和奖励,他们跟随着不可抗拒的诚实正直的历史洪流滚滚前进。这就像在社会环境中,生命战胜了贫困和死亡,并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一样。所以自由的这种本能就能扫除一切的障碍,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正是个人无所不在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经常蕴藏于灵魂深处,并且推动着世界的进步。
但是那些真正以人类事业为工作的人,那些真正为人类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人,从来也不会被那些微不足道的所谓“奖励”所引诱,也不会被那些渺小的所谓“惩罚”所畏惧。如果在一场战争中,一支身强力壮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只不过是为了升官晋级、捞取军衔或者勋章而战斗,或者说因为害怕受到军法处置而作战;而与之作战的军队则是一小撮侏儒,但是他们心怀对祖国的热爱,那么胜利将属于后一支队伍。如果一支军队已经丧失了真正的英雄主义的精神,那么奖励和惩罚不过是“门面功夫”,最终将导致军队的腐败和怯懦。
人类的一切胜利和一切进步都源自人类内心的力量。
十、人类一切进步都源自内心的力量
因此,如果一个年轻学生,他立志以终生从事医学事业为己任而努力学习,那么他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为了继承遗产或者获得美满的婚姻或者其它任何物质利益而进行学习的话,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专家或者伟大的医生,而且世界将永远也不会因为他的工作而前进一小步。那些需要这些刺激的人,最好永远也不要成为医生。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爱好和特定的工作,这些爱好和工作虽然平凡普通,但一定是有用的。而奖励体系可能使人背离自己的天职,而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使他徒劳无功,并且迫使他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如果这样,那么发自人类内在本性的活动就可能被扭曲、贬低,乃至是泯灭。
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世界在进步,我们必须鼓励人们取得进步。但是进步总是来自新生事物,这往往不是人们能够预料到的,也得不到任何奖励。相反,往往是新生事物的领导者为此而殉道。上帝不允许诗歌诞生于诗人对于在朱庇特神殿 (Capitol)被授予桂冠的这种野心追求中。一旦这种争名逐利的念头进入到诗人的心灵,那么诗人必将江郎才尽。当诗人淡泊名利的时候,诗歌才会从诗人的心灵“喷涌而出”。就算诗人摘取了桂冠,他也会觉得这种奖励毫无意义。真正的奖励在于诗人通过诗歌揭示了自己获得胜利的内心力量。
然而,的确存在一种赋予人类的外在奖励。例如,当演说者看到听众的表情随着他所激发的情感而发生变化时,他体验到了一种极大的快乐,这是一种只有当一个人在被爱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的快乐。我们的快乐是触动人们的心灵以及征服人们的心灵,这才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回报的奖励。
有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我们觉得自己置身于世界伟人之林。只有继续保持心灵宁静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幸福的时刻。这种幸福时刻的来临也许是因为得到了爱情,或者收到儿子送来的礼物,也许是来自一项伟大的发现,也许是来自一本书籍的出版。此时此刻,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地位更高的人了!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有人得到授权而来给我们颁发勋章或者奖励,那么这个人就是我们获得真正奖励的十足破坏者。这时,我们正在消失的幻觉会大声呵斥:“你是谁?谁说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人?谁还能凌驾在我之上授予我这个奖励呢?”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来说,奖励只能是天赐的!
就惩罚而言,一个正常人的灵魂是通过充实自己而达致完美的。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惩罚总是以压迫的形式出现的。对于那些生长在罪恶之中、本性恶劣的人来说,惩罚也许能发挥点作用。但是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他们无法阻止社会的进步。刑法以惩罚威胁我们,以防止我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诚实。但是我们并是因为害怕法律而变得诚实。如果我们没有烧杀抢掠,那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是因为我们生命的自然本性在引导我们前进,引导我们超越和避免那些卑鄙和罪恶的行为。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真正的惩罚是使人丧失关于个人力量和个人尊严的意识,这是人类内在生命的源泉。这样的惩罚往往落在那些春风得意的成功者身上。当我们认为那些人正被快乐和幸运所包围时,他们可能正在遭受这种形式的惩罚。我们往往看不到威胁到自己的真正惩罚。
那么在这个方面,教育可能有所作为。
塞吉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人类社会迫切需要重建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我们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是为全人类的复兴而奋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