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平与性格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在20世纪已经成为只有专家们才去研究的对象,因此大多数近年来获得声誉的哲学家只在他们的同事中间闻名。然而维特根斯坦的名声却远远超越了哲学的界限。在不治哲学的人们当中,提及他的名字的次数多得惊人,听到他的名字的场合也各自不同,同样令人惊讶。在许多人眼中,他被认为是20世纪哲学的典型代表,好像他不仅在其著作中而且在人格上都体现出哲学本身的面目:难解而深邃。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他著作中的内容常被人随便取来当作警句。这些内容之所以被人这样使用,是由于其文体风格和结构的适宜,也因为似乎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智慧。
许多当代哲学家认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外行人对他的评价就由此而来。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仍然要由历史来决定;同行人的判断并不一定永远正确。然而不管结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维特根斯坦的生平和思想无论如何都是非比寻常的。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出生在维也纳,在家中排行第八,最为年幼。他的父亲是一位实业家,也是奥地利最富有的人物之一;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宅院是维也纳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
维特根斯坦家族父系和母系历代都以家道殷实和教养良好著称。他的祖父是来自黑森的一位富有的犹太羊毛商。他改信基督教中的新教,娶了一位维也纳银行家的女儿。其后不久他便把经营中心转移到维也纳,在该地他和妻子成了艺术赞助家。他们让儿子卡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接受花费昂贵的古典式教育,但是卡尔拒不从命,十七岁离家奔赴美国,有两年靠在饭馆服务以及教小提琴和德文课为生。回到维也纳后他开始学习工程学。除了继承的遗产,他在几十年间由于成功经营钢铁工业而增添了大量财富,跻身奥匈帝国最重要的实业家行列。他在过了五十岁不久便退休,用一些时间给维也纳报刊撰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尽全力鼓励全家从事文化和音乐活动的是维特根斯坦的母亲莱奥波尔迪娜。她也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同施蒂里亚的地主乡绅有着亲戚关系。她的音乐兴趣颇为浓厚。受她的邀请,勃拉姆斯和马勒是家中常客;在她的鼓励下,维特根斯坦的兄长保罗成了一名音乐会钢琴演奏家。保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一只手后,拉威尔和施特劳斯参与为保罗写出独手演奏的协奏曲。维特根斯坦本人也具有很好的音乐天赋。成年后他曾自学吹奏单簧管,但是他最突出的音乐才能却表现在全凭记忆用口哨吹奏出整篇乐谱的能力上。
莱奥波尔迪娜·维特根斯坦信奉罗马天主教,所以维特根斯坦也是在这种宗教信仰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宗教是他一生始终强烈关注的主题。有好几次他曾认真考虑去当修道士。然而他的宗教观点却不是正统的,到底是什么信仰他也从未讲出。在他的著作中透露过一些与此相关的暗示。
也许是由于自己切身的经验,卡尔·维特根斯坦的教育观点很是奇特。他让自己的孩子都在家里受教育,课程全由他自己安排,直到十四岁为止。这项计划并不成功。到了维特根斯坦该上学的时候,他竟进不了维也纳的高级中学(相当于文法学校)甚至实科学校(相当于现代中学),因为他达不到所要求的标准。最后他通过了林茨一所省立实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在那里上学的还有一个同龄人阿道夫·希特勒。维特根斯坦在该校度过了三年不愉快的时光,1906年离校时并未取得升进大学的资格。这是一次挫折,因为他曾有在维也纳跟博尔茨曼学习物理的志愿。然而他一直表现出工程学方面的天资,这是他父亲的专业;据说他在童年就制作出一种缝纫机的模型,证明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因此他的父母便将他送进柏林-夏洛滕堡的一所工艺学院。
维特根斯坦在那里生活得也不愉快,三个学期之后便离开了这所学校。然而他却对航空工程产生了兴趣,这是他未来职业的一条最新发展途径。他于1908年前往英国,当年夏天在德比郡靠近格洛瑟普的高空大气层研究站进行风筝飞行试验。当年秋季他进了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
维特根斯坦的名字留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上有两年之久,尽管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欧洲大陆。在曼彻斯特停留后期,他正致力于设计一种在桨片尖端装有喷气嘴的螺旋桨。他对这种设计所涉及的数学问题产生了兴趣,接着又转向数学本身,最后则被关乎数学基础的哲学问题所吸引。他问自己认识的人关于这门学科可以读些什么书,有人便让他去读罗素的《数学原理》。该书对维特根斯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前他所读的哲学书很有限;他读过叔本华的某些著作,此外就很少了。罗素这本书使他了解到逻辑和哲学的最新发展,促成这些发展的正是罗素本人和戈特洛布·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对这些思想极感兴趣,决心进行研究。1911年他到耶拿大学面见弗雷格,把自己的一篇文章交给他看,请求指导。弗雷格建议他到剑桥师从罗素。因此维特根斯坦便在1912年早些时候到了剑桥,注册入学。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只待了五个学期。然而这却是一段对他成长影响最大的时期。他同罗素讨论逻辑和哲学,后者在当时写的一封信中讲到他时说,“(他是)继摩尔之后我遇到的最有才能的人”。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很快便不再是师生关系,虽然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戴维·平森特在日记中说,“很显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信徒之一,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教益”。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得到教益的影响并不全是单向的。
维特根斯坦很喜欢旅行。1913年他同平森特第一次去冰岛,然后又去挪威。挪威深深吸引了他,这一年晚些时候他自己又返回挪威。他在靠近肖伦一个农庄的偏僻角落自己修建了一间小屋。除了一度去维也纳短暂停留过圣诞节之外,他在此一直居住到1914年夏天。他把住在小屋内的时间专用于研究逻辑。G.E.摩尔曾来此探望他,并在停留期间记录下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代表了后来发展为维特根斯坦第一本著作《逻辑哲学论》的研究进程之最初阶段。
第二章 早期哲学
在本章中我将讨论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评析维特根斯坦这本书的主要学说会使他的后期哲学容易理解得多。
第2、3两节专讲《逻辑哲学论》本身。第1节说明几件背景事实,它们将使《逻辑哲学论》更容易理解。本章结尾(第4节)则就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对其他哲学家产生的影响作出一些论述。
第1节的背景描述虽然旨在为讨论《逻辑哲学论》作一般性的准备,却特别是为刚刚接触哲学的读者而写的。它谈到逻辑和哲学中的某些专门概念,后者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将以直截了当的方式阐述这些概念。
1. 目的与背景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讲明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即要表明哲学问题可以通过正确理解语言如何起作用而得到解决。他的说法就是当我们理解了“语言的逻辑”时,我们就将解决哲学问题(《逻辑哲学论》第3-4页)。这确实是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的中心思想,代表了其早期与后期哲学中一脉相承的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逻辑”的看法在两个阶段中有着明显的不同,后期思想就建立在对前期某些最重要思想的否定上。
正如刚才所说,维特根斯坦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他的目标是解决哲学问题,他想通过显示语言怎样起作用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理解语言会解决哲学问题正是《逻辑哲学论》所要阐明的,这也正如他的后期哲学以不同方式所做的那样。我们不久便将讨论这个阐述过程。首先,我们必须弄清“哲学问题”这个短语表示什么意思。
人们可以将哲学描述为这样一种努力,即澄清和尽可能回答一系列根本性的和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我们想从总体上全面理解自己和所居住的世界的时候。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存在与实在、知识与信念、理性与推理、真理、意义以及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问题本身的形式是:什么是实在?事物存在的本原是什么?什么是知识,我们怎样得到知识?我们怎样确知我们关于知识的主张不是全盘错误?什么是正确推理的准则?什么是合乎道德的正当生活和行为方式,为什么?
哲学问题无法用经验的方法解决,例如通过使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进行观察,或者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它们是些概念的和逻辑的问题,要求进行概念的和逻辑的研究。几千年来有大量的才智投入这种澄清和回答哲学问题的工作。某些哲学家试图建立解释性的理论,有时内容非常详尽,范围也很宏大;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试图靠耐心的分析和批评去澄清和解决个别问题。几乎所有在哲学史上有过贡献的人都一致认为上述问题——存在、知识、真理、价值——极为重要;至少从古典时期起就有的哲学争论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基础展开的。
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则逆流而上。他认为哲学的正当任务不是去关注上述问题,因为照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由于误解语言而产生的一些虚幻问题。他说,哲学的正当任务是澄清我们的思想和话语的性质,因为这样一来传统的哲学问题就会成为伪问题并从而消失。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包括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就是以这种方式致力于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的。
《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思想是认为语言有一种深层逻辑结构,理解了这种结构便能发现清楚表达和有意义言说的界限。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看,其重要性在于可说的东西就是可想的东西;所以人们一旦明白了语言的性质并从而明白对什么可以进行清楚和有意义地思维,人们也就看清了语言和思想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它们便成了无意义的东西。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意见,传统的哲学问题正是在这个超越意义界限的领域中产生的,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企图说出不可说的东西——在他看来也就是打算思想不可思想的东西。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出这个论点,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这一说法:“可以说的,都可说清;不可说的,只可不说。”(《逻辑哲学论》第3页,并参看命题7)维特根斯坦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对这个主张作了更充分的表述:“(《逻辑哲学论》的)主要论点是关于什么是命题(即语言)可以表述的(也就是可以思想的)和什么是命题不能表述而只能揭示的;后者我认为是哲学的中心命题。”
维特根斯坦这些主张的重点在于表明哲学的正当任务是“除了可说的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完全无关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要说,然后在另外有人想说出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就向他证明他没有将意义赋予他的命题中的某些符号”(《逻辑哲学论》6.53)。但是这个消极的结论并不是事情的全貌,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像伦理学、美学、宗教以及“人生难题”(《逻辑哲学论》6.52)这类问题并非由于本身没有意义而被排除;而只是在打算对它们有所说时才产生没有意义的东西:“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它们通过自身得到显示。它们是神秘的东西。”(《逻辑哲学论》6.522)在这里可能做到的只是“显示”而不是“言说”。维特根斯坦有时会说到《逻辑哲学论》“未曾写出的更为重要的后半部”,意思是说《逻辑哲学论》没有说出的东西指明了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该书从语言界限之内显示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道:“伦理的东西好像是由我的著作从内部界定的……今天许多人喋喋不休谈论的东西我都通过在我的书中不予言谈加以限定。”
因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讲明语言是怎样发生效用的,目的就在于确立上述这些论点。讲得更具体些,他的任务是揭示语言的性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说明意义怎样附着于我们所断言的命题。因此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讲述命题是什么以及构成命题意义的又是什么上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就等同于确定出思想的界限;因为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研究前者也就是研究后者。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这个特点,因为它至关重要。
除非知道一些有关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哲学背景,否则人们不会正确理解他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法。这个背景就是逻辑和哲学的发展,大多要归功于弗雷格和罗素的著作;它们早在《逻辑哲学论》出版前几十年间便已出现,维特根斯坦在于剑桥师从罗素期间便从后者那里获知。因此我将从一些有关的特征讲起。
便于首先讨论的一个问题涉及哲学中的命题概念,因为下文将经常出现关于命题的说法。暂且将一些复杂的情况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一个命题就是某种被断言或被主张应视为真的说法,例如“这张桌子是褐色的”,“这本书是讲维特根斯坦的”,“正在下雨”。但是命题不应与用来表述命题的句子相混淆。一个句子是任何语言中合乎语法的一串字词,由某个人在某一时间和地点写出或说出。一个句子只需要遵守它所从属的语言的语法规则就能成为句子,它并不一定还要“有意义”:类似“绿色的思想凶猛地睡着”这样一串字词尽管没有意义却仍然算是句子。与此不同,一个命题是在有意义且不无聊地使用一个句子(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陈述句)时所断言的内容,因此命题与句子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区别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说出或写下的不同的句子可能都在说相同的内容,即表达相同的命题;而不同的人在相同或不同的场合所使用的相同句子却可能是在叙述不同的内容,即表达不同的命题。这里有一些实例:“it is raining”, “il pleut”, “es regret”, “下雨”,分别来自英文、法文、德文和中文,但都表达相同的命题即“正在下雨”。这就具体说明了第一种情况。相反,当我说“我头疼”和你说“我头疼”时,相同句子的不同使用说出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即表达两个不同的命题)。这就具体说明了第二种情况。
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应该将命题视为用一个句子(或者一组同义的句子,不管语种相同还是不同)所表达的思想。而另一些哲学家则说命题是句子的意义或者是在人们知道、相信、记起或希望某件事情真正发生时心中显现的客体——例如,如果杰克相信吉尔爱吉姆,那么依照这种看法,杰克的相信行为的客体便是“吉尔爱吉姆”这个命题。这些提法并不相互排斥;也许命题可以同时包涵所有这些提法。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问题面前停下来——稍后会对命题的性质另外作进一步的考察,就目前而言这个简述已经够用了。现在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中,命题是说出的或写出的思想的表达式;因此在这里我们的兴趣并不涉及英文、德文或中文的句子,而是在使用这些句子时所表达的思想。
如上面所述弗雷格和罗素的著作所带来的哲学发展是与理解《逻辑哲学论》有关的重要背景知识。开始讲述这些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便是观察罗素在一篇有名的逻辑分析文章中所处理的一个问题。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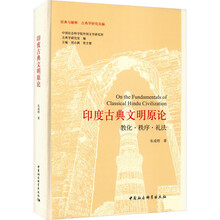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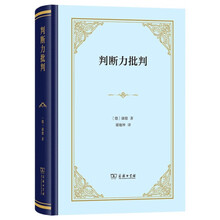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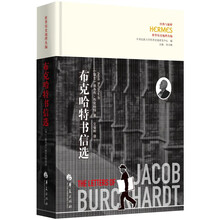



——《卫报》 雷蒙德·塔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