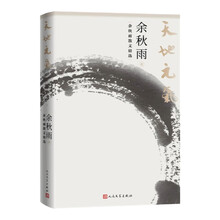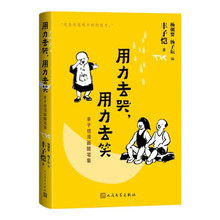菌子
每年的四月和七月,我都特别想回家乡去。
四月,漫山遍野开满了索玛花。
七月,菌子吃得了。
充沛的雨水过后,云南人民就要开始一场舌尖的盛宴和冒险了。
“七八月份的云南人民,总在生死离别之间。”
街头巷尾,聊的都是菌子:
“今天又买到点鸡枞和干巴。”
“这么大朵?安逸哦,赶快拿回去炒嘛,下午就不好吃了。”
“要得。你中午来不来唻?”
“我今天有点忙,忙完了再说!——新鲜的海椒要不要?我给你扯点拿过去。”
“好久不见,老表。”
“今年又中大招了,二麻,二麻,医院住了两天。”
“你娃还是注意着点,不要把命出脱了。”
“晓得,晓得。”
“我家今天做菌子火锅,你给来吃?”
“走嘛!怕死不是共产党!”
捡菌子,这个“捡”字,又轻松,又美好。
我从小就觉得,能够在山上捡到菌子的人,都是不一般的奇人。反正从小到大,我上山多次,也到处留意观察,一次菌子都没有捡到过。
夏天,在雨水过后的第二天,太阳一照,菌子就特别多。
上山拾菌的人一般都知道“菌子窝”在哪里。他们早早上山,去往神秘又熟悉的地方,扯掉用树枝搭建的“伪装”,惊喜地发现又一次能满载而归了。
核桃菌、青头菌、黑羊肝、白羊肝、干巴菌、牛肝菌、奶浆菌、鸡枞、松茸,一个个新鲜俊俏,根部还沾着泥土,让人垂涎欲滴。拾菌人把它们小心地聚拢,背到市场售卖。
我们小时候,又肥又大的鸡枞,一大把才卖十块钱。有时候,遇到那种菌伞张开过度,有些破败,或有蚂蚁爬过的,一两块就能买到一大堆,拿回家做菜可以吃到饱。吃不完的,用油炸成鸡枞油,吃面的时候,挑一点来拌着,美得很。
好的菌子,我们家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新鲜的青椒和大蒜炒,那味道鲜香脆嫩,爽滑可口。吃在嘴里,简直不能再幸福。
菌子
每年的四月和七月,我都特别想回家乡去。
四月,漫山遍野开满了索玛花。
七月,菌子吃得了。
充沛的雨水过后,云南人民就要开始一场舌尖的盛宴和冒险了。
“七八月份的云南人民,总在生死离别之间。”
街头巷尾,聊的都是菌子:
“今天又买到点鸡枞和干巴。”
“这么大朵?安逸哦,赶快拿回去炒嘛,下午就不好吃了。”
“要得。你中午来不来唻?”
“我今天有点忙,忙完了再说!——新鲜的海椒要不要?我给你扯点拿过去。”
“好久不见,老表。”
“今年又中大招了,二麻,二麻,医院住了两天。”
“你娃还是注意着点,不要把命出脱了。”
“晓得,晓得。”
“我家今天做菌子火锅,你给来吃?”
“走嘛!怕死不是共产党!”
捡菌子,这个“捡”字,又轻松,又美好。
我从小就觉得,能够在山上捡到菌子的人,都是不一般的奇人。反正从小到大,我上山多次,也到处留意观察,一次菌子都没有捡到过。
夏天,在雨水过后的第二天,太阳一照,菌子就特别多。
上山拾菌的人一般都知道“菌子窝”在哪里。他们早早上山,去往神秘又熟悉的地方,扯掉用树枝搭建的“伪装”,惊喜地发现又一次能满载而归了。
核桃菌、青头菌、黑羊肝、白羊肝、干巴菌、牛肝菌、奶浆菌、鸡枞、松茸,一个个新鲜俊俏,根部还沾着泥土,让人垂涎欲滴。拾菌人把它们小心地聚拢,背到市场售卖。
我们小时候,又肥又大的鸡枞,一大把才卖十块钱。有时候,遇到那种菌伞张开过度,有些破败,或有蚂蚁爬过的,一两块就能买到一大堆,拿回家做菜可以吃到饱。吃不完的,用油炸成鸡枞油,吃面的时候,挑一点来拌着,美得很。
好的菌子,我们家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用新鲜的青椒和大蒜炒,那味道鲜香脆嫩,爽滑可口。吃在嘴里,简直不能再幸福。
还有一种,是当地彝族人的做法,用火烧。把菌子烧熟之后,撕开成条状,再把青椒烧熟,撕开,把它们聚拢放到一个木碗里,放上几颗剥好的蒜粒,再用一根木棒来舂,蒜粒被舂碎,和辣椒、菌子融合在一起,撒点盐,倒入山泉水……这样做出来的菌子,有火烧过的一点点煳焦味,又辣又鲜,吃过一次的人,都不会忘记。
当然,在云南,菌子还可以炒糊辣椒。炒腊肉、炒火腿、凉拌、炖鸡汤、油炸、做火锅……不管是什么做法,都是很美味的。
为了安全,菌子除了要买常见、常吃的之外,一定要做熟,熟到透才能放心吃。
广为流传的“用肉眼辨别,好看的不要吃”,和“多放大蒜,蒜变了颜色不要吃”,这两种说法经过很多次验证,都是不可靠的。
要记住,丑的菌子,也有可能让人中毒哦。
头晕,发烧,“看见小人人”的幻觉,是最常见的中毒反应。
有一次,我们院,有一家人吃菌子,吃着吃着,全家都跑了出来,说厨房里有条怪物。
还有我舅,有一次吃黄牛肝没煮熟,出现幻觉了,跑出去,见人就喊:“我是一只孔雀你给晓得?”
前两年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位母亲,因为误食“见手青”,中毒之后,看见了逝去的女儿……此后的每一年夏天,她都会吃很多很多的“见手青”。
这让人心碎。
冰粉
燥热的夏季,热浪滚滚。
不戴帽子、满头大汗的骑车少年。
出来买菜的主妇。
从油腻的饭馆里钻出来,直接暴露在炎炎烈日下的男人。
他们都奔冰粉摊子而去。
西昌,满城的冰粉摊子。树荫下,一米见方的保温箱里装着冰块,冰块包围着一个搪瓷盆子,里面装的就是搓好的冰粉。有的冰粉摊会准备两个小凳子,有的没有,客人直接过去,点了站在阴凉处喝。老板会拿出小碗,小心地舀一块出来,然后用勺子轻轻在碗里切打,完整透明的冰粉瞬间裂开成了晶莹通透的碎块。两勺同样冰镇过的、浓浓的红糖汁迎头浇上去,糖水瞬间从碎裂的缝隙呲溜进去,和冰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喝一口,冰凉嫩滑,甜香四溢,身上的燥热马上消除,真是痛快无比!
我喝了二十多年的冰粉,前几天才第一次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冰粉籽果实的照片。一种特别美的植物,果实是如李子大小的小圆球,穿一件轻盈薄脆的外衣,像一个初次穿上芭蕾舞裙的胖丫头。朋友说,钳开外衣以后,里面是比芝麻还小的冰粉籽,做一盆冰粉需要的冰粉籽,要从很多很多这样的果实里提取出来。她还说,现在这种野生植物越来越少,种植的人也不多了,人们都用果冻粉和魔芋粉来代替,做出来的冰粉,像有嚼劲的果冻,再被“别出心裁”地加上花生碎、葡萄干,乃至各种切碎的红绿果脯,东西加得越多,越难喝,那种纯天然的冰粉味,再难寻觅。
尽管如此,这些年不管去到哪个城市,不管是去吃川菜,还是火锅,只要店里菜单上有“冰粉”,我总是会点的。即便那红糖汁并不香醇,还搭配了切碎的山楂片,但总归,还是有那么一点留存在记忆里的味道的。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不敢奢求完全的原汁原味,有那么一点,也就够了。
传统正宗的手搓冰粉,制作起来非常麻烦。将细小如针尖的冰粉籽包进纱布里,把纱布扎紧,在装了纯净水的盆里用力揉搓,不一会儿就能看见有细滑的浓浆从纱布里渗透出来。搓一盆冰粉,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很大的力气,到那盆清水变了颜色、变得浓稠,“点”入一些石灰水。传统工艺难,难就难在这个石灰水的量上,多一点,太老,少一点,不凝固,刚才揉搓的功夫就全白费了。
我20年前在西昌读书的时候,很爱在周末去一条巷子里的冰粉店喝一个老阿姨做的冰粉。这位阿姨每天搓两盆冰粉来卖,完全手工。老阿姨的家乡在雷波县金沙江畔,那里盛产甘蔗,她所用的红糖是亲戚家土灶榨出来的碗糖,香醇,浓郁,原汁原味,用来搭配冰粉,口感绝佳。老阿姨卖的冰粉,五毛钱一碗,对于当时生活费一百元的我来说,也是负担得起的。所以,为了那一碗清凉和甜蜜,走再远的路,我也会去。
去年,我带着女儿回了一趟西昌,坐车经过那条老街的时候,感到暑热难当,突然想起那家小店,就和司机聊了起来。哪知那司机也熟知那家冰粉店,并告诉我:“店还开着呢。”我惊喜万分,立马改变行程,请他把我们送到那里。
还是那样一个小小的门头,熟悉的、镶着玻璃的、斑驳的桌子,两盆嫩嘟嘟的冰粉上盖着一块玻璃板,还是那个装红糖的、印着喜鹊的搪瓷杯,系着围裙的老阿姨还在亲力亲为。
我问老阿姨:“年近70了,为什么不休息呢?”
老阿姨说:“不能休息,一休息,就浑身不舒服,要生病。”
屋子里,坐了好多人,又有很多穿校服的孩子蹦跶进来,叽叽喳喳,你拍我打的。还有几位中年人,钻进来,喊一声“谢嬢嬢,要一碗冰粉”,站着喝完,然后把钱放柜上就走了。我身边的条凳上,坐着一位些许发福、有谢顶趋势的男人,他在慢慢地喝。我心想,也许当年,我们也曾在这里相遇过呢,他那会儿可能刚在学校打完篮球,撩起衣服的一角,擦擦汗,就过来了。
我端起碗,和女儿分享了这一碗甜蜜的食物。
“好喝吗?”我问她。
“嗯!”不到两岁的女儿点点头,伸出小手指着玻璃柜台说:“再倒!”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