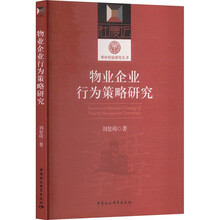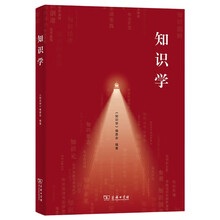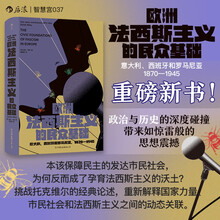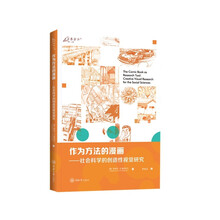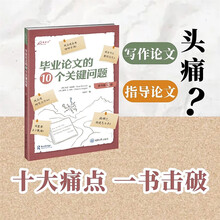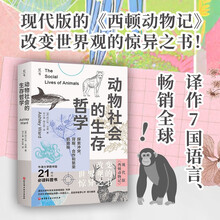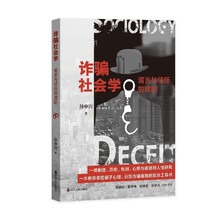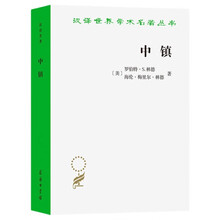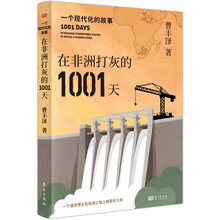《小时候过年》:
下过几场大大小小的雪后,厚厚的日历,一页一页越翻越少了。
盼着盼着,年,终于陕来了!
小时候,每逢过年,记得差不多都是从卖猪开始的。
那往往是刚进人腊月后不久的某一天。
这天的早晨,爹和娘起得比以往要早。他们脚步轻快,心情愉悦。我和弟弟妹妹们趴在暖暖的被窝里,瞧着出出进进的爹,还有出出进进的娘,感觉屋里的空气似乎都一下子轻盈了起来。
可不是吗,要卖猪了呢,今天,我们家就要有一笔一年之中最大的收入了呢!
爹从院大门门洞里推出独轮车,给独轮车打好气,找出油壶,冲轮轴上“咕嘟咕嘟”打油,摘下上房房檐上挂的绳子,放车上,紧一紧系在腰上的围脖,到我大爷家去,让我大哥、二哥吃了饭过来帮个忙——绑猪。
娘顶着那块蓝花头巾,忙着拉风箱“呱嗒呱嗒”做饭,给猪破例煮一锅稠稠的地瓜粥,凉在盆子里。
饭还没吃完,大哥、二哥就来了。娘赶紧放下碗,用一根手指头试试凉在盆子里的粥,然后舀到猪食槽子里让猪吃。
猪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食,自打春天还是十几斤的猪娃时,被娘从集上背回来,顿顿不是草就是洗碗水刷锅汤,这回吃得特别香,槽子里含一大口,“吧唧吧唧”嚼着,不待“咕噜”咽下去,插进槽子里的嘴就又是一大口。毛茸茸的一双眼睛,看着娘。
娘摸摸猪的背,手指当梳子,梳梳猪脖子上硬扎扎的鬃毛,把盆子里的粥刮擦干净,都给倒上,一点儿也没剩。
不多会儿,猪吃好了。
爹、大哥、二哥抓住猪的后腿,把猪放倒绑起来,弯腰憋红着脸抬到独轮车上。我赶紧扶着车,坐到另一边的前头坠偏。爹架起独轮车,娘把已拴在车前头的绳子拾起来放在肩上拉着,我们向收购站走去。
天灰蒙蒙的,一呼吸嘴前一团白白的热气。出村后。地里还覆着雪,白白的雪被下,麦苗正做着甜甜的梦。
远处的村子里,有零星的鞭炮声,那是即将到来的年的声音,也是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声音。
收购站在镇东的河边上。老远就看到了河上飘起的热气,听到了河水的喧响。
这条河是打南边来的,拐个弯后,悠悠地向北而去了。夏天,河两岸是茂密的芦苇,风一吹,叶子相互触碰,“刷刷”地响。里面,各种野花儿竞相绽放,是小鸟们的天堂。
收购站里已有很多很多卖猪的人,拉着地排车的,推着独轮车的,都有,他们排成长长的一条队,都延伸到了外边那条东西向的沙土路上。
是呀,紧算慢算还有二十多天就过年了,谁不想赶紧把猪卖了,去置办年货呢,那可是浓郁的酒,喷香的肉,光鲜鲜的新衣,红艳艳的头绳,脆脆响的鞭炮呢!
紧挨着过磅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栅栏,老大,圈着好多收购进去的猪。黑的、白的、花的都有,有的趴着,有的站着,有的走来走去,不慌不忙、十分悠闲的样子。
收购员戴着蓝套袖,耳朵上夹着烟卷,忙得连说句话都顾不上。
随着队伍不断向前移动,慢慢地,轮到我们了,爹和娘把猪推到磅秤旁。收购员摸摸车上的猪,看大小、肥瘦,准备定级。猪越肥,定的级越好,卖的钱越多。
爹和娘都笑着,看着收购员摸猪,谦恭而又小心地等待着。
收购员说了个级,征询地看着爹和娘,意思是要是不同意,可以不卖,再推走。
爹立刻同意了。这是个挺不错的级,符合他和娘来之前的预想。
别的几个收购员立刻过来,帮着父亲解绳子,把猪抬到磅秤上一个专门过磅的木托里。
收购员抹抹秤,报了斤数,在磅秤顶上用圆珠笔开票。
他们在猪屁股那儿的白毛上剪上记号,放进木栅栏。
娘跟过去,抓着栅栏,看着我们的猪。我们的猪也回过头来,看着娘,依依地,不肯往深处走。
爹拿着票,到旁边一个平房窗口,排队弯腰递进去,等待里面算盘响过,把盖上章的票递出来,再到另一个窗口排队,领出了钱。
我站在独轮车旁,看着车。
爹过来了,喊了几声娘,娘从栅栏那儿走过来,不停地回头瞅着我们的猪,接过爹递给她的钱,点两遍,从棉袄内兜里掏出包钱的那块旧手绢,包进去,揣好。
爹架起车,我们往回走。
没有了猪,独轮车轻快了。我骑坐在独轮车中间凸起的那道脊梁骨上,一口一口,吃着一串爹刚给我买的又酸又甜的糖葫芦。
爹和娘商量着要给我们小孩子做新棉裤、新棉袄。过年了,有钱了。娘说,明天她就到商店去买布。
爹一声声“嗯”着,听娘说。娘说话,爹要同意,都是说“嗯”。
他们边说着,边往前走。
过会儿,娘又说:“要不再给顺子买顶帽子吧,他都给我说过好几回了。”顺子是我。娘说的帽子,棉的,电影上八路军戴的那种,灰色。我一听,立刻扭头瞅爹。爹说:“嗯。”噢——答应了!我心里兴奋不已,如同冬日的某个早晨,起床后忽然发现院子里已落了第一场大雪般惊喜,因为我们小学有一个同学就戴着一顶,非常漂亮,我羡慕极了。
过年我也能戴上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