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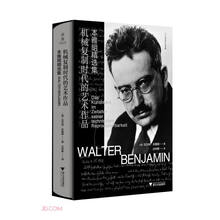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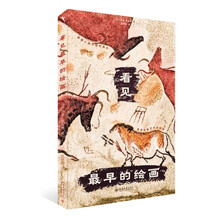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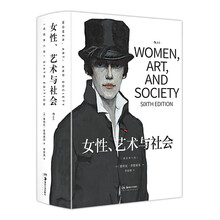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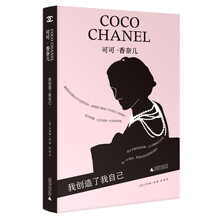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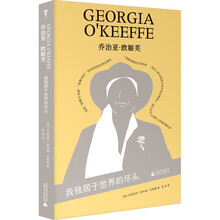
波普艺术与先锋派
即便波普艺术在纽约艺术界最为成功的时候,批评家们对于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亦争论不休。有人宣称波普艺术家强化了寻常物的意义,并通过在新语境中呈现它们,揭示了它们的“崇高”意义(Chase,1976:22)。其他人指责他们不能发展而只能重复自己的观念(Moffett,1974:32)。班纳德(Bannard,1966)指出,这些画家已经放弃了现代主义美学传统,对美学观念的发展也毫无助益。争论是复杂的,即便在现代艺术内部,对美学传统的理解亦有不同。正如我们所见,作为20世纪那些重要抽象作品的基础,现代主义美学传统亦为纽约艺术界的大部分风格提供了基础。
与这种发展并行的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另一次先锋派运动,其先行者是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该运动的特点是,通过为日常物品(所谓的“现成品”)任意加上艺术品的标签,来尝试打破先锋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给《蒙娜丽莎》的复制品加上小胡子,将一个大批量生产的小便器作为一个喷泉雕塑来展出,通过这些方式,杜尚改变了这些物品的意义,破坏了艺术品独一无二的神圣品质,改变了寻常物的意义(Benjamin,1973; Huyssen,1980)。
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先锋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拓展了杜尚的观念,并将其运用到先锋音乐的作曲上。凯奇的目标是生产由偶然决定的艺术,其中艺术家的自我以及艺术与日常经验的所有区别都将荡然无存。因为受到同辈音乐家的排斥,凯奇试图联系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他是抽象表现主义者“俱乐部”的早期成员(Kirby and Schechner,1965:67)。在他及其长期合作的舞蹈家梅尔塞·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的影响下,一群舞蹈家、画家和诗人参与到了激进革新的舞蹈项目之中,并在格林威治村的贾德森纪念教堂做了偶发艺术活动(Jowitt,1971:81)。
凯奇对画家的影响是双重的:他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了日常图像、艺术品和事件,并将它们转化到一个新的思想进程之中,其基础是杜尚的如下观念,即艺术应该充满了游戏、双关语和悖论(Sandler,1978:170; Perreault,1968:259; Rose,1968:280)。另一方面,这一运动通过将视觉艺术中的高雅文化置于荒谬之地,以及表明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可以互换的,而有助于蚀空高雅文化的基础。
波普艺术有两个重要支脉。其中一个是由参与偶发艺术的艺术家(Baldwin,1974),以及那些试图改变观众对待日常事件态度的艺术家发展出来的。最早的那批波普艺术家,将展示潜在于各类遍布当代社会的符号和信息中的模糊性作为自己的主题。克拉斯·奥尔登堡在其“仓库”中展览的雕塑,是诸如各类符号、衣服和食物等日常物品,这代表了波普艺术破除因袭的一面。阿罗威(Alloway,1974:101)认为,这些雕塑是“对实际上在实体商店里售卖和展示的各类商品的激进转化”。
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在美学传统面前的举棋不定的态度,以及他们想要以某种方式将美学传统与通俗文化的视觉图像结合起来的欲望。对这些艺术家而言,严肃艺术的视觉图像和流行艺术的视觉图像的结合越发成问题。克拉斯·奥尔登堡的评论能够说明这一点(Glaser,1966:23):“我深受商业艺术与纯艺术或精品绘画和偶然效果的区分的困扰。我认为我们已经特意尝试探查了这一领域及其滑稽的弦外之音。”
一般而言,这些艺术家惯于以讽刺的方式对待美学传统。利希滕斯坦以戏仿和漫画的方式模仿了现代美学传统中的名作,其中包括塞尚、毕加索、蒙德里安、莫奈和一些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的画作(Seitz,1972:64)。梅尔·拉莫斯(Mel Ramos)戏仿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法国绘画,如莫奈、布歇(Boucher)和安格尔(Ingres)等人的作品(Truewoman,1975)。贾斯珀·约翰斯创作的作品,为了讨论艺术符号的本质,借用并拓展了杜尚的观念(Johnson,1965:140)。这些艺术家似乎在建议人们,在当代社会既不要把艺术太当回事,也不要把艺术家太当回事。
其他艺术家对待流行主题的方式因人而异。这一对待通俗文化的不同方式的缩影,可以在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和生活方式中,以及他拒绝对自己的表现对象做任何评论,以相似的方式处理布里洛盒子、电椅照片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等方面见出。从一种文化视角来看,安迪·沃霍尔是这次运动的主将,他以极端方式表征了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发生的审美价值变迁的事实。他的作品表征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其内涵唯有借助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换言之,一些波普艺术家不只是在简单地使用源自通俗文化的主题和图像;从其使用这些材料的方式来看,它事实上就是一种通俗文化。
虽然一些艺术家在通俗文化工业的语境中制作了一些极为深奥的作品,通俗文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由意在造成某种审美效果的标准化生产程序构成(Cawelti,1976)。在此类作品中,复杂的表现对象被简化,具有普遍诱惑力的表现对象便以这种方式得到呈现。因为那些程式稍作修正就能反复使用,新版作品就能被以极快的速度生产出来。这些公式的特点的集中体现是安迪·沃霍尔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生产的丝网印刷肖像画。在当代艺术风格之外工作的艺术家,经常从现存的审美传统中选取元素,并将它们化约为公式;相反,沃霍尔则用源自通俗文化的要素创造出新公式。换言之,他的表现对象、技巧以及材料(其形式是大众媒介照片),都常常取自通俗文化。从本质上讲,他的题材含蓄地评论了“媒介文化”对生活的影响(Deitch,1980; Schjeldahl,1980)。
沃霍尔的丝网印刷肖像画以表现对象的照片为基础,涵盖了尽人皆知的剧照、新闻照片、传统家庭的快照,以及沃霍尔自己拍的拍立得照片(Bourdon,1975:44)。虽然丝网印刷肖像画是以照片为基础,但是它们提供的人物脸部的细节信息,比由具象派画家创作的肖像画还少(Bourdon,1975:44)。换言之,在这些肖像画中,题材的复杂性被极大简化了,只表现为一种模式化线条。事实上,沃霍尔并不是要如实地呈现其肖像画的人物,而是在呈现“富于魅力的幻影”。沃霍尔赋予其表现对象的,是它们被简化但更加迷人的容貌和个性版本。在眼睛和嘴唇的重要性被普遍放大的同时,那些缺点和无吸引力的特点,就被遮盖了起来。据说,他的目的是使那些肖像画显得“极其魅惑”。他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创造关于他的人物的标准图像,这些人物符合那些在通俗文化中广为流传的特定的美丽观念。在生产最终版本的“准机械化”程序的不同节点,他会给那些照片式的图像上色。但是沃霍尔强调,他做这些时十分随意,可谓马马虎虎。事实上,他的所有艺术产品(包括制作电影和写作)的特点就是毫不费力。技艺是禁忌。沃霍尔贬低且不认同任何美学传统。据说,他已经达到了自认的最佳效果,一种直觉的结果。批评家认为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关于形式和观念问题的意识。
通俗文化通常由一群合作者或某个有多位助手的人生产出来。在此意义上,沃霍尔的艺术生产方式与通俗文化相似。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他将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工厂”(The Factory),一直被助手和同事环绕,随行人员包括一个摇滚乐队和一个电影剧组。在20世纪70年代,该群体收购了一份月报和一个电视节目,此外还制作书籍。休斯(Hughes,1982:8)认为,沃霍尔批量生产了“他的大众产品的图像,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到底是谁生产了他的大多数作品这一问题,从那时起,其经纪人就一直避而不谈(大概有一半的作品是由其助手印出的,只不过签了沃霍尔的名字罢了)”。
归根结底,波普艺术是不是先锋运动?显然,波普艺术家重新界定了艺术的诸多美学和社会维度。他们通过采纳原是作为通俗文化而被创作出来的卡通漫画和广告,以及创造像食物和房屋家具等的复制品,重新界定了何谓恰当题材的惯例。一些波普艺术家,如罗伯特·劳申伯格和贾斯珀·约翰斯,通过将寝具或木片等物体贴于画布上而重新界定了画布(Siegel,1985:152—153)。克拉斯·奥尔登堡等人,通过创造各种装置而重新界定了艺术品,这些装置是真实的设置而非对艺术品的再现。像丝网印刷这类新技术,则改变了艺术作品的生产工序。
然而,波普艺术中的“抗议”因素是以讽刺和戏仿的形式直接针对美学传统自身而非更宽泛的文化的。波普艺术还试图通过修正与题材、技术有关的惯例,来重新界定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关系,这些惯例维持着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分野。
作为对战后现代艺术世界的一次全面社会学分析,本书*越了传统的艺术史风格……克兰以扎实的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探究了先锋艺术家工作与社交背后的社会背景,特别是来自消费社会及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极具启发性。
——布赖恩沃利斯,《美国艺术》
克兰在本书中展现了极富创造性的学术才华。她历经数年,深入研究了大量文献材料,包括艺术家的传记、艺术评论、艺术纪录片、博物馆和画廊的展览目录,以及拍卖行的销售记录等,再现了先锋艺术运动的兴起和转型。
——罗萨娜马尔托雷拉,《当代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