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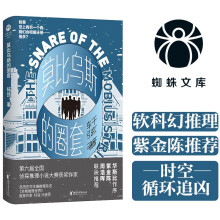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本书的作者是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在作者的学术生涯中,其前期一直从事外国建筑方面的研究,但自退休之后,便一头扎进中国乡土建筑当中。在他看来,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是乡土文化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非常大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本书集合了作者有关乡土建筑两类具有代表性的著述,一是乡土建筑研究的论述,一是精选了序跋中的七篇。文章学术观点清晰,短小精悍,优美抒情,可读性强。在这一篇篇饱含深厚感情的文章里,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受到家园故去甚至遭受摧残的伤痛,也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被点滴侵蚀的忧虑,更有一份为“为抢救传统村落‘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决心。
代序
年过八十,终于老了,这才体验到什么叫记忆力衰退,原来它不是“渐行渐远”,而是跟拉电灯开关一样,吧嗒一声,一件事便再也想不起来了。不过,它也会有几次反复,说不定哪天就会有陈谷子、烂芝麻忽然闪进脑子,但是,那些似真似幻的故事要求证便难了。于是,有一些年富力强的朋友就逼迫我写几段回忆录,不写,便不给饭吃。不给饭吃,即使对我这样的老糊涂来说,也是怪可怕的惩罚,我便运气调息,想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有三个时期倒是还有点儿事情可记。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上山下乡搞乡土建筑研究时期。正好是少年时期、壮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前两个时期虽然也很有些重要的情节,不过那是全民族性的事件,我的经历跟许多朋友的一比,简直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不妨先把它们撂下。第三个时期,倒是有点儿我个人的特色,虽然未必能吸引多少人的关心,但也会有人觉得有趣。
其实,这第三个时期和前两个时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日寇侵略者在南京杀死了我的三爷爷和小姑姑,也把我从滨海一个中等县城赶到了农村。整整八年,随学校上山下乡,在祠堂里住宿,在庙宇里上课,在老乡家里洗衣服,煮白薯吃。那些淳厚的农妇,以仁慈的心对待我们这些连衣服都洗不干净的孩子。我们把从田里偷来的几块小小的白薯请她们煮,她们会端出一大盆煮白薯来,看着我们吃下肚去。我们发烫的脸都不好意思抬起来对她们说声谢谢。这岂是此生能忘记的!
第二个时期,在学校里遭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的冲击,见到了恶,也见到了善。好在闹了两年多,学校里就要“斗、批、改”了,把我们一批人弄到农场去“脱胎换骨”。农场可是美丽的,有无边的水稻和菜花,有高翔远飞的大雁和唱个不停的百灵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爽的环境,心想下半辈子务农也不赖。看来我身上流动着的还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父母的血。这一身血早晚要流回土地里去。祖国苏醒过来不久,80年代初,我就凭着被农场生活唤醒了的对乡土的爱,去找了我在社会学系读书时候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询问他那里有没有机会让我去做乡土建筑研究。看来费先生还有很重的顾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叫我不妨去问问翁独健先生。我以前不认识翁先生,但还是骑着自行车进城到他家去了一趟。他正在藏书室里翻书,我说了来意,他没有停手便摇摇头,我只得辞了出来。这件事正好证明我的愚蠢,那正是“心有余悸”还担心“七八年来一次”的时候,闹什么新鲜事儿。
于是,老老实实回学校,仍然干我的外国建筑史和外国园林史的研究。“隔山打牛”,挺滑稽的,何况只能从老书本上识牛。
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一晃几年过去,来了机会。1989年浙江省龙游县的政府领导人居然想到把本县村子里一些高档宗祠和“大院”拆迁到城边上的鸡鸣山风景区去,弄成一个“民居苑”。为了干好这件事,邀请我们建筑系派人去帮他们把那些要拆迁的房子测绘一下。系领导同意了。我从50年代起便负责一门叫作“古建筑测绘”的实习课,当然在奉派之列,带着学生去了。那年代的学生学习努力,工作认真,很快便完成了任务,于是向我和另一位女老师李秋香提出要求,带他们到附近村子里再参观一些古老民居。这建议跟我的兴趣合拍,便答应了他们。
第一个想到的主意是到建德去。大约五六年前,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认识了建德市的叶同宽老师。他天分高,可惜“成分”也“高”,上不了大学,便坚持自学,终于成材,那时在一个什么政府部门做建筑设计工作。龙游跟建德相近,可是,他在什么部门工作呢,一点也不知道。但我还是带着学生到了建德。从火车站进城,上个长坡,迎面就是园林局,我们敲门进去打听,真是老天有眼,正巧叶老师就在园林局的技术科里工作。
叶老师是一位心肠火热的人,我们把愿望一说,他立即答应接待,先安排好了住宿、伙食,又立马带我们游了一趟千岛湖和一趟富春江,也看了几个小村子。
随后,我们到了杭州,住在六和塔附近,因为我们在六和塔上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把该做的工作做完,一身轻松,就到浙江省建设厅,找到了当副厅长的一位老同学。谈了一会儿,他知道了我们对乡土建筑有兴趣,就说,他老家永嘉的楠溪江流域有一大批很美的农村建筑,正好,他过几天就要去出差,如果我们乐意去,他可以带上我们。我和李秋香立即决定,先把学生们带到东阳、义乌看看,送他们上了火车回学校,我们就跟这位老同学到楠溪江去。
送走了学生之后,还有三五天时间,我和李老师都不是喜爱城市繁华的人,杭州虽然风光旖旎,毕竟还是一身城市气,于是,立即决定回建德再住几天,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好的老村子。这一回去,收获可大了,叶同宽老师把我们带到他老家新叶村,对我们此后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来说,这竟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我们当时见到的新叶村,简直是一个毫发无损的农耕时代村落的标本,非常纯正。当然,说的是建筑群和它的环境,不涉及政治和经济。它居然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一座文峰塔,据说,整个浙江省几百上千个村落就只剩下这么一座塔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过去倒曾经有过上百座。村子里其他各类建筑如住宅、宗祠、书院等等的质量都很高,保护得也很好。村子的布局,它和农田、河渠以及四周山峦的关系也很协调,简直是一类村子的典型。
我和李秋香都很兴奋,一面走走看看,一面就商量起怎么下手研究这个课题来。
待回到杭州,第二天清早搭上副厅长的车,一整天不曾太耽误,破路上磨磨蹭蹭,赶到永嘉已经天黑了,店铺都早已关上了门。小吃店也都打了烊,敲开一家,求老板给个方便,每个人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找了一家宿店睡觉。
第二天清早就下乡,楠溪江两岸的村落一下子就把我们抓住了。借一句古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这是我们以后二十多年来对楠溪江不变的赞誉。初看,那些房子虽然都很亲切,又很潇洒,但是,似乎又都很粗糙,原木蛮石的砌筑而已。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什么吸引了我?哎哟,原来那原木蛮石竟是那么精致、那么细巧、那么有智慧,它们都蒙在一层似乎漫不经心的粗野的外衣之下,于是就显得轻松、家常。看惯了奢华的院落式村舍,封闭而谨慎,再看这些楠溪江住宅,那种开放的自由、随意的风格,把我们的心也带动得活泼有生气了,仿佛立即就能跟房主人交上好朋友。这真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我们是从温州乘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北京的。路上,我们兴奋地把一个研究计划讨论定型,只待动手干了。但是,经费呢?怎么办?总得有几个车票钱吧。“一钱难死英雄汉”,这是武侠小说里的老话,连秦叔宝那样的好汉都被逼得上市去卖黄骠马,我们能卖什么呢?只有一辆破自行车!总不能带着学生一起行军吧,好几千里路呐!
几年前建议费孝通先生和翁独健先生领导起来去做的工作,难道还依旧是空想?放下不做,那可是太可惜了,农村里拆旧建新的风已经刮起来了,我们当然不反对造新房子,但总得留下几处这么美的老村子呀。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忽然出了个奇招:先做新叶村,问问叶同宽老师有没有可能向建德的什么单位筹点儿路费。我们精打细算,把人力压缩到最低,第一次去四个人,要四个人的来回车票。
就这样病急乱投医,有点儿滑稽。不料宽厚的叶老师回了信:可以!很快就把钱寄过来了。那时候他是一位极其平常的普通技术人员,甚至还不是正式进了编制的人员。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了,我们跟叶老师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次面了,我从来不问他,这笔钱是他从哪里筹来的。我隐隐觉得,这钱是他私人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公款里报销这笔路费。找人去“筹”?没有一丁点儿借口!是叶老师开动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工作!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去
目 录
代 序
乡土建筑研究
兰江岸边
来到了关麓村
徽商村里的生活
初到黄土高原
婺源掠影
清华彩虹
芙蓉村
到张壁村去
重回楠溪江
曲径通幽处
俞源村
九龙山下人家
苍坡村
岩头村
蓬溪村
楼下村掠影
狮峰寺一日
岭南的暖冬
洞主庙
告别俞源村
从哥老会说起
走好,福宝场
碛口恋
序跋选摘
《古村郭峪碑文集》序
《江南明清门窗格子》序《走近太行古村落》序
《宁海古戏台》序
《乡土屏南》序
《福建土楼建筑》序
《故园——远去的家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