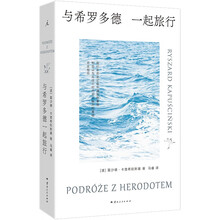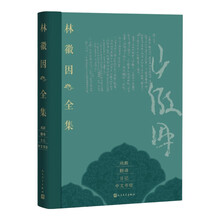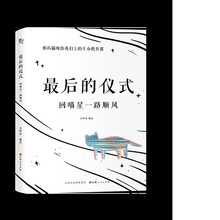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苏轼:一樽还酹江月》:
之前东坡受贬前来黄州,经过季常庄上,见其家四壁萧然,季常却安之若素,言笑晏晏,妻子奴婢更皆脸有自得之色。苏轼惊异并称慕其人其家风、其淡定从容之态度——这也影响了黄州后来的苏轼吧。季常杀鸡宰鸭,没有半点让苏轼感觉到自己是个落魄人,似乎更像季常衣锦还乡的亲人。这雪中送炭的滋味,仿佛眼下之床前明月光。
东坡走下台阶,轻轻坐在石凳上。
“签判苏轼,目无长官,不尊礼教,中元节过太守官邸而不拜,特罚铜八斤,以儆效尤。”苏轼站在台阶下,羞隗交加,又怒又恨。
凤翔太守陈希亮(公弼)如同寒潭般的目光扫来,与苏轼目光对接,苏轼不由自主低下了头。在这个看似身瘦体弱、面貌寻常的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长官面前,苏轼常常找不到自信。年仅二十七岁的他,年少气盛,在内心里,他十分痛恨陈太守。
事隔多年以后,在季常家——对了,季常是陈太守公弼公的幼子,季常借着酒意告诉苏轼:“子瞻兄,先父常在私底下夸赞兄之人品才华,让弟引以为楷模呢。依弟看来,兄长才高八斗是真,疏放不羁亦不假,骄傲自恃更多多。若无吾父,恐怕以你我二人不识高低天性,更不知要闯下多少祸事,弄出多少贻笑大方的言行来。子瞻兄,父亲前年亡故,小弟有个不情之请,请兄长为吾父书传并书墓志铭。”苏轼慨然提笔,饱蘸浓墨,以行楷书款款写来:“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是的,这是真心话,苏轼而今深深后悔了。
当年,他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主考官(时知贡举)欧阳修赏识,声名大振。欧阳修一再称许:“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而后,苏轼又参加了极难的制科考试(通过进士考试之后,特别出众贤良人才经推荐,再参加制科考试。两宋三百多年江山,通过之人仅为二十余人),并高中三等(一二等为虚设,实际上苏轼即为第一)。弟弟子由为四等。
兄弟同中,前所未有。苏轼到了凤翔,仿佛明星出场,府衙中某吏役,出于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尊称他为“苏贤良”。不料陈太守听到,大怒,当场发话:“府判官何贤良也!黄口小儿,不知老少,无有高低,岂有此理!”他下令答杖拍马小吏,让苏轼很是下不来台。尔后,苏轼所写公文,即便是府里头斋醮、祈祷类的小文,从语气到行文规范到遣词造句,陈希亮每每认真到吹毛求疵,毫不客气涂抹删改,篇篇往返不休。在之前一直受到他人夸赞、以文章自负的苏轼看来,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没法活了。
不久,陈希亮使人于廨字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终南山。亭成,他请苏轼作记,苏轼乘此机会“公报私仇”,狠狠在文中挖苦陈太守:“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生命苦短,木石之台都不可能长久,太守肉身凡躯您就别指望与日月同辉了。物和“吾”,不过是沧海一粟,始终都会过去的。
陈希亮见了,微微一笑,未改一字,令人刻石留存。他私下里对幕僚说道:“苏陈两家同乡,且数代世交,苏明允为我儿子辈,苏轼不过是孙辈。平日里从不假以辞色之缘故,实因苏轼年少暴得大名,我担心他骄傲自满,种下祸害。盛名累累,恐怕他担不起啊。”而今识遍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苏轼这才明白公弼公当年的良苦用心。少年得志,遇到吹捧容易,遇到严苛的爱护难。端着架子,毫不客气,裁抑锋芒太露的后辈的长官,虽一时让入难以接受、难以忍受,终归,比起那些无用的吹捧,让你更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对你好的吧。有些人,是上天派来帮你的,磨炼你的心性,助益你的成长。“唉,可惜,我明白得太迟了。”回首二十多年来,他在宋之官场一路走来的坎坷、艰辛、苦痛,写下的那些几乎让他掉脑袋的诗文,他而今深深后悔当年没有理解公弼公的良药苦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