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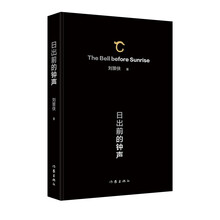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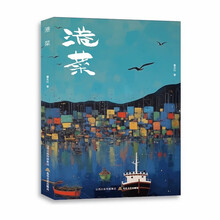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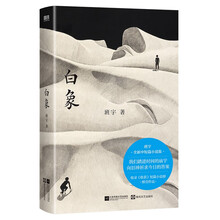
★止庵短篇小说作品首次集结出版
★重温1980年代: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
★这本书是一些好故事,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以及如海风般扑面而来的80年代的潮潮湿气,主人公们在自己的生活节点里无所适从,意义和价值成为他们人生之上的重负;如若这重负卸却之后呢,“人生不过如此”,——然而如果再多问一句的话,那个“如此”是什么呢。
★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以此来区分,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止庵
1980年代,一个正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一个“用一台海鸥DF-1就可以撂倒一个姑娘的时代”,一个谈论尼采、昆德拉甚至托洛斯基、索尔仁尼琴都稀松平常的时代;苦闷、沉默、死亡、自由等诗性命题充满着年轻人的生活,但面对正在生长的水泥森林,他们也肆无忌惮、漫谈理想,鲜活又沉闷,是孤独的江湖游侠。那或许是一个被过度美化的乌托邦,但它承载着许多曾有的辉煌。学者止庵首部短篇小说作品,在五部短篇中,重温1980年代,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止庵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
《世上的盐》:墙上的时钟指向十二点,幻觉里当的一响。我把脸转向窗外。五颜六色的遮阳伞,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年男女,杯子里的饮料呈现诱人的橘黄色……你还不来。
《墨西哥城之夜》:过道里什么都是淡淡的,白色的,墙壁,衣架,衣架上挂着的衬衫,连厨房透过来的日光也是淡淡的,白色的;只有那个公文包是黑的。
《喜剧作家》:是这个地方吗?好像……好像很宽敞很整洁……有一片阴凉……有一棵树皮剥裂的老槐树……泛着淡绿的白花一簇一簇幽幽的花香……孩子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们围着小桌坐在树下……好像什么也记不得了…
《走向》:站台上的两排柱子,晃晃荡荡的人影,向一端翘起的檐顶,四周沉沉的暮色,以及远处那盏红灯,都令他奇怪地感到是在一条船上。
《姐儿俩》:我们站住,看那架飞机起飞,听见那种轰鸣,越飞越远,直到变成一个银白的小点儿消失在蓝天之中。
墨西哥城之夜
孩子的父亲回到家,一眼就看见那个黑公文包。过道里什么都是淡淡的,白色的,墙壁,衣架,衣架上挂着的衬衫,连厨房透过来的日光也是淡淡的,白色的;只有那个公文包是黑的。鼓鼓囊囊,带着一股油亮的光泽,在墙上投了个大黑影子。
厨房隐隐传来说话声。
透过沾点油腻的玻璃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的侧影,身材高大,壮壮实实,胡茬浓重,脸膛红扑扑的,穿件黑衬衫。说话时做着手势,身子一动一动,吐出的烟在斜射的光线里飘忽升腾。
孩子的母亲面对他坐着,马扎很矮,她的身躯显得硕大,甚至显得笨重。米黄色连衣裙盖住膝盖,双腿叉开;腿和手臂又白,又丰满。她仰脸望着他,不时笑笑。脚边有堆空豆荚,粒粒嫩绿的豌豆从她指间弹出,在铝盆里蹦蹦跳跳。她身后煤气灶上有口锅正滚开着,一股炖鸡的味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孩子的父亲走到厨房门口,把带回家的一条带鱼放在那儿。那条鱼又扁又薄卷成难受的样子,就像从来没有活过。厨房又飘出一股炖鸡的味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他就走开。他的影子也是瘦小的,映在墙上成了怪异的形象。影子从墙上缓缓滑过,滑向他自己的房间,谁也没听见他的脚步声,谁也没觉出那个瘦小的人形走过了过道。
走过孩子的母亲的房间门口,他站住了。门开着。女儿仰面躺在床上,双臂伸开,两条瘦长的腿探出床沿。十岁了,还那么单薄,那么羸瘦。她的脸上淡淡的,两眼望着天花板。咚的一声,有只肥胖的黑猫沉重地蹦到她扁平的胸上,随即就跳开了。忽然又扑上去,抱住她的手啃呀啃的,嘴里呜呜地叫。她不躲闪,也不打它。
他从门口悄悄走开,就像刚才他悄悄走来。女儿没有任何反应,就像他既没有走来,也没有走开。他缓缓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
后来,从他的房间传出轻轻的音乐声,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吃晚饭的时候,他的房门开了。房间里一片黑暗,黑暗里凸现出他的脸、他的身体。脚步缓慢,飘飘忽忽,就像已经逝去的音乐。
过道里灯光煌煌。饭桌已经摆开,新桌布显出清晰的褶痕。红的番茄,绿的豌豆,白斩鸡油光光的。还有那盘带鱼,炸得干干的,呈褐色。孩子的母亲围着条花围裙,匆匆把菜端来,又匆匆回到厨房。那个黑公文包挂在衣架上,那个男人坐在桌旁。他挑了块鸡腿放进孩子的碗里,孩子坐在他身边,低头摆弄着筷子。然后那个男人站起来,大声催促孩子的母亲快来吃饭。她答应着,急忙跑来入座,两个乳房轻轻闪动。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瓶啤酒放在桌上,酒瓶散发着凉气,上面蒙了层 水雾。
孩子的父亲低声说:“今天我不喝。”
那个男人朗朗笑了:“天这么热,喝点怕什么?来,满上。”
说着就伸手取走他面前的杯子,递给孩子的母亲。她把杯子倒满,又放回他面前。泡沫溢出了,顺着杯壁流到桌上,淡蓝色的桌布浸湿了,颜色变深,继续洇开来。他迟疑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那个男人领口敞着,露出粗壮的脖子,手臂汗毛粗重,黑黑的一层。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啤酒,忽然问道:“昨天夜里看球赛了吗?”
孩子的父亲淡淡一笑,摇了摇头。啤酒好凉,反倒使他不舒服。
这时候孩子的母亲抢着说:“墨西哥城十一点是北京夏季时间夜里两点。”
她还伸出两个手指比画了一下。她的手不大,胖胖的,皮肤光洁细腻。
那个男人喝了酒,脸更红了,说道:“看足球挺来劲的,当然要是能亲临现场就更棒了。咱们这玩意儿不行,简直太窝囊。哪个体育项目也比不上这个,一个国家行还是不行就看足球了。去得了去不了墨西哥城,就看出行不行了。”
孩子的父亲又喝了一口,索性把杯子里的酒喝干。还是太凉,刺激得他胃有点儿疼,身上打起颤来。他就又满满倒上一杯,又猛地喝一大口。他忽然说:“不知道曾雪麟坐在电视机前作何感想。”
他们笑了,然后他们喝酒、吃菜。孩子默默地吃饭,从不抬起眼睛。孩子的父亲一口喝完杯子里的酒,把杯子轻轻放在桌上。孩子的母亲又把酒瓶伸过来,被他拦住了。他好像无意中碰了她手一下,她的手的确又柔软,又光滑。
“你们慢慢吃吧。”他站起来。
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又把门关上。把台灯打开,他的影子就又投在墙上和天花板上,就又是奇形怪状,又在吓唬他自己了。不在前面就在后面,在头顶上一片光幻化成另一片光;瘦小的身体笼罩在巨大的影子里,就像不是他而是那个影子在走动。
他终于坐下,影子终于静默。点燃一支烟。拿起报纸。张张报纸登的都是墨西哥城的消息,他默默地放下报纸,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把报纸推到他视野之外。
他在录音机里放了盘磁带,是肖邦的《练习曲:作品第十号》,把灯关上。黑暗降临,然后音乐降临……许久,许久,微微睁开眼睛,窗帘在夜风中轻轻飘拂,大衣柜的镜子有隐隐的反光,桌子和椅子显出暗暗的轮廓,床单是淡淡的白色,录音机的指示灯红的绿的闪光。
一阵敲门声打破了音乐的静谧。他把台灯扭亮时门已经开了。是孩子的母亲,抱着一床被子。她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长发遮住双肩,皮肤白皙,还穿着那条米黄色的裙子,没穿袜子,露出圆圆的脚趾,趿了双红拖鞋。
“今天孩子在你这儿睡一晚上,行吗?”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又看了看他,眼神平平淡淡,走进房间,把被子放在床上。转身往外走,脚步沉甸甸的,肥大的臀部一扭一扭。
他缓缓站起身来,房门口已是空空洞洞。过了会儿,对面房间的门一响。他站着。他的影子投向门口,拉得长长的,一直伸出门去。屋里没有了音乐,也没有了黑暗,只有光亮,而光亮仿佛令他战栗。
他久久站着,终于有鞋底蹭着地面发出的嚓嚓的声音,女儿终于出现在门框之下。她又单薄,又羸瘦,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手里抱着那只肥胖的猫。
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台灯被他挡住,他的影子落到她的脸上。她不看他,不声不响地走进房间,把猫放在床上。猫哑着嗓子叫两声就不叫了,屋里又是一片沉寂。他慢慢坐下了,眼睛还盯着女儿。她来到桌边,把书包放在桌上。
“作业做完了吗?”他的声音干干的。
女儿的头动了一下,像是听见了,又像是没听见。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地响,声音艰涩使人难受。她的背伛偻着,肩胛骨耸起。他看不见她的神情,她也一直不转过脸来。
忽然她不写了。是在注视着什么。一只大蚊子飞向台灯,在纱罩上撞来撞去。她慢慢凑过身去,突然一把抓住了。捏着翅膀举到眼前细细地看着,蚊子的那些瘦长的腿伸来伸去的。她仔仔细细掐掉它的翅膀,又仔仔细细掐掉尾巴,然后把它放在桌上。蚊子的腿显得更长了,还爬呀爬的,就像个畸形的蜘蛛。她双手撑着桌沿,探着身子,一直看到它死掉,腿都伸直了。
她收拾好书包,走到床边,把她的被子铺开。那只黑猫被吵醒了,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又倒下睡了。孩子的父亲起来,带得椅子一响。女儿转过身看了一眼,又把眼睛移开,开始脱她的裙子。灯光照着,她的皮肤黄黄的,一条条肋骨凸出,瘦得像隔年的纸糊的窗户。两条腿细长细长的,还有点儿弯。他缓缓地像个影子似的来到她的身后,把一只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她的肩膀瘦得没什么肉,皮肤挺粗糙的,左边肩上还有个小黑痣。
“我跟你妈妈……已经……离婚了……”
女儿扭过脸去,后背像是轻轻抽动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没告诉你……你太小了……”
孩子的头缓缓垂下去,一只手伸到背后解着裙子后边的拉链,动作很慢,有点儿机械。
“爸爸……等找到……就搬走了……找到房子……”
他的话越说声音越低,越说越不连贯,几近于耳语,又几近于梦呓。而女儿还是一声不吭,也不转过头来。他突然不说了,屋里又一次归于沉寂,仿佛窗外归于夜。只有女儿脱裙子发出的断续的、的声音。他坐下了,忽然从大衣柜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惨白惨白的,还有点儿歪斜。他的背后,昏黄的灯影里,女儿把裙子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她真瘦,身上哪儿都能看出骨骼的轮廓。他看着她钻进被子,她的所有动作都缓慢而机械。她的脸一直背向他,几乎像一张纸贴在墙上。他伸出手,手有点儿颤抖,把灯罩歪过来一些,黑暗就笼罩了女儿。她还是一动不动。
他又拿起一张报纸,还是墨西哥城的消息。他把目光移开,报纸在手上轻轻作响。忽然听见女儿低声唤道:“爸爸。”
他抬起头,一片微弱的光映到墙上,仿佛飘忽不定。女儿还是脸冲着墙,还是刚才那个姿势。就像是幻听,沉沉的夜里就像是从远远的地方传来种种声响:长的,短的,高的,低的,哭的,笑的……他还是来到床边,女儿还是没动。他俯过身去。女儿紧紧闭着眼睛,眼皮在微微打颤。她没睡着。
他把身体收回来。女儿两只手蜷在胸前,肩膀耸着,紧贴着墙躺着,像被什么挤压着似的。他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在床边坐下,躬下身,双手托着脑袋,闭上了眼睛。
女儿忽然翻了个身,把他惊动了,他扭过脸,觉得自己浑身都在痉挛。女儿仰面躺着,一只瘦瘦的手臂伸出了被子。他凑过去,看着她,又轻轻摸摸那只手。女儿没有反应,真的睡着了。他轻轻站起身,轻轻退离床边。
幽暗的光线里,女儿的面容显得安详,显得舒展,就像不是她似的;她轻微地打鼾,就像是从她肉体的深处释放出了她的灵魂。
他把台灯关上。随即就有一束淡弱的光投进窗来,他打了个寒战。那束光亮了桌子的一角,亮了床上的一条,一直把女儿的一只消瘦的手照亮,那只手竟有一点儿枯干的样子。他往窗外望去,不远的地方,孤零零的有一盏昏暗的路灯。
他把窗帘拉好,让屋里的一切都沉浸在黑暗里。
这一夜,女儿的鼾声是平和的,她的面容也是宁 静的。
他起来的时候,女儿还睡着,还睡得那么安详,那么舒展。阳光照着淡红的窗帘,淡红的光照着她的脸。她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儿淡淡的笑。那只黑猫醒了,凑到她鬓边嗅来嗅去。他把它抱开。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
对面房间的门紧紧关着,没有丝毫响动;过道什么都是淡淡的,白色的,而那个黑公文包还在衣架上挂着。他回手把门关上,走过去,拿件衣服把公文包盖住。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儿也看不见。
他回到房间,把女儿唤醒。
“还早着呢。”孩子揉揉眼睛,又打了个哈欠。
“今天早点儿上学去吧。”
他把衣服都递给她。她磨磨蹭蹭地穿上起来,听见猫在门外叫了一声。孩子的父亲不时催促她几句。孩子系好鞋襻儿,走出房间的时候,对面的门也打开了。那个男人出现在门口而她看见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
……
姐儿俩 001
走向 045
墨西哥城之夜 079
喜剧作家 091
世上的盐 209
后记 229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止庵的书写带我们重观文字的干净面貌,它立意在寻常日子里,但并不困囿于此,而是直击人心深处的感喟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