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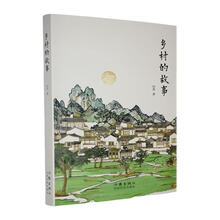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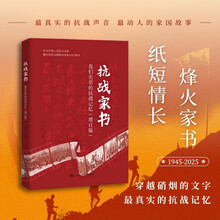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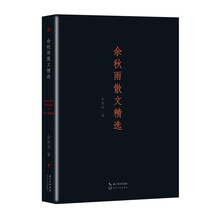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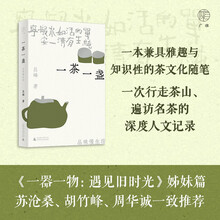
节气与哮喘,或农历中的梨
唐才子的才情由酒酿出,宋才子的才情由茶点出,明清两代才子的才情大抵是由妓女所熬出的。妓女是末世之药。现代的才子,只落得一个钱字——要由钱铸出了。
完全因为我,祖母才对节气恐惧的。童年时候,我每逢节气就大发哮喘。尤其春秋两季中出对子一般的节气,我很难逃脱得了这气喘吁吁的功课。灶头上粗壮的药罐白汽如虎,客堂里四把雕花木椅上坐着苍耳、辛夷、枇杷叶和蜈蚣——这些已经混为一谈的气味,有人嗜好这种味道。宝玉是个喜欢药味的性情人,他内心倾国倾城的凄苦随着沸沸药味而气化,气化出一位倾国倾城的林姑娘。黛玉可作代玉讲。读《红楼梦》我初觉得,宝玉内心世界并不丰富,他的一些行为都缺乏心理基础。后来我才认为这是曹雪芹的创造:他把贾宝玉的内心世界塑造成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可谐音为“能代玉”也。如此,小说也好看了。宝黛不能结合象征那个时期的精英必然人格分裂。从这点上看,《红楼梦》是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精神分析小说,寓言主义小说和想象小说。
于是,也成为我们想象的乐园。像药味,像节气,也像一只摆放在农历中的梨。为了治咳,我吃掉多少梨呢?我常想我如果活在二十世纪初的话,一定是个肺病患者。尽管这是最富有才情的疾病……傅山开出的药方,是一船梨,让他坐卧其间,顺流而下,一船梨从山西吃到河南,他在黄河上痊愈了。黄河是我们最大的药罐,诸子百家大抵于其间熬成。宜川的壶口其实可以叫“罐口”:天下黄河一罐收。药罐边的人影,哪怕目不识丁,也是文化人无疑,更何况风情万种的一代名妓呢,呼应在长江旁边。冒襄《影梅庵忆语》中写道:“姬当大火铄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枕边足畔六十昼夜,凡我意之所及,与意之所未及,咸先生之。”冒襄说的是董小宛。“茶花女”如果服中药,她就更能体会到小仲马的爱意。唐才子的才情由酒酿出,宋才子的才情由茶点出,明清两代才子的才情大抵是由妓女所熬出的。妓女是末世之药。现代的才子,只落得一个钱字——要由钱铸出了。“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即使年纪轻轻,都已老态龙钟,那种穿青衫拂水袖容华若桃已随所供奉的舞台一并消失。
就像熬药是中国行为,节气也是我们独特的创造。可以注册商标。我想我们的老祖宗是个语文老师,喜欢把一篇文章割碎,他把全年划分为二十四个段落:“立春”的段落,“雨水”的段落,“惊蛰”的段落、“春分”的段落……然后,就能较为方便地找出主题思想:我们的农事活动。大块文章遇到小刀割肉,老祖宗们是一帮揭竿而起的社会闲杂人员,统统加入“小刀会”。
其实更像一张课程表,天人合一的农事课程表。校长就是宇宙,班主任就是皇帝。皇帝不是被称为“天子”吗?就是校长的儿子。噢,让我们坐好了,不讲话,不做小动作,握紧锄头,两眼望前,看着一粒芒种在处暑里急如霜降。身在教室,胸怀世界,听校长的话,跟班主任走,小雪小寒,大雪大寒,无雪不寒。
但我已足足有十五年之久不关注节气了,我的哮喘在发育阶段不治自愈。现在每逢节气,我的紧张完全因为我的儿子。我不哮,他倒喘上。英国科学家近来的研究认为,哮喘更可能源于基因。也就是说我把国民党军队打跑,但留下的几个军统特务潜伏在我体内,通过一枚精子,在我儿子身上大搞破坏。我儿子的偏激、暴躁、缺乏毅力和疾病方面,简直是我归来的童年。看来除了有疾病基因,还有性格基因。甚至是命运基因。我很害怕他重复我的道路。想不到一枚精子竟能携带这么多东西,设想让一个人携带,他可能要满载一辆货车。生命中哪有不能承受之轻,当它还是一枚精子之时,就是负重的。深夜,我躺在我儿子身边,听着他艰难的呼吸,不觉泪流满面。只有一个哮喘者知道另一个哮喘者的痛苦。我觉得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有罪的,遗传性哮喘把他一年生活划分出二十四个段落。二十四个沉重呼吸的段落。这就使他往往想飞。一种轻盈。这也使他小小的心对天文有了兴趣,特别是对一些带有节气点的星座。
“金牛座,黄道星座之一。冬季星座中一个很美丽的星座。位于英仙座和御夫座以南,猎户座的西北。每年约五月十四日到六月二十三日太阳在金牛座中运行,小满、芒种和夏至三个节气点都在金牛座中。”
儿子犯病期间,常常会幻想,他粗促急断地说着:“我要做宇宙医生,把这些节气点都开刀开掉,它们是胆结石。”他妈妈开过胆结石,并带回家来。有一阶段,这些暗黄(稍渗出些绿意)的石丸是他最喜欢的玩具。我想到蒙克,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为了怕自己的疾病遗传给后代,就拒绝结婚。但一个人总是有结婚的冲动,特别是有点年纪又想过有规律生活的男人。再比如卡夫卡反复几个回合的订婚、毁婚,我认为很大程度这是他们医学文明的胜利。也是理性的胜利。
哮喘与节气这样密不可分,我几乎要把哮喘看成农业文明了。宇宙有一种节奏,一个人没有把握好,这个人就犯病。但没有哪种疾病像哮喘一样与宇宙的关系这般亲热,也这般立竿见影。不犯病时,我想我们的呼吸表达天籁,当气喘吁吁,这就是走调的独唱。如果把哮喘病人的呼吸记录下来,对照卫星云图,会不会发现暴雨或大水迹象?哮喘是我们的宇宙观出了毛病。“人是万物之灵”,现代哲学打破这个神话。从另外角度——怎样的角度呢?我想人还真是万物之灵,他是宇宙的一件模型,我们目前对宇宙的认知和对大脑的认知同在一条水平线上,就是说宇航工业与脑颅医学的进步是联袂的。人的求知欲也很可怕。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冥想的能力。冥想才是生活的重要部分。这点上,我很喜欢印度人。我们现在对地球形状有个新观念,即认为它是梨形。我想这与我们对子宫的了解差不多。子宫上大下小,像一只放倒了的梨。根据卫星探测资料,地球看起来也如一只梨。赤道部分鼓起,是梨的躯干;北极有点偏尖,仿佛梨蒂;而南极凹下,直似梨脐。这样,整个地球就是个梨形旋转体了。地球与子宫通过梨的形象而早已难分难解。多么奥妙,我们的身体与宇宙万象丝丝缕缕地牵挂着;形象美好,那梨形地球是暗处的子宫,更是一位丰臀细腰的女子,在茫茫宇宙之中像坐在岸边一样。
写到这里,我终于给这篇习作找到题目。师出有名。原本想叫《我们的节气》,或是《节气,药或梨》,似不够空灵。现在可以称之为《农历中的梨》,其中隐含节气的意思:因为节气毕竟是此篇中心。若无节气这中心,此作就失了气节一般。梨可谓是比喻——节气的比喻:那二十四个节气宛若二十四只黄澄澄的梨,挂在虚无枝头,被哮喘病人摘到。
又想起童年,我会背许多唐诗,但觉得哪首唐诗都和我无甚关系。破旧的《新华字典》所附“节气歌”,我认为才是了不起的杰作: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它帮助我对节气的掌握,于是逢其前后,我就给儿子熬药。现在只在煤气灶上熬了,全没有红泥小火炉的意境。熬药之际,内心不免有点苦涩,也会冷不防,一些活跃的想象跳将出来:
最早发现节气的人是个哮喘病患者,他根据自己的发病规律,摸索到这个自然现象,安排下部落里全年的农事。所以他也是最早的农民科学家和最早的农业部部长。行文至此,已是尾声。我又后悔了。决定把《农历中的梨》,改为《节气与哮喘》。尽管更实,但是妥帖。我终于舒出一口气。
——著名编剧 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