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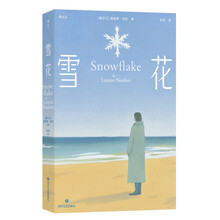
*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为中英双语版,特别收录诺贝尔文学奖、两次布克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普利策奖、布莱克纪念奖等得主J.M.库切的英文译本,属于国内首次引进。此书于1981年在意大利被评为当年*佳外语小说,并于1988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 作者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是一位南非作家、诗人和演员,是使用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堪斯语)写作的重要女性作家之一。她出版过多部小说、诗集和剧本,参演过《希望的大地》《四海姐妹》《第四帝国》等电影。分别于1977年和1991年获得南非荷兰语文学中*负盛名的赫佐格诗歌奖和小说奖。
*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私密独白,“我”在紊乱的时间和散落的场景中追忆,对奴隶制进行了一次虚构的拷问:贩卖、压迫、女性、身份、非洲和大自然本身……还有愉悦的性——同时又充分意识到其无限的痛苦和悲哀。主人公并没有徘徊在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分析上,在她狂热的回忆中,每段记忆都具有相同的重量,既拥有孩童般的纯真又拥有苦难和失落的真实。作者调度卓越的文学语言,打破语法和标点符号的限制,让文字和图像纠缠、流淌,一首如梦似幻的散文诗在我们眼前展演。
为了一座神秘的城市,一个奴隶女孩陪同她爱恋的主人和一队人,从非洲东海岸港口城市向内陆进发。但这一群人在陌生的地形里迷了路,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奴隶女孩,wei一的幸存者,在一棵猴面包树的裂隙中得到了庇护。在这里,她第一次完整拥有了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思想。她孤独地向猴面包树低语,追溯自己所有的过往,也反思自己的存在和意义,在这里重构自己的时间,与大自然共存,最后进行自我的殒灭。
那,就怀着怨憎吧。但我已禁止自己心怀怨憎。那,便怀着嘲讽吧。嘲讽就轻松多了。它透明坦率,漠不关心;我可以像一只缩进巢里的小鸟儿,退回我的树洞里,去笑话我自己。还有保持安静。也许保持安静,只是为了梦得更远吧,因为人的第七感,正是睡眠。
过去,我还常常为时间所困扰,当我仍然想要这日夜更迭以外的更多东西,当我执迷于计数,却不确定白日里那些我打瞌睡的时间是否该被算入夜晚,如果夜晚是平静无事,而白昼是忙碌无暇。睡眠就是夜晚。我有时是怎样将这夜晚无尽绵延的啊,在最黑暗的虚空里,尽可能地将自己蜷缩成最小的一团,额头顶着膝盖,好杀死那咬噬我五脏的痛楚;在攀缠着我的紊乱念头中,紧盯住一个颜色,并凭此固守住我自己,于是事后我便可以说,我的睡眠是蓝色的,是血一般的鲜红,又或者,是一片灰白过渡的阴影。我粉身碎骨地醒来,头晕目眩地坐起,踉踉跄跄,将一只满是尘土的脚放入长矛利刃般的阳光中。这平静而凶残的,整日不休地钻削着我居所的光束。
这是那些珠子出现以前的时间。那些珠子出现以后,时间便好打理得多了。如果我经常放纵自己睡去,那不再只是偶然,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只是逃避了。那时我才是活着的,我这样告诉自己。
珠子的到来,给了我计数日期的决心。我是几天前捡到它们的,计数则是后来才有的主意。我将这些新发现归入了那一小堆陶器碎片里。那些碎片也是好奇心引领着我从各处收集回来的。那是些距离这棵树或远或近的旅途,是我偏离了原本取水的路线,抱着或犹豫、或无聊、或心灰意冷的心情走上的杂散迷途。而那段取水之路,当时已几乎要被我踩出一条清晰可辨的小径了。
我正在开辟自己的道路,一如那些荒野走兽。这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像马鹿,不,不像马鹿或斑马,不像水牛或任何一种群居动物。它们互为各自感官的补充,共同应对危机,共同在那些一旦落单便无力招架的凶险面前存活下来。即便如此,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仍会沦为猎物,仍会孤独死去,一个接一个地,在各自的命数里。而我踩着我自己的道路,如此刻意,仿佛是要提醒自己,我已在此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我在此住得很好。又或者我应该说:我,同样在这里存活下来了,但是我只依靠我自己,就算是在我感觉大地之下无处不是蛇蛋的日子里,就算是那时,我也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尽量不要踩到它们。
我的小径,这条我如此轻柔地踩出的去往溪流的小径,纤细,微弯,绕过灌木丛和小树林,穿过平坦的草原——冬天正要为其染上绛红,再翻下最后一道陡坡,便可抵达阳光下波光潋滟的水面。这水面同我张开的双臂一般宽,两棵小马图米树守护着的地方,是我的饮水地。往下游去,是我洗澡的地方。而上游,也就是这段支流汇入主溪的地方,是大象的浅滩。
那时,我险些丧命象群脚下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我们年轻女孩间曾会互问的谜语:什么东西把它的生命装在肚子里?想必是那一大群轰隆作响的肚子,令我不安地傻笑了片刻,后又使我的喉咙一阵干堵,因为我那可怜的藏身之处,与象群间仅隔着一块突起的石头和几株芦苇。成群的脚掌从我身旁矫健地踏过,迈入溪流。水花溅起,它们平静地沐浴着。我缩进了我自己的怀里。没有人会像一个奴隶女孩那样,在如此严密的监护之下成长起来。我还可以补充一句,也没有人会像一个奴隶女孩那样,如此愚昧无知地成长起来。就算是我,一个闪耀的特例,在面对野生动物和它们的生活习性时,依然是如此的蠢钝,因为我的知识仅限于与象牙交易有关的那点信息。每隔一季,一只大象便会吞下一颗石子,而这些石子余生都会在它们那巨大的肚子里滚来滚去,滚来,又滚去。一切令我费解的宏大的事物,到头来都会被我降作荒谬可笑的东西来消化、理解,以证明我有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力量,然而这一个我却如此可笑地蜷缩在石头与芦苇的背后,像一只没有壳的鼻涕虫,一只不过我小指尖大小的软壳甲虫,在忐忑的假死状态里,等待这漫长而拖延的嬉戏的结束,那样我便可以像一个人类一样重新站立起来,环顾四周。最后一声大象的嘶鸣从对岸传来,我浑身僵硬地站起,拂去身上湿黏的泥沙,在轻抚着芦苇的微风中,瑟瑟发抖着。
现在,我与那群大象已经可以友好相处了,我偶尔还是会不小心闯入它们的浅滩和洗澡地点。只是,友谊这个词,总有些居高临下,并不恰当。我生活于此,它们生活于此。仅此而已。有时,从我所在的高地可以看见它们背部的曲线,在远方水面闪烁的波光中起伏、转动,我可以听见它们的嘶鸣,看见成对的象牙举起落下、一闪而过,而我仍然难以将眼前这一幕奇景,与我曾经佩戴过的光滑的镯子相连结。有些连结,仍然在回避着我。
如果我连从这猴面包树的入口到那一小堆陶器碎片和其他种种发现这短短一段路上的事情都不能悉数知晓,不知道去要这么多步,回来要那么多步,关于我的旅程,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我有时觉得它仿佛已经持续了一生,并且仍然在继续,仍然会继续,就算现在,我只是在围绕着一个地方不停地打转而已。
去要这么多步,我的脚却已经累了。当我把它们全都带回这儿时……我知道自己在收集的是什么吗?我又要用这些破烂东西……做什么呢?时间变成了珠子,也就变成了破烂。
在我记忆的纷繁小径上,盘桓着几个阴森可怖的身影,挡住了我每一次回望的目光。我认得这些身影。但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于朦胧中赫然耸现,像是人形,又像是个长满毛发的墙角,又或是一个旋转着的茅草屋,张开大口,要将我吞下、将我拖走,一个盛怒之下如暴风雨般向我袭来的大口,以惊人的速度咆哮而下,又在距离我一码开外的地方突然转向,徐徐漫步,诱我上前;我有时也会察觉到某种寂静的、扭曲的期待,随之而来的是明明白白的沮丧,当无数拧着我的尖螯变成灌木丛里松垂的卷须,当森罗万象全都消散,干脆利落,只留下一片深不可测的苍茫。我记忆里这些纵横交错的轨迹,比我一生实际所见的还要多。如果这些记忆是属于我的,如果我的探寻求索没有那样频繁地落空,以致各种蛛丝马迹都已烟消云散,我还能找到些什么吗?我无法追踪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各种各样不通往任何地方的小径,从我的居所向四面八方散射开去。无人铺设它们,它们就这样出现了。当然,刚到这里时,我也借用过动物们踩出的小道,因为除却那些不通往任何地方的小径,这地方便再没什么可利用的了。只是很快我便得出结论:我的思维方式与这里的其他生物并不互通。我得去寻找、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了。我找到了。
找到了,我说。胆战心惊。
最重要的东西,水,我无需特意去找。这一带有很多的水。你看得见,也听得到。我用我的礼物——一个鸵鸟蛋壳,盛起那溪水的涟漪。我将蛋壳捧于一弯清莹的、从一块粗糙的岩石上跳耀下来的水之弓中,以捕捉水的光泽和声音。我就这样一勺又一勺地盛着溪水,将这闪烁着、低语着的水之神灵倒入我的另一件礼物——一个陶土罐中,然后用双手慢慢举起这满满的一罐水,将其置于头顶,再屈膝拾起我的蛋壳勺子,沿着那条取水之路,走回我的猴面包树。
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稀树草原的食物;也发现了当我将食物摘下、挖出、捡起之时,是在与动物们相互竞争。那些果树并不为我萌芽、开花、结果,以抚平我的饥饿;那些块茎和根茎并不为我在地下生长、膨大;不是为了取悦我,绿心树才滴落它的花蜜;不是为了使我恢复精力,平冠树才恰好立于那片阴影的中心;斑点兰花迎风招展,不是为了愉悦我心;紫罗兰树在初夏绽放一树的花香,也同样不是为了我。
疣猪觅食后,一个新手开始仔细搜寻这片已被专家们翻了个遍的稀树草原。她学着像它们一样跪下,没有獠牙可用,她便试着用一根木棍戳刺坚硬的地表,没有对可食用的鳞茎和根茎天生敏感的嗅觉,她便试着用视觉尽力探寻。所获寥寥,她沮丧离开。狒狒觅食后,同样的情形又再度上演了,只是她再三确认过狒狒们都已离去,才大胆涉足了它们的领地。
我害怕狒狒的怪相,远甚疣猪、薮猪的獠牙。他太像我了。我害怕在他那张丑陋的脸孔上辨认出我自己的影子,它让我想起我在这里的劣势地位,想起我的浅陋无知。我为自己映照在他狰狞面目里的情绪与欲望感到羞耻,也为自己身形的精细优雅感到可笑,当我四肢跪地,粗野而拙劣地模仿着他的时候,我的精细优雅是多么的多余。我鄙视他,他的力量,他的狡黠,他对这世界显而易见的精通与掌控。我鄙视所有、每一只狒狒。那肥胖脸颊上的贪馋令我厌恶,那不堪入目的公开交媾,雌性那自轻自贱的乞求,她们在雄性强硬的大手和刺耳的辱骂下的躲闪,还有当你于兽群中发现他们时,他们那紧挨在一起的眼睛——我认为这也是贪婪的一种表现。我对他们了解得太多了,与我的品味实在不符。如果他们被关在笼子里,我定可以好好嘲笑他们一番。而至于他们对我又了解多少,在那些斜觑的目光之中,他们什么也没有透露。我想,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碍眼的东西,一个局外人,远远地隔离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
只有当我入睡时,我才完完全全地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统治着我的梦中时光,我心满意足地占据着我的梦。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于我自己,才有存在的必要。
我是在仓皇逃离一只狒狒哨兵的追逐时,闯入那块被夷平的土地的——在我看来是被夷平的。我摔倒在地,摊平四肢,大口喘着粗气。我转过身来。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要跳到我的指尖上。我鼻中呼出的阵阵气息,扑簌着干草微微颤抖的叶片。
我就那样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一只听天由命的食腐动物——对它而言,饥饿是一种熟悉的、可以等待着被平息的感觉。然后我看到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一些小小的光珠,在我睫毛间闪动着绿色与黑色的微光,又在我指尖于草叶间翻寻、触碰到它们的刹那,化作了一颗颗真实的珠子。我坐起,将它们从泥土和干枯的草根间挖出,捧在我的掌心。两颗黑色,一颗绿色。我将这无用的发现带回了我的树。
它们像花粉一般微小。我细细检查着它们,在其数目、颜色允许的范围内,将其排列成了数量有限的各种图案。我认得它们。第二天,我还想回到发现它们的地点,但却迷失了方向,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着,寄希望于我能辨认出一棵树,或者一个岩石山坡,因为那地方就紧挨着一个小山坡,这我是记得的,我还记得那些苍白的、梯子似的树根,那是一棵岩榕攀附于岩壁之上编织而成的;然而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游荡在这片稀树草原上,就像我还从未在此建立起任何系统,就像最初,我刚刚抵达这里时一样。
最初,没有时间,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思考顺序;也没有类别,因为生存的挣扎消除了所有的差异。现在我可以允许自己拥有分类的奢侈,以及对新旧知识的判断、运用。我甚至可以反思自己在做什么。我可以让我的思想连续而有规律地运转,不起波浪,不见涟漪。我可以将我的思想聚拢成圆,就像一个陶罐,再将其设想为清凉而精确的东西,就像一罐水。我可以让这陶罐的口沿高高突起,像喷涌的水柱,好抵御那些一不小心就可能将我穿透、将我完全填满的蓝色和黑色气体的缥缈虚无。我还在我的思想里装进了各色各样的物品,一排又一排,无穷无尽,无可计数。感谢上苍,我可以忆想出足够多的物品来堙没一切,即便我记得的一切都已消耗殆尽了,我还可以杜撰出新的东西。对付虚无,我有很好的办法。
此时此地,这几颗无需我去想象的小珠子,和我曾经见过的、佩戴在男男女女脖颈还有手腕上的是同一类。曾经它们还可以被用于交换物品,就像曾经我也可以被用于交换别的什么东西。当然,我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我曾经可以换得些什么。一枚圆环钱币。无数枚圆环钱币。另一个我不甚了解的领域,是钱应该怎么花。我的一切都是别人给予我的,这是一个奴隶女孩的特权。我头上的屋顶。我身上的衣服。还有食物——就我而言,是非常丰盛的食物。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这些珠子如此之小,在我存放它们的树瘤上几乎肉眼难辨;可是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它们。我了解我的树,就像一个盲人了解他的家。我了解它的每一处平面、凹陷、凸起、边缘,它的气味,它的黑暗,它那巨大的光之裂隙,就像我从未了解过那些我曾被吩咐睡在其中的茅草屋和房间,就像我只能了解属于我的,且只属于我的东西,我这从未有人踏足过的居所。我可以说:这是我的。我可以说:这是我。这些是我的脚印。这些是我火堆的灰烬。这些是我的磨石。这些是我的珠子。我的陶器碎片。
在我灰色的树皮之下,我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当我走出我的大树之时,我是骄傲地站立着的。只是后来,我怀疑自己是否又摆出了那副故作轻松、宠辱不惊的姿态——这是很容易培养的,我学会了在我的主人们面前摆出这副样子,想着留下一个好印象,会有我的好处,同时在这样的表象之下,心里却满溢自负,因为我手里握着的那一丁点琐碎的权力。
而如今我不可一世地伫立在这里,眺望着这片稀树草原。每一次我走出来,世界便是属于我的。每一次我从守护着我的树里走出来,我就又一次成为了一个人,一个强大的人。我远远眺望着这片风景,植物繁茂,动物成群,地平线上的紫色山丘斑驳零星,试图将它们围起。每一次从猴面包树的腹中重生,我都这般狂妄自大地伫立着。太阳勾画出我的影子。风为我穿上衣裳。我指着空气说:空气供养我活着。灌木莺啼叫起来,他是在啼叫着我的名字。我就是所有的一切,他啼叫着。
……
中文 1—126
英文 127—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