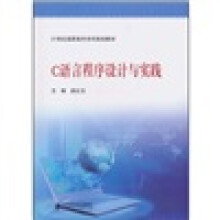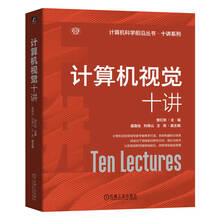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上海女声》:
摇到外婆桥
秦文君
外白渡桥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座桥,除了它,我没有用情更深的桥了,在我眼里它既是幸运的,也是怀有哀伤的。
我是闻着苏州河与黄浦江的气息长大的,刚出生那会,父母住在东大名路325号,紧靠着外白渡桥,从满月后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大人抱着出来认识这座桥。从部队转业不久的母亲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处工作,办事处的总部在中山东一路的太古大楼,而母亲所在的联合采购部在圆明园路上,单位的头儿答应在一间空的办公室里安一张小床,母亲可以把我带着来上班,雇一个帮手照料我,她抽空时过来哺乳。
我生命的第一年,每天清早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走过必经的外白渡桥,她雇来的小阿姨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婴儿用品。小阿姨是个眼神清亮,有些孩子气,像小麻雀那样天『生欢乐的农村女孩,她一路走一路逗引着我,婴孩是满心盛着快乐的,她一逗我就笑,年轻的母亲也跟着笑,我们笑声咯咯地来来往往,无忧无虑。
弟弟出生后东大名路的房子住不开了,全家搬到南昌路一机部的宿舍住,那里的房子好,家具也是公家配备的,缺点就是离外白渡桥远了点。不过我珍藏着自己戴花边帽骑玩具自行车在外白渡桥上玩耍的照片,它是温暖的外婆桥。
念小学时,处在最爱幻想的年龄,大人带我乘车路过外白渡桥时,我会感觉自己是这一带的老土地,喜欢伸长脖子嗅着四周烂熟于心的气息,每一次都东想西想地幻想半天。还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外白渡桥桥下的小西餐店吃西餐,我自豪地在桥板上踩动着,在桥上还找到稀奇古怪的东西:一颗生锈的小铆钉和一只玻璃弹子,玻璃弹子上面刻着印痕,我把它们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猜测着这是神秘而幸运的暗号。
进中学后懵懵懂懂地知道忧伤了,有一次心里冒出“我来自何方”的念头,寻根的愿望和自我意识渐渐强起来,曾悄悄地从外白渡桥走到东大名路,远远地看老房子还在吗,却没有勇气走进无比亲切的房子,似乎看一眼就安心了,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根基了。
1971年我初中毕业,知识青年都要下乡,我不想扛着锄头去种地,心里的浪漫情怀不灭,于是报名去拥有大片原始森林的黑龙江林场。可是政审竟没有通过,说是我的舅父解放前做过某银行的高级襄理,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舅父成了我的污点,招工者认为根正苗红的孩子才配去保卫北疆。中学老师知道舅父是优秀的人,更何况我当时连舅父的面都没见过,她打听到林场来招工的人住在浦江饭店,便连夜带我去浦江饭店说清缘由。
浦江饭店挨着外白渡桥,彷徨中的17岁的我在黑夜里细眺外白渡桥,听着黄浦江上轮渡汽笛尖锐的鸣喊,外滩上高亢的钟声,我感觉到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的低沉,它的老迈沧桑和淡定令伤感的我产生深深的信赖。看见它的那一刹那间,我就安心了,少年轻狂时虽不懂它过眼的历史烟云,也忐忑着此次前去是否能如愿,更不知命运将会带领我去何处漂泊,可是这座桥让我不再孤独胆怯,它好比知心长者,让我感觉到有一颗沉静厚道的心在陪伴我。
冥冥之中,我在生命最低潮的时期再次相逢我的外婆桥,续上了它与我千丝万缕的恩情。
终于获准去林场,离开上海前我没去任何地方,只去了外白渡桥,默默和它告别。对它有难言的依恋和不舍,觉得它代表我美丽的故乡上海,是我精神生命成长的见证,也是我怀乡的所在。
之后的几年,我在黑龙江历经艰辛,做粗重的力气活,住女生帐篷,一个帐篷住三十来人,每人的铺位不到60公分,一翻身就滚到别人的铺上去了,在艰难孤寂的每一天,我都盼着冬天,到了最冷的年关,就能放探亲假。每次探亲回沪我都会去外滩,到外白渡桥上走一走,外白渡桥就像一个寄托。我会长久地坐在看得见外白渡桥的地方,看着车来人往,感觉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位置,只有自己没有位置了,成了最心痛的客人。
1979年从黑龙江返城后,我的不少活动都在外白渡桥附近进行,我更深地瞳得我的外婆桥陈旧的哀伤,它曾见证了这座城市屈辱和凌乱的过去,还有,从大桥落成纪念铜牌上的英文看,桥名它应为“公园桥”,可自从1906年木桥拆除新建钢桥,外白渡桥的称呼,阴错阳差地给了这巍峨高大的钢桥,桥名被呼唤了百年,而它真正的名称“公园桥”却被人遗忘了。
它新的哀伤也许是被城市太多年轻的、赏心悦目的建筑所包围,不少与它匹配的具有上海风情的老建筑已经飞快地消失了。如果把绘制城市的蓝图比喻成作家的写作,我们可以快快地为出品而写,也可以慢慢地精心地不失尊严地写,一个体面的城市,它的苍老记忆是不该被割断的。
用现在的眼光看,外白渡桥的钢材并不上乘,建造过程中采用的铆接技术也早被淘汰。如今也再不会有“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的属于老早的风情,但外白渡桥和经典老建筑的存在留住上海沉甸甸的记忆,传承着一代一代人的精神和情感。
秦文君,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著、有《男生贾里全传》、《小香咕系列》和《会跳舞的向日葵》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