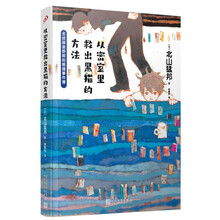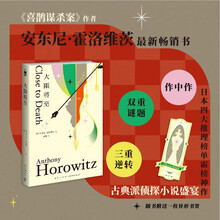青田Y字路
渐入盛夏,稻田里绿意盎然。田间的灌溉渠水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愈发清澈透明。风吹稻秧,掀起一片稻浪。
田园风景中延伸出一条笔直的公路,铺着沙石的道路在阳光下闪烁着白色的光芒。被这灼眼的光芒吸引着迈步前行,随即来到一个Y字路口。一棵巨大的杉树立在路边。
往右走,是茂密幽暗的杉树林。朝左走,是一片荒废的住宅基地,那一带原本将山林农地改造,计划建成住宅区,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被置之不理。
立于Y字路口的是一棵树龄过百的老杉,树干漆黑粗壮,在连日炽热的骄阳下,将它深沉的影子落在地面上。
喂,说话呀,臭婆娘!哑巴啦!
这时,从某处传来叫喊声。
声音来自不远处的中前神社院内。今天刚巧是“夏越祭”[1] [1]夏季六月份举行的祭祀庆典,驱除半年来的厄运。的最后一日,狭窄的参拜道上挤满了贩售炒面、烤紫菜年糕、鸡蛋仔等小吃的各式摊子,嘈杂喧闹。参拜者们滴落的汗水与食物中的酱汁、酱油、白糖混杂在一起。
院内深处阴凉的石板路上,正展开惯例的古董集市,沿路摆放着旧衣物、陶瓷器,还有一些杂货。叫喊声就是从那边传来的。
你们瞎了狗眼吗?这能是路易威登?这他妈是香奈儿?
院内更深处远离嘈杂的竹林里,停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后部车盖打开,后备箱里摆放着成排的假名牌。
当地小混混态度恶劣地大声叱骂一个中年女人,她好像就是兜售那些仿冒品的老板娘。不知是因为男人骂声太大,蝉鸣才更加嘹亮;还是因为蝉噪,男人才骂得愈响。
男人剃着光头,后脑勺上的刺青是一条锦鲤。鱼尾朝着鱼头的方向翘起来。男人满头大汗青筋暴起,每当他大吼,那尾鲤鱼就好似灵活地跳来跳去一般。
刚才还在挑选假名牌的顾客们,此刻都聚集在远处注视着这边的骚乱。他们中不乏有人回头张望,希望有谁能快点过来控制局面;却没有一个人主动挺身而出。
“在这摆摊儿,得到许可了吗?从哪儿钻进来的?”
小混混粗鲁地推了一下中年女人的头,女人被汗水沾湿的头发沉重地贴在头皮上。男人一把抓起她的头发用力拉扯,几乎要把头发揪下来。女人疼得面部扭曲。
“知道了……我知道了!”
她嘴里道歉,语调却带着怒气,口音不像日本人。
这语调更加激怒了男人,“哈?”
男人毫不留情地扇了女人一耳光,对着下巴又是一巴掌,揪住她的耳朵,似乎要用自己厚重的手掌将女人低低的鼻梁碾塌。每受一击,女人口中就发出唾液翻腾的声响。
围在远处观看的人群目睹这一幕之后,纷纷逃离现场。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男子从白色面包车后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但他无力阻止这一切。
男子是中年女人的独生子,名叫中村豪士。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个高中生,其实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
“干吗?”小混混朝豪士吼道。
豪士立刻后退几步。小混混紧逼上前,一只手仍抓着女人的头发,另一只手抓起豪士的衣领。
豪士紧缩成一团,稍有点内八字的双腿微微发抖。
“……请住手。”
古董集市离这里不过十几米,却异常遥远。豪士求救的声音似沉入水底,无法抵达那喧杂之处。
为了救儿子,母亲猛地抓住小混混的手臂。豪士趁机逃开,脚步凌乱地踩过卵石地,踢着枯草,一溜烟地朝古董集市主办方的白色帐篷跑去。
在帐篷中手拿罐装啤酒谈笑着的主办人们,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突然冲进来的豪士。他浑身是汗,就像被雨水打湿了一样。
“对……对……对不起!”
豪士从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对不起!请快去救人!”
主办方负责人藤木五郎吓了一跳。哪儿有人受伤了,还是有人打架?比起思考这些,他最先想到的是:“啊,这孩子会说话呀!”
还记得年幼的豪士是跟着母亲——日本名叫洋子吧——来到古董集市的。那个在母亲身边独自玩耍的乖巧孩子,不知不觉也长这么大了,最近还开始帮忙母亲搬运及管理商品。
他母亲人缘好,与客人和主办方的联络等,都由她一手操办。但毕竟他们母子卖的是假货,再怎么能招揽客人,作为主办方来说,都不便对他们表示欢迎。这么说来,将近二十年了,几乎每周都会与他们二人碰面,五郎却没有和那个孩子说过话。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事,五郎竟误以为豪士是不会说话的。毕竟作为晚辈不擅与自己这些长辈们交流或许亦属正常,但就连在古董集市里帮忙的其他年轻人,豪士也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
眼前的豪士浑身颤抖,主办人们终于站起身来。
“小伙子,发生什么事了?”
五郎向院内深处的竹林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像打狗一样在殴打豪士的母亲,女人跪在地上哀声求饶。
五郎不禁咂舌。
虽然不欢迎小混混来闹场,但作为主办方,名义上也不便为贩售假名牌的商贩出头。明知自己必须出面阻止,却迈不开沉重的脚步。
泪水充满了豪士的眼眶,他无助地等待着仍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五郎他们。此刻,只有他一个人干着急,那焦躁的神情像在无言地呼喊:“再不快去救人,母亲就要被打死了。”
五郎他们不情愿地朝事发现场走去。或许是因为喝了啤酒的缘故,才走了几步,汗水就一下子冒了出来。
强烈的阳光下,五郎等人悠哉游哉地走到竹林的阴影下。林间吹过习习凉风。
“好啦,好啦。”
五郎插到两人中间开始劝架。
小混混内心似乎也在等待五郎他们的到来,顺从地放开了女人的头发。
男人力道一定很大,他松手后,女人湿漉漉的头发依然翘起,头皮上渗出了血渍。
“真是的……”跟在众人后头走过来的五郎的妻子朝子看到血迹,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她扯下搭在自己脖子上的毛巾,压住女人流血的头部。
伤口似乎异常疼痛,女人发出低沉的呻吟。
“我说,这位兄弟,这位妹子,咱儿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把警察招来了就不好收拾了。”
五郎对二人说道,分不清他在劝哪方。
小混混吐了一口唾沫,冒泡的唾沫似乎散发着恶臭。五郎不由得后退几步。
五郎见过这个小混混。据说他之前在杉尾组混得不错,但杉尾组解散后,他也没有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时常在当地小酒馆里吹嘘已有别的组织要招他入会。然而事实上,如今这个年代,势力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没剩几个。他无非是靠着低保在维持生活。想必今天他也是无事可做到集市消遣时间,看到庆典热闹喧杂,回忆起自己耀武扬威的过去,便向卖假名牌的女人收起了保护费。
但是,女人当然没有义务交保护费给小混混。话虽如此,如果五郎这时候站出来为这母子俩出头的话,就等于允许贩售假货。
“啊呀,兄弟。”
五郎拍了一下小混混的肩膀,说道。
即便只是轻触一下对方的肩膀,五郎也透露出一股气场,让对方瞬间猜到他以前也是个江湖商人。
“今天就算卖我这个老爷子一个面子,别跟他们较真儿。当然,也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这妹子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倒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是吧,妹子。”
五郎转向女人,语气温和地说道。
“我,钱,没有……有,包。包给你。成吗?”女人商量道。她平时日语说得流利,现在却因恐惧而嘴唇发抖,话语变得凌乱。
小混混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后备箱里的假货,盘算能换多少钱。
“一个两个的可别想打发我。这些假货,卖了也没几个钱!”
五郎安抚他说,拿去送给经常光顾的小酒馆里的那些女孩子,她们肯定会高兴。男人似乎觉得不坏。
不知跑去哪儿的豪士这时突然出现,在母亲身旁蹲下,将湿毛巾敷在她肿胀的脸上。原来他刚才去为受伤的母亲浸湿了毛巾。
五郎的妻子朝子站起身来,对五郎轻声嘱咐道:“总之,你先把他们带过去,我过一会儿就拿几个包过去。”
“好。”五郎点头。
“啊呀,兄弟,先消消气,我们到那边去喝杯冰啤再说。”五郎推了推男人的后背。
男人们离开后,朝子对受伤的女人说道:“大姐,没事吧?撑不住的话,我带你去医院吧。”
“没事儿,对不起,让您担心了。”
“喂,小伙子,对面急救站的帐篷里有冰块,你去取一些过来,就说是藤木的太太让你去的。你妈的脸,得赶紧冰敷一下才行。”
豪士听到朝子吩咐,顺从地去取冰块。白色面包车旁放着看店人坐的折叠椅,朝子让女人先坐在那儿。
这片背阴处凉风习习,但也有很多蚊子。有一只蚊子停在朝子的手臂上,她迅速将蚊子拍死。丰腴白净的手臂上留下了红色的血迹,不知是谁的血。
“大姐,你们现在还住水无的町营小区里吗?”朝子挠了挠手臂,说道。
“是的……啊,不是,现在我儿子一个人住在那里。”女人回答。她的目光追逐着去取冰块的儿子的身影。
虽说是町营小区,但也就排列着几栋老旧的平房。房子大多无人居住,路过房门口,生锈的液化石油气罐映入眼帘,格外醒目。
“那大姐现在住哪儿?”
“我,现在,住新里的公寓那儿。”
“一个人?”
“不,和丈夫一起。”
“噢,大姐你再婚了?”
“证还没领……”
听到女人这么说,朝子突然想起来是有这么一件事。
五郎的那些旧相识里,有一个叫菅原的男人。年轻时到东京学习厨艺,结果没有出师就返回故乡,打日工维持生活,很快便迷上了赌博醉酒。
幸好,当时他从去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站前的停车场。不时向别人吹嘘:“一个车位五千日元,共九个车位。我每个月只要有这笔收入,就饿不死。”日工也不去打了,大白天就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晃悠。脸色一看就是肝不好。
五郎说过,大概两三年前,这个菅原好像和哪里的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
有一次,五郎偶然在小酒馆里遇到了菅原。
“那个女人是冲着我的财产才跟了我的。”菅原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
“就你那芝麻点儿大的停车场,还能叫财产呢。”五郎拍了一下他的头,说道。
菅原就此陷入了沉默,不甘心地继续喝酒。
那个和菅原同居的女人,就是眼前这位大姐。朝子是什么时候因什么事情得知此事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又有一只蚊子停在朝子白皙的手臂上,她伸手去拍却没有拍着,肌肤上留下了掌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