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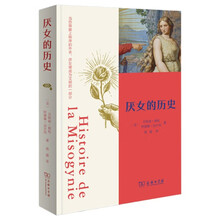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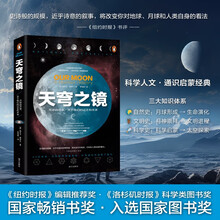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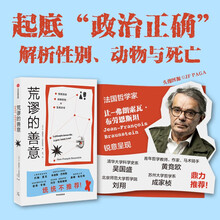





记忆是座矿脉,迎上去的时刻,记忆往往会拽住人的衣角,敦促自己飞针走线,织补破洞和深渊,那里收藏着年轻时的决心。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有个19岁的女大学生读到了一本残破的二手书,名字叫《第二性》,她欣喜若狂,感觉眼前的世界可以伸展得很远很远,融化了正在发生的“青春戏剧”。“剧场”的影子一直伴随着她,去攀援绝壁,不自由地去练习自由。有记忆,和有车有房有点不同,知道自己的来处,于是……
这本小书就这样呈现在您的面前了。
如果“作为女人”是我的处境意识,那么作为中国女人,我急切地想厘清“自我”的来龙去脉。
——张念
作者携带着feminism的力道,带领我们冲入哲学概念的丛林,去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拉康相遇。知雄守雌,将计就计,反戈一击。在惊险诡异的概念剧场,“厌女症”作为存在论的创伤,获得了诗学意义上的宣泄功效,而feminism继续逃逸、蜕变和生成,穿越幻象,使得“意义王国”中的无权者获得某种概念性形象,在政治机器朽坏的边境处,继续围海造田……
何谓女人
何谓女人,即关于女人的属性,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成为论证权力秩序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自然差异出发,亚里士多德认为:雄性动物比雌性动物高贵,这一原则适用于人类,从而使得性权力成为政治权力的原型。当然自然世界的这种差异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秩序的问题,但其用意在于以此来比附作为“政治动物”的人在属差上的特性。关于权力秩序的论证,古典政治学必须依托一个自然摹本,而性别则是最为显在的自然实存,于是基于生理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就成了无须深究的政治现象。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困境,就是说:他如何可以穷尽我们经验范围内的差异?再者,每个具体的规定性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个更一般的原则?比如亚里士多德非常尊重自然次序,而有关人的自然差异还包括长幼,长者的理智比幼者更为发达,按这样的逻辑,一个年长的女人就应该比年幼的任何人更应该具有理智,但我们发现,这里的长幼仅仅是针对男人而言。当亚里士多德说,有人天生就是奴隶,其理由是这类人不具备理性能力,这个依据是非自然的;那么,这个世界还存在这样的状况:有人天生就是女人,其服从的依据仅仅是自然差异,就是说,在关于政治服从的论证中,亚里士多德采取了双重标准,丧失了逻辑的一致性。
当然,亚里士多德做了一个补充性的论证,同样具有理性的男人与女人,后者在理性能力方面并非完全的丧失,比如像奴隶那样,而是她们的理性能力没有男人充分,而问题的关键是,他并没有指出,为什么女人的理性份额就天生比男人稀少,依然语焉不详。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是概念高手,每一个对象在他那里,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定性,但恰恰是作为概念的“女人”,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模糊性。
可以理解的是,亚里士多德是在政治实践的范围内来谈论女人的,他的目标并不是探究何谓女人——尽管看起来,他在做这样的工作,甚至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加明显——而是说对女人的属性规定必须服从于政治共同体的要求。这样一来,似乎表明,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属性先于共同体的形成,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于是,一种循环论证的链条就出现了:自然根据作为表象,被纳入思维活动之中,而思维的产物依然停留在自然的规定性之中,并没有超越某种必然性。
古典主义的必然性与偶然、无目的相关,而与此相对的理性,则与目的性与完善性相关,如果政治是人的一项理性行为,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合乎宇宙规律的第二自然的话,克服必然性之于女人而言,就是一项如何成为女公民的事业,否则,合乎目的性的要求怎么才能得到满足呢?如果在政治共同体中,女人还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其存在的规定性难道不是与政治共同体的理性相对立的吗?
是的,一旦理性问世之后,女人总是作为难题而出现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政治学》与《理想国》的争辩,最关键的还不是哲学史所说的唯心与唯物之争,全然的唯心与全然的唯物,之于“女人”似乎都不成立。
在讨论《政治学》与《理想国》有关“女人”的著名争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争论发生的理论前提,就是柏拉图的“女公民”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成为了一种“服从的德性”,因为亚里士多德误解了《蒂迈欧篇》的“切诺”。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作为宇宙生成的神秘力量的“切诺”(载体),理解为一种完全消极被动的存在,只是具备可能性的“质料”,理性与质料的关系正如造房子的人与树枝的关系。在柏拉图那里,“理型”并不具备空间性,否则理型进入“切诺”,就变成了空间进入空间,在此,“切诺”如德里达理解的那样,其腾让与馈赠的风范就消失了,而“空间”则成了一种侵入性的行为产物。亚里士多德批判了“理型”说,认为“理型”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几何数”,而他给出的“形式”概念是有空间性的,是形式激活了质料的潜在性与可能性,使之成为实存之物。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型”与“切诺”共同创造了实存意义上的万物,他们之间是一种共在共存关系,而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必然意味着可感事物的规定性不可能单方面地来自“形式”的能动性。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雌性动物一次就可以受孕,而雄性动物可以多次授精,他的用意在于“形式”进入质料,如生命的受精行为,形式与其制造之物,如“一”与“多”的关系,并强调这种状况适用于其他的本原。但是,作为生命“质料”的“雌性动物”,与树枝之类的质料区别在于,成为房子的树枝可能不再是树枝了,但“子宫”依然还是“子宫”。
《形而上学》的另一个疑点还是关于性别,就身体作为创造生命的“质料”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与女人没有属差,双方都不具有实存性。如果遵循这个原则,那么《政治学》之中所规定的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依据何在?男人比女人更具理性的根据又是什么?而最有现实感的亚里士多德在此必须向《论灵魂》求援,灵魂的级差直到基督教出现以后才崩解了。因此,就政治实践而言,《理想国》第五卷干脆跳开理性能力的性别差异说,并与《蒂迈欧篇》的“切诺”相呼应,但疑虑依然存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理性与城邦的关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城邦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有所不同,城邦并非一个取自家政原型的自然共同体,而是一种高级的活动,与理性高度匹配的结果就是,城邦即政治活动必须抽离自然。尽管灵魂类别说贯穿在《理想国》中,但聚焦性别问题的第五卷指明:男人与女人的生理差异不同于一个男医生和男鞋匠的差别,这将意味着性别差异与灵魂等级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在女人可否成为城邦护卫者,即肩负起政治责任方面,柏拉图的回答是肯定的。同为护卫者,最为自然的男女情欲该如何处置,就是说在自然差异面前,柏拉图将此差异作为一种共产设想的条件,而非起点来论证取消家庭的可能性。第五卷的激进色彩有目共睹,柏拉图认为家庭私有之私有性,首先在于一个男人之于一个女人的专有性,那么破除这种专有属性的关键就是消解婚姻制度。当亚里士多德的性别属性从自然差异一跃成为德性差异的时候,我们看到,男人的跳跃是成功,他成为父亲的自然事实,在希腊法典中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意味。同为创生小公民这项生育活动的参与者即女人,成为母亲并没有多大的政治内涵,女人其实还是滞留在自然的范围,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在自然家庭的框架中来辨识女人的。
柏拉图显然同等对待生育活动的双方,为了保持理性论证的连贯性,他甚至认为所有的孩子也应该为城邦所共有,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按照理性原则的优先性,为城邦所有肯定优先于为家庭所有,这和现代观念如此相近:在宪法规定中,抽象法人的公民身份优先于家庭的私有成员身份,就是说,某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其次才是某人的孩子、妻子或者丈夫。理性与自然的对立是剧烈的,这里涉及柏拉图之于城邦的一种绝对的理性立场,政治生活恰恰是人彻底告别自然状态、趋向完善的共享的路径。
尽管亚里士多德也坚持政治活动的理性规定,但其权力模型却带有自然的意味,这样的差异决定了两位哲学家之于女性政治身份的不同态度。关于如何处理城邦与家庭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自然持存,即生物意义上的人来谈论家庭的功能,而相对于家庭生活而言,城邦生活更高级,更能显示人的尊严,是一种更好的值得过的生活。这样一来,奴隶、小孩以及女人因为其理性能力的缺失或者不完善,自成一类。在此,合乎目的性的城邦与合乎必然性的家庭,隐含了关于自然的两种理解。合乎目的性的城邦,顺应自然法则,这里的自然如《蒂迈欧篇》中的宇宙,是在神意的最佳选择中出现的,即自然规律就是理性的。而合乎必然性的家庭,则是一种偶发的自生现象,与城邦秩序相比,家政秩序的形成似乎没有太多的理性参与,只是满足人的本能需求而已,比如吃喝与交配,因此,生物性本能是与古典政治学中的“自然秩序”相对立的。
当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同样坚持灵魂等级的自然正当性,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为了保持住生物性存活的现实经验,为这个灵魂等级增添了一个新的级差,那就是性别。就人类世界而言,比城邦秩序更为原始的生物性存在,扰乱了政治理性的融洽与统一,包括后来坚持享乐原则的伊壁鸠鲁学派,以及对身体蛮力保持关注度的斯多葛学派,都试图回答比完美的自然秩序更加原始的力量,即人的问题该如何纳入哲学家的思考之中。《政治学》显然更加注重人的事实,而政治的发生也只能是在人群之中,那么,可不可以有一种政治秩序既能符合超然理性的规定,而同时又建立在人的动物性前提之下?也就是说:在进入城邦生活之前,人从哪里走来?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是家庭,而柏拉图则认为,没有一个前政治的存在,人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动物性的,而不可能同时是两者,即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在共同的动物属性之上,高贵与卓越不可能是天生的,如果说一个人天性高贵,此处的天性(nature)显然不是指生而高贵,而一定是在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中来指认。
于是,关于何谓女人的争议就在两个方向产生了分歧:在城邦理性的眼里,性别是不存在的,自然的多样性统一在理性的政治权力之中;在人性经验的方向——这个方向还必须借助于动物界的雌雄差异,性别被体验为理性、情感以及行为方式上的不同,有时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自然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女人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物,因其被划入家庭范围之中,女人的存在也就与城邦生活是相对立的。因此,作为人类成员的一半,女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被政治生活所排斥的存在,这是有关女人的最为古老的困境,这个悖论一直延续到现代政治学的左右之争中。
显而易见的是,古典政治学的基础在于自然正当,即服从的理性根据来自自然秩序,这个被神意所选择的结构是最恰当最完善的。而政治体成员的差异,即德性差异,是统治秩序的原型,作为先验规定,主人与奴隶都是天生的,但同时又指出,城邦的目标在于让人向好向善,是政治促进了人的完善性与优异性,那么,既然天性已经注定,完善性的进程目标其实就意味着如何对待并处理这些差异,使得各不相同的人群能够共同生活。而要达成共同生活的目标,就必须服从这些自然差异所形成的秩序,这样一来,完善性就成了一个虚置的口号。因为自然秩序一直存在,对完善性的理解,应该与可能性相关,在此已经暗含着一种超越,即如何超越这种先在的自然规定,才是政治的宗旨。
当城邦的正义体现为是其所是的时候,权力模型的设置是静态的、恒定的,而非生成性的,它隐瞒了柏拉图宇宙论的“切诺之谜”,而只有超越才有可能提供一种动力模态。当女人的属性被限定在自然规定之中时,我们的问题是,政治之于女人意味着什么,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奴隶。如果本分,即是其所是,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应有的样子与责任,那么政治的目标显然就不是完善,而是怎么让统治长治久安,政治的稳定性成了第一诉求。这类似于儒家所设计的道德位序结构,正因为没有一个灵魂等级来规定人的属差,所以古希腊的“是其所是”在东方智慧中对应的是“得其位正”,人并非预先带着某种自然属性来到这个结构之中,而是这个整全的朴素的宇宙观的结构决定了你是什么,使得这种结构的压迫性更加隐蔽。
因此,儒家学说中的女人,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结构性的,这个结构的奠基如《易传》所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此,不需要政治生活为中介,去厘定人的属性,这属性由天道直接昭示男人女人应该承载的道义,这道义就是“夫妇之道”。夫妇之道在《序卦》列为三纲之首,即夫妇之道作为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的自然原型,使得三纲伦常被纳入自然秩序之中。这样一来,天予之体的男与女,一出生就自然承接了乾坤之道,而由自然的乾坤之道化成人伦之道的前提是夫妇,就是说男与女不是生理结构上的唯物辨识,或者基于这种自然差异,不是这类人与那类人的差异,而是在夫妇关系中,一种抽象的自然能量(阴阳)才可显现为道德现象或者政治现象。因此,从天尊(上)地卑(下)说取象而成的道德位序结构,其不可化约的基本构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人的属性,而是一种关系,更进一步地说,强调的是夫妇关系之中的相互性,这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女人属性不同,但此处的相互性一方面与生生原则暗合,另一方面生生活动的结果这不可确定的可能性受制于位序结构。取象自然天地的男女,阴阳互济的相互性嵌入夫妇关系之中,就是说正是夫妇之道以及次生的父子之道的自然正当性,作为君臣关系,即政治服从的根源,来自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自然取象,这样一来,所有处在服从位序之上的个体,同属于阴性,从而担保了非自然的君臣关系的正当性。与古希腊政治学不同的是,东方的权力关系来自道德位序结构,并统摄在阴阳的二元性之中,合乎阴阳互济之自然正当,无须思维抽象,直接取象自然,现象就等于本质。
这个由生命创生形象,由最核心的男女之道予以强调的阴阳互济,作为推演人间事务的动力学机制,夫妇之道成为道德理性的逻辑起点。《大学》有云:“夫妇之道,造端乎人伦。”在此自然与人为并没有严格的对立,人间的道德现象与政治现象非关创造,只不过是大化运转的一个部分与环节而已,只需顺应天道即可。男女之道作为原动力,外推到道德与政治,这样的核心圈层结构,似乎达到了无可辩驳的圆融性,但阴阳两种能量共同具有的主动性,即它们共同的相生相济的自然运作法则,被固化为伦理结构中的位序说,当代表阴性力量的女人被践行为“妇”的时候,“妇道”在文化史中,显然变成了一项严格的道德规程,这样一来,何谓女人的问题,尽管逃脱了本质主义的规定,但并没有获得生生—互济的盎然天机,而是落入了一种道德规训的巢窠之中,同样背离了哲学思考的方向,因为自然成像的这张底片本身,也有可能是千变万化的。
导论 女性主义的哲学气质
事物的来处:一/二
作为思想调性的女人
何谓女人
这是/不是女人
第一章 黑格尔意识哲学中的“女性迷踪”
伦理起点——兄妹关系——爱欲辩证法—— 城邦-国家精神
第二章 启蒙/反启蒙辩证中的“女人”
自然/文化——尼采的女人观——启蒙道德:焚毁女人
第三章 存在主义的处境意识与“第二性”
表象氛围、处境——我是我的身体——亲密关系中的他者——绝对控制/绝对服从
第四章 精神分析的研判:女人不存在
性别伤口——以父之名登陆语言——忧伤和欲望——女人想要什么
第五章 思考差异成为女人
性别零制度——穿越认同幻象——差异与虚无——激进的伦理维度
第六章 人的平等与性别差异
不平等的另类起源——差异伦理——平等的再生性
第七章 差异原则,或安提戈涅的三副面孔
历史终结——男子气的绝境——伦理的善好与美学的险恶
第八章 身份政治及其僵局
父权制家庭——资本主义的政治衰竭——权利外套
第九章 女性欲望与革命的女性主义
独立之外的解放——女权主体——差异就是政治决断
余论 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
后记
有关男女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的记忆,其实是我们在反思判断中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张念想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工作。而在黑格尔那里,比如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及兄妹之情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哲学问题:我们到底是把“事情”之“事”与“情”当成结果(然后寻求原因)还是当成存在(阐述其意义)。显然,张念关注的也不是原因,而是意义;于是“存在之痛”就成为另一个相应的话题。我认为就中文写作而言,这是某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就这一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毕竟,伤(殇)与痛(异)是我们在讨论男女问题时绕不过去的概念。
——哲学家 陈家琪
这是一出黑格尔、拉康和女权主义者Z之间的《三岔口》,真是越打越缠绵,打出了学术,打出了激情,还打出了票房!别围观!让我们跟着作者,冲出去,在女人中成为女人!
——哲学家陆兴华
张念不屈不挠地在中国女性主义运动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许久以来,在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她勇敢而清醒的介入形象。这次,她又让我们听到了女性主义的哲学呐喊!
——理论家 汪民安
以德里达术语来讲,女性主义更多地属于其所说的石祖中心主义议题,而非逻各斯中心主义议题,这也是为何女性主义更多地在经验科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社会学等)而非哲学中被讨论的主要原因。然而,女性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纵贯主体存在始终的特殊彼者,却无法被哲学以多种逻各斯技巧(如辩证法及各式还原)所取消或隐藏,而总会以多种异质的、隐晦的、难言的方式存在于逻各斯之侧。拉康在晚期指出,苏格拉底之所以在其最终时刻拒绝妻子参加,是为了确保其作为“例外”的哲学之父位置,但这难道不可理解为也是为了确保逻各斯的同一性与纯粹性吗?
因此,除了张念所特有的女性—哲学家立场之外,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在逻各斯与石祖两个维度上同时讨论女性主义。这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角与观念(如其实际上在反面也点出了“男性之痛”与“哲学之伤”),也同时引入了“逻各斯—石祖”两者之间关联这一更为宏大的议题。
——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学博士 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