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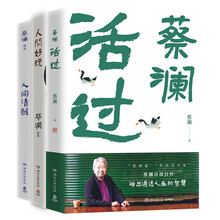









《自深深处》前后矛盾,爱恨交织,沉痛却又轻灵,是王尔德一部美妙而难以言说的作品。精装中英双语本,香港城市大学朱纯深教授精心修订译作,新增译序、译后记和注释。
1895年,王尔德与同性情人波西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对簿公堂,被判“有伤风化罪”,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在狱中,王尔德给波西写下这封文学史上的著名长信,痛斥波西的种种不是,也探讨了耶稣、爱恨和文学,又似对两人的未来有所期待。
1897年1-3月
亲爱的波西:
经过长久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定还是由我写信给你,为了我也为了你。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在漫长的两年囚禁中,除了使我痛心的传闻外,连你的一行书信,甚至一点消息或口信都没收到。
我们之间坎坷不幸、令人痛心疾首的友谊,已经以我的身败名裂而告结束。但是,那段久远的情意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而一想到自己心中那曾经盛着爱的地方,就要永远让憎恨和苦涩、轻蔑和屈辱所占据,我就会感到深深的悲哀。你自己心中,我想,将会感到,当我孤独地卧在铁窗内服刑时,给我写信要胜过未经许可发表我的书信,或者自作主张地为我献诗;虽然这样世人将一点也不知道你的所为,不管你选择怎样充满悲哀或激情、悔恨或冷漠的言辞来回应或者叫屈。
毫无疑问这封信中所写的关于你还有我的生活,关于过去和将来,关于美好变成苦痛以及苦痛或可成为欢乐,个中很有一些东西会深深伤到你的虚荣心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一遍又一遍地把信重读吧,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除灭。假如发现信中有什么你觉得是把你冤枉了,记住应该感谢世上竟还有什么错失,可以使人因此受到指责而蒙受冤屈。假如信中有哪怕是一段话使泪花蒙上你的眼睛,那就哭吧,像我们在狱中这样地哭吧。在这儿,白天同黑夜一样,是留给眼泪的。只有这个能救你了。假如你跑到你母亲跟前告状,就像那次告我在给罗比的信中嘲弄你那样,让她来疼你哄你,哄得你又飘飘然得意忘形起来,那你就全完了。假如你为自己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过不久便会找到一百个,那也就同过去的你毫无二致了。你是不是还像在给罗比的回信中那样,说我“把卑劣的动机归咎”于你?啊!你的生活中可没有动机。你只有欲念而已。动机是理性的目标。说是在你我的友谊开始时你年纪还“很小”?你的毛病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对生活懂得太多。少男岁月如晨曦初露,如鲜花初绽,可那纯洁清澈的光辉,那纯真向往的欢乐,已被你远远抛于脑后了。你脚步飞快的,早已从“浪漫”跑到了“现实”,迷上了这儿的阴沟以及生活在里边的东西。这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惹上麻烦,向我求助的;而我,以这个世界的眼光看是不明智的,却出于怜悯和善意出手相助。你一定要把这封信通读,虽然信中的一词一语会让你觉得像外科医生的刀与火,叫细嫩的肌肤灼痛流血。记住,诸神眼里的傻瓜和世人眼里的傻瓜是大不一样的。艺术变革的种种方式或思想演进的种种状态、拉丁诗的华彩或元音化的希腊语那更丰富的抑扬顿挫、意大利托斯卡纳式的雕塑、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调,对这些,一个人可以全然不知,但却仍然充满最美妙的智慧。真正的傻瓜,诸神用来取乐或取笑的傻瓜,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这样的傻瓜,我曾经当得太久了,你也已经当得太久了。别再当下去了。别害怕。恶大莫过于浮浅。无论什么,领悟了就是。同样记住,不管什么,你要是读着痛苦,那我使它形诸笔墨就更加痛苦。那些无形的力量待你是非常好的。它们让你目睹生活的种种怪异悲惨的形态,就像在水晶球中看幻影一样。蛇发女怪美杜莎,她那颗能把活人变成顽石的头颅,允许你只要在镜中看就行。你自己在鲜花中了然无事地走了,而我呢,多姿多彩来去自由的美好世界已经被剥夺了。
一开头我要告诉你我拼命地怪自己。坐在这黑牢里,囚衣蔽体,身败名裂,我怪我自己。暗夜里辗转反侧,苦痛中忽睡忽醒,白日里枯坐牢底,忧心惨切,我怪的是自己。怪自己让一段毫无心智的友情,一段其根本目的不在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友情,完完全全左右了自己的生活。从一开始,你我之间的鸿沟就太大了。你在中学就懒散度日,读大学就更不堪了。你并没有意识到,一个艺术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作品的质量靠的是加强个性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要求思想的默契,心智的氛围,安详悠静的独处。我的作品完成后你会钦佩赞赏:首演之夜辉煌的成功,随之而来辉煌的宴会,都让你高兴。你感到骄傲,这很自然,自己会是这么一位大艺术家的亲密朋友,但你无法理解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那些必备条件。我不夸大其词,而是绝对实事求是地要你知道,在我们相处的那个时候,我一行东西都没写。无论是在托基、戈灵、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你在身旁,我就才思枯竭,灵感全无,而除了那么几次以外,我很遗憾地说,你总是呆在我身旁。
比如,就举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记得是在1893年9月,我在圣詹姆斯旅馆租了一套房间,这完全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写作,因为我答应过约翰·赫尔写个剧本却完不成合约,他正催着要稿呢。第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我们就你的《莎乐美》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这的确并不奇怪。因此你就退而给我写些愚蠢的信纠缠这件事。那个星期我完成了《理想丈夫》的第一幕,所有的细节都写好了,同最终的演出本一样。可第二个星期你回来了,我简直就无法再动笔了。每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来到旅馆,为的是有机会想想写写,省得在自己家里,尽管那个家够安宁平静的,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打搅。可是这份心思白费了。十二点你就驾着车来了,呆着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到那时我只好带你去皇家咖啡座或伯克莱用午餐。午餐加上甜酒,一顿通常吃到三点半。你到怀特俱乐部歇了一个钟头,等下午茶时分又出现了,一呆就呆到更衣用正餐的时候。你同我用餐,要么在萨瓦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照例我们要等到半夜过后才分手,因为在威利斯菜馆吃过夜宵后这销魂的一天不收也得收了。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过的生活,天天如此,除了你出国的四天外。当然我过后不得不到加来去把你接回国。具有我这样心地禀性的人,那情形既荒诞又具悲剧性。
现在肯定你必得意识到这一点吧?你一个人是呆不住的:你的天性是这样迫切执拗地要求别人关心你,花时间陪你;还要看到你缺乏将心智持续地全神贯注的能力:不幸的偶然——说它偶然,因为我希望已不再如此——即你那时还无法养成在探索智性事物方面的“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你这个人从来就不能优雅地玩味各种意念,只会提提暴烈的门户之见——这一切,加上你的各种欲望和兴趣是在生活而不在艺术,两相巧合,对于你本人性灵教养的长进,跟对于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工作,具有同样的破坏性。你现在必得明白这一点吧?把同你的友谊,跟同像约翰·格雷和皮埃尔·路易斯这样还要年轻的人的友谊相比时,我感到羞愧。我真正的生活,更高层次的生活,是同他们和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同你的友谊所导致的恶果暂且不说。我只是在考虑那段友谊的内在质量。对于我那是心智上的堕落。你具有一种艺术气质初露时的萌芽迹象。但是我同你相遇,要么太迟要么太早了,我也说不清楚。你不在时我一切都好。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那年十二月初,我劝得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后,就重新拾起、再度编织我那支离破碎的想象之网,生活也重归自己掌握,不但完成了《理想丈夫》剩下的三幕,还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佛罗伦萨悲剧》和《圣妓》。而这时,突然之间,不召自来,不请自到,在我的幸福生死攸关的情形下,你回来了。那两部作品有待完稿,而我却无法再提笔了。创作它们的那份心境永远也无法失而复得了。你本人现在已有一本诗集出版,会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不管你承不承认,这都是你我友谊的核心里一段不堪回首的真事。你同我在一起时便绝对是我艺术的克星,而竟然允许你执拗地隔在我和艺术之间,对此我羞愧难当,咎责难辞。回想起来,你无法知道,你无法理解,你无法体谅。而我一点也无权指望你能做到这些。你的兴趣所在,不外乎餐饭和喜怒。你的欲望所寄,不过是寻欢作乐,不过是平平庸庸或等而下之的消遣享福而已。这些是你禀性的需要,或认为是它一时的需要。我本来应该将你拒之门外,非特别邀请不得登门。我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的软弱。除了软弱还是软弱。半小时的与艺术相处,对于我总是胜过一整天地同你厮混。在我生命的任何时期,对我来说任何东西只要与艺术相比,便无足轻重了。但就一个艺术家而言,如果软弱使想象力瘫痪,那软弱就不亚于犯罪。
我还怪自己让你给带到了经济上穷困潦倒、信誉扫地的穷途末路。我还记得1892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同你母亲一道坐在布莱克奈尔秋风渐黄的树林里。那时我对你真正的性格知道得很少,有一次在牛津同你从星期六呆到星期一,而你来过克莱默同我呆了十天打高尔夫球。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你身上,你母亲开始跟我说起你的性格。她说了你的两大缺点,你虚荣,还有,用她的话说,“对钱财的看法大错特错”。我清楚记得当时我笑了,根本没想到第一点将让我进监狱,第二点将让我破产。我以为虚荣是一种给年轻人佩戴的雅致的花朵;至于说铺张浪费嘛——我以为她指的不过是铺张浪费——在我自己的性格中,在我自己的阶层里,并不见勤俭节约的美德。可是不等我们的交情再长一个月,我便开始明白你母亲指的到底是什么。你孜孜以求的是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无休无止的要钱,说是你所有的寻欢作乐都得由我付账,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过些时候这就使我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你抓住我的生活不放,越抓越紧。总而言之,你的铺张挥霍对我来说是乏味透顶,因为钱说真的无非是花在口腹宴饮,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乐上。不时的让餐桌花红酒绿一下,可说是件赏心乐事,但你的无度却败坏了所有的品味和雅趣。你索取而无风度,接受而不道谢。你养成了一种心态,认为似乎有权让我供养,过着一种你从未习惯过的奢侈生活,而因为这一点,如此的奢侈又让你胃口更大。到后来要是在阿尔及尔的哪家赌场输了钱,第二天早上就干脆拍个电报到伦敦,要我把你输的钱如数存到你银行的户头上,事后便再也不见你提起。
我告诉你,从1892年秋到我入狱那一天,看得见的我就同你以及为你花了不止5000英镑的现金,还不算付的账单呢。这样你对自己所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明白一二了。你认为我是夸大其词吗?我与你一起在伦敦普普通通的一天的普普通通的花销——午餐、正餐、夜宵、玩乐、马车及其他——大概在12至20英镑之间,每周的花销相应的自然也就在80到130英镑之间。我们在戈灵的三个月,我的花费(当然包括房租)是1340英镑。一步一步的,我不得不同破产案的财产管理人回顾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太吓人了。“平实的生活,高远的理念”这一理想,当然了,你那时还无法体味,但如此的铺张奢侈却是令你我都丢脸的一件事。我记得平生最愉快的一顿饭是同罗比在索赫的一家咖啡馆吃的,所花的钱按先令算,数目同你我用餐时花的英镑差不多。同罗比的那顿饭使我写出了第一则也是最精彩的对话。意念、标题、处理方式、表达手法,一切全在一顿三法郎半的套餐上敲定。而同你的那些挥霍无度的餐宴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只记得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了。你的要求我频频迁就,这对你很不好。你现在明白了。我的迁就使你更经常地伸手索要,有时很不择手段,每次都显得粗鄙低下。太多太多次了,宴请你而不觉得有多少欢乐或荣幸。你忘了——我不说礼貌上的道谢,因为表面的礼貌会令亲密的友情显得局促——我说的不过是好朋友相聚的雅趣、愉快交谈的兴致,那种希腊人称之为τερπυòυκακ?υ的东西;还有一切使生活变得可爱的人性的温馨,像音乐一样伴随人生的温馨,使万物和谐、使艰涩沉寂之处充满乐音的温馨。虽然你也许觉得奇怪,一个像我这样潦倒的人还会去分辨这样丢人和那样丢人的不同,但我还是要老实地承认,这么一掷千金地在你身上花钱,让你挥霍我的钱财,害你也害我;做这等蠢事对我来讲、在我看来,使我的破产带上了那种庸俗的由穷奢极欲而倾家荡产的意味,从而令我倍加愧怍。天生我材,另有他用。
但是我最怪自己的,是让你使我的道德完全堕落。性格的根基在于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却变得完全臣服于你。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是千真万确。那些接二连三的吵闹折腾,在你几乎是出于肉体的需要,可同时又使你的心灵和肉体扭曲,让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听不敢看的怪物;你从你父亲那儿继承的那种可怕的狂躁,使你写出令人恶心的书信;你对自己的感情完全失去控制,要么郁郁寡欢长久的不言不语,要么如癫痫发作似的突然怒发冲冠。凡此种种性格扭曲、狂躁和情感失控,我在给你的一封信中都已提及——这信你把它随便丢在萨瓦伊或哪家旅馆,而让你父亲的辩护律师得以出示给法庭——那信中不无悲怆地恳求过你,假如你那时能认识什么是悲怆的心情和言辞的话——我说,这些就是我为什么会对你与日俱增的索求作出致命让步的根源所在。你会把人磨垮的。这是小的胜过大的。这是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在一出剧本的什么地方我说过这是“唯一历久不衰的暴政”。
而这又是无可避免的。生活里,每一种人际关系都要找着某种相处之道。与你的相处之道是,要么全听你的要么全不理你,毫无选择余地。出于对你深挚的如果说是错爱了的感情,出于对你禀性上的缺点深切的怜悯,出于我那有口皆碑的好心肠和凯尔特人的懒散,出于一种艺术气质上对粗鲁的言语行为的反感,出于我当时对任何事物都能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出于我不喜欢看到生活因为在我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小事(我眼里真正所看的是另外一些事)而变得苦涩不堪的脾气——出于这种种看似简单的理由,我事事全听你的。自然而然地,你的要求、你对我的操控和逼迫,就越来越蛮横了。你最卑鄙的动机、最下作的欲望、最平庸的喜怒哀乐,在你看来成了法律,别人的生活总要任其摆布,如有必要就得二话不说地作出牺牲。知道大吵大闹一番你就能得逞,那么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粗撒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毫不怀疑你这么做几乎是无意识的。最终你不知道自己急急所向的是什么目标,或者心目中到底有什么目的。在尽情利用了我的天赋、我的意志力、我的钱财之后,贪得无厌的心蒙住了你的眼睛,竟要占据我的整个生活。你得逞了。在我整个生命最为关键也最具悲剧性的那个时刻,正是我要采取那可悲的步骤开始那可笑的行动之前,一边有你父亲在我俱乐部留下一些明信片恶语中伤我,另一边有你用同样令人恶心的信攻击我。在让你带着到警察局,可笑地去申请拘捕令将你父亲逮捕的那天早晨,我收到的那封信,是你所写的最恶毒的一封,而且是出于最可耻的理由。对你们两人,我不知如何是好。判断力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恐惧。老实说,在你们的夹攻下,我欲逃无路,盲目地跌跌撞撞,如一条牛被拉向屠宰场。我对自己心理的估计大错特错了。我总以为小事上对你迁就没什么,大事临头时我会重拾意志力,理所当然地重归主宰地位。情形并非这样。大事临头时我的意志力全垮了。生活中说真的是分不出大事小事的。凡事大小轻重都一样。主要是由于最初的无动于衷,让那凡事听你的习惯很没有理性地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不知不觉地,这成了我禀性的模式,成了一种永久的、致命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佩特会在他的散文集第一版那言辞微妙的跋中说道:“失败就在于形成习惯。”当他说这话时,牛津的那些死脑筋们还以为,这话不过是故意将亚里士多德有些乏味的《伦理学》文字颠倒过来说罢了。可是话中隐含了一条绝妙的、可怕的真理。我允许你榨取我的性格力量,而对我来说,习惯的形成到头来不止是失败,而是身败名裂。你在道德伦理上对我的破坏更甚于在艺术上。
逮捕令一旦批了下来,你的意志当然就主宰一切了。当我本应在伦敦听取律师的高见,冷静地考虑一下我让自己一头钻进去的这个令人发指的圈套——你父亲至今一直称它为陷阱——你却硬要我带你去蒙特卡罗。在这天下首屈一指的肮脏地方,你好没日没夜地赌,只要赌场不关门。至于我呢,赌纸牌没兴致,就一个人留在门外头了。你不肯花哪怕五分钟时间同我讨论你和你父亲使我面临的处境。我的事不过是为你付旅馆的费用和赌债而已。只要稍稍提及我面临的严峻处境你就心烦,还不如人家向我们推荐的新牌香槟更让你感兴趣。
我们一回到伦敦,那些真正关心我安危的朋友恳求我避到国外,别去打一场无望的官司。你说他们这是居心不良,我要听他们的话便是胆小鬼。你逼我留下来,可能的话在审判席上靠荒唐愚蠢的谎言伪证顶住。最终当然是我被捕入狱,而你父亲则成了一时英雄。何止是一时英雄,你们家莫名其妙地跻身于神仙圣人之列。好像历史也带上了一点哥特式的离奇古怪,从而使历史和史诗之神克里奥成了众缪斯中最不正经的一位。靠着这份离奇古怪,结果是你父亲在主日学校的文学里将永远活在那些个心地和善纯良的父母之中,你将与少年撒母耳并列,而在地狱最底层的污渎中,我将与杀害儿童的雷斯和性变态的萨德侯爵为伍。
……
译序
自深深处
De Profundis
译后记
★千年文学产生了远比王尔德复杂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魅力。无论是随意交谈还是和朋友相处,无论是在幸福的年月还是身处逆境,王尔德同样富有魅力。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