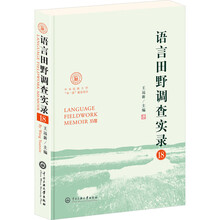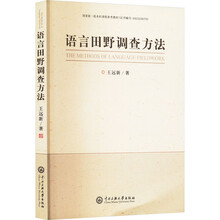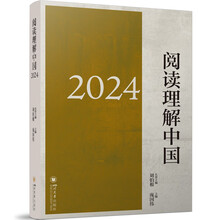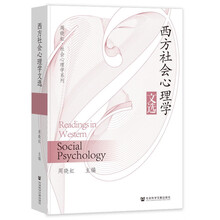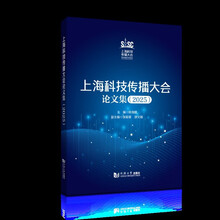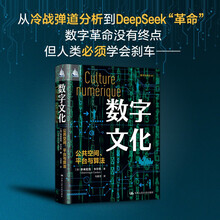—— 第五章 《案例分析》
社会化媒体上知识生产: 文本与实践
——以“新浪微博禁评事件”为例
We make tools, You make them do.
社会化媒体还是社交网站?谣言乱象抑或是新的启蒙运动?作为中国(zui)大的社会化媒体,新浪微博(Sina Weibo)具有其独特的技术架构,并通过中国民众、媒体、机构的使用实践互动出一套具有独特“表达含义”(Expressive Meaning)的知识生产、知识接收与知识发酵的方式;同时,这一过程还具有一种“记录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 能够体现出现今中国社会中的某种糅合混杂的世界观构成(Weltanschauung Construction),即民众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媒体依旧是政府把控局面的重要场所,而传播权力归属是社会各方力量争夺的目标。
一、 问题的缘起: 被关闭了的“评论”功能
2012年3月31日,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新浪微博的官方网站上出现了这样一条公告:
新浪微博公告
各位微博用户:
(zui)近,微博客评论跟帖中出现较多谣言等违法有害信息,为进行集中清理,从3月31日上午8时至4月3日上午8时,暂停微博客评论功能。清理后,我们将再开放评论功能。进行必要的信息清理,是为了有利于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流环境,希望广大用户理解和了解。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条公告意味着新浪微博,中国用户量排名第1的社会化媒体在这三天的时间内,其3亿用户无法对他人发布的微博直接评论,只能“裸转”(只转发不评论)或“转发并评论”(以下简称“禁评事件”)。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这次禁评事件的原因在于之前有人利用社交媒体散布“谣言”。但是,这一举措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首先,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能否可以被政府行为予以禁止?
其次,什么样的谣言需要政府出台这样的举措予以惩戒?
再次,经由此次禁评事件之后,对中国社会,民众又获得了怎样的认识?
评论,作为舆论的一种话语表达形式,由传播者使用语言符号生成,其含义产生在特定的语境(context)当中,并随着语境的变化与使用的变化进行“旅行”。
社会化媒体上的评论可以看作是现实生活中的街谈巷议的“网络版”,其作为一种内容生产,(zui)为活跃也(zui)难以把握。尤其是在中国,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属性与定位暧昧游移,使用社会化媒体的群体复杂多样,政府又缺乏对此成熟的认知与完善的法律,致使这种原本隐匿着的言论“洪水”突然现身之时,乱象频发,其合法性与可能性经由此次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诚然,“乱”或“不乱”是从管理的角度对其所进行的定性,但是如何来认知这种“高度语境化”的“知识”,倒是颇值得探讨和追寻。
二、 视角选择、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一个事物经由不同的视角可以被观到不同的样貌。作为互联网产品的一种,社会化媒体具有很多互联网本身的特质和特性。之前的研究均从不同的视角给出过在“他们”眼中的互联网意味着什么的解答。
涂尔干—功能主义传统认为互联网增强了社会的有机团结,因此他们着重关注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更关注互联网造成的文化霸权以及相应的精英统治;韦伯主义传统则从“理性化”视角,强调互联网将少了时空限制,并由此生成能“区隔”身份地位的新文化;贝尔和卡斯特则认为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说“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数字信息技术为社会结构的“网络形式”的普遍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哈贝马斯等人则强调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实践的作用,而批判理论则强调互联网对艺术和娱乐媒体的影响。
无疑,这些视角都揭示出互联网的部分特质,而这些特质在社交媒体的研究中也有所发现。现在对社会化媒体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化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结构性扩张在新闻生产方面的作用与价值。二是社会化媒体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包括网络舆论研究。三是社会化媒体与线下行为的互动与影响。四是社会化媒体与制度民主和社会权力。五是社会化媒体的商业前景开发与应用。
需要指明的是,现今对社会化媒体的很多研究都是功能主义取向的。功能主义的问题在于,“这种方法……试图将多元的文化领域用一致(Correspondence)、功能(Function)、因果联系(Causality)、相互作用(Reciprocity)等方式联系起来”。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去深究,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为什么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需要且必须要有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
。而罗伯特?默顿认为,“知识社会学主要致力于探究知识与人类社会或人类文化中存在的其他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由于知识社会学的哲学基础认为,“在经验过程中,当主体的兴趣集中在世界的某一特殊方面时,客体就显示给了主体”。因此,如果想要“发现”事物,必须“关心理智和思想产生的实际社会条件”。
换句话说,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是其研究对象与其存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目的是经由对研究对象的全方面把握更好地理解两者,而(zui)终目的是试图理解在某些历史—社会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
而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的勾连(articulation)恰恰契合了这样一种研究设想。
首先,社会化媒体上的“评论”在研究过程中(zui)经常被关注的两个问题是“碎片化”与“谣言”。“碎片化”的提出是相对于完整的系统的理性地如“支配地位的权力形式”、一般的“知识”而言的,而感性的表达与零散的只言片语无法达到“知识”的要求。但是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也许单独的表达(Utterance)不能称之为知识,但是当这些信息汇聚成为一个整体(Totality),它就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算得上是一种“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不是先验地就存在的,而是需要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和产生的,因此那些谈话从实践层面上看是成为知识的必经途径,是“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碎片化”不仅不再是一个研究障碍,相反,对于世界的认识只能从“碎片化”的言论中提炼得到。相对应地,如果没有总体性的理解则无法理解部分。仅仅是收集到了海量的经验材料并不能说明对整体的世界观已经有了把握。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现象的研究是为了获得更高层面的对于整个社会世界观的认识,没有后者,前者的行为与现象将无从理解;后者虽然不依赖于前者而存在,但是必须从前者碎片化的内容中提炼出来。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只有把握整体才能理解局部的论述,而每一个碎片中都有整体”。
其次,“谣言”之所以称之为“谣言”,关键的点在于“被定义为不真”。假的背后原因诸多,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谣言”是如何被制造或者被定义为“谣言”的,换句话说,每人每天都在撒谎,为什么只有这些成了“谣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被研究的对象充分地展现(Express)出来,但是之前的“谣言”传播基本上都是“人际传播”,缺乏研究的文本与样本。由于世界观是潜藏在人们的内心中的,在之前的经验材料的搜集中并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而恰恰是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谣言”被记录下来,“谣言”可以被追溯,这较之从前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更像是一种自发的真实的表达。而“记录性阐释的历史就是阐释的事物本身的历史”。
再次,当我们面对社会化媒体上海量的传播者与其生产出来的信息或言论,传统的功能主义或其他方法只能带给我们对某一问题某种高度“去语境化”的解读,但是就对于整个事物的理解来说,并不能给出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zui)为关键的一点,功能主义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归类以便进行“理论化”(Theorize),而这必然伴随着对信息的类型进行分类和取舍,而分类和取舍的背后必然带有意图。因此如果比较极端地说,所有的功能主义研究背后都存在着作者本身的世界观,这必将影响到(zui)后的结果,功能主义所宣称的“(jue dui )客观”其实掩盖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但是知识社会学并非宣称自己研究的背后没有世界观,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这种研究包含了对知识活动背后的动机的探索和对思考过程本身受社会生活中思考者参与的影响方式和程度的分析。”
此外,知识社会学还致力于研究“无法被理论化”(the Atheoretical)的东西,这点已然超出了功能主义的能力范围。之所以会无法被理论化,原因在于“事实上,世界观的问题在于它的实质来自它的内涵之外”。这一特质的基础是人类会同时存在于几个不同的维度世界中。
其表现形式就是评论的主体同时栖居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评论的形式变化极多,内容差别又大。但“无法理论化”的东西不等于没有理性(Rationality),如果能够适用一种特殊的阐释手法,照样可以将其具形。而方法就是要回归前理论(Pretheoretical)的发生阶段,回归日常生活。
具体落实到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知识社会学认为需要对以下内容进行研究:
知识社会学在对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所关注的不仅是盛行一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包括(1) 这种思想产生的整个社会背景……以及促使某些集团有意识地宣传这些思想并在更广泛范围内传播它们的(2) 动机和(3) 利益……此外,知识社会学想要说清楚某个社会集团如何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4) 表达。与各种类型的知识相一致的认识和用来发展各种知识的相应的(5) 社会资源,对于理解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对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这些变化是由下述因素造成的: (6) 像技术知识这样的某些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技术知识的运用使得人类日益控制自然和社会成为可能。同样,由于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思想在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它便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到了(7) 传播思想的机构和手段上,以及询问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是,它把注意力集中于(8) 现存教育制度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制度反映和影响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方式。(9) 知识社会学也对报纸、知识的普及及宣传的作用给予了适当关注。(10) 知识活动框架内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11) 知识活动的载体,即知识分子。
因此,根据上述的方法并结合社会化媒体的实际操作,我们继而可以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第1,社会化媒体在中国诞生与发展的整个社会语境如何?
第2,中国的社会化媒体是如何架构的?
第3,中国媒体的操作准则与指导方针如何?
第4,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第5,不同的言论各自代表了何种利益诉求?
而这些需要研究的问题落实到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中,则被划分进入三个不同的层次(Strata): 在讨论知识社会学对外部世界(Global Outlook)的理解方面,认识通过三个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隔的层面逐步向上。首先是客观意义(Objective Meaning),其次是表达意义(Expressive Meaning),再次是记录意义(Documentary Meaning)。其中,客观意义可以经由事物所展示的现象来把握,但是前提必须是事物可以被展现出来;表达意义主要是指个体的主观认识,需要通过对事物所处的语境和事物的历史来把握;记录意义来自前两者的综合,但它们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叠加,而是记录意义来自其中但又可以超越其独立存在。这里的记录意义如同整个世界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民族气质(Ethos)。所有的三种意义都兼具内容与形式。因此,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化媒体进行分析,我们希望可以沿着这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逐步深入,于是原来的问题就变化成为:
第1,客观意义: 社会语境,媒体架构,技术手段。
第2,表达意义,方针政策,使用习惯。
第3,记录意义,行为意义,权力分析。
下面的分析我们将沿着这三条思路逐步展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会采用比较的方法,原因有两点: 一是按照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取得综合的认识需要采用三种非正统的研究方法(Unorthodox Methods),即将不同层面的分类抽象后相互整合进彼此;调查经济—社会与知识氛围之间的一致程度;研究文化对象之间的并行对应结构。因此,如果想要知道A是什么,需要通过与A的外延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出。不仅要比较弥散的话语(Discursive Utterance),还要比较固定的结构因素(Nondiscursive Elements of Form)。二是通过将不同的社会化媒体进行比对,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中国社会化媒体的存在方式,这不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结果,而恰恰是在不断的实践使用过程中逐步与环境互动形成的,而这也指向了(zui)终的记录意义所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