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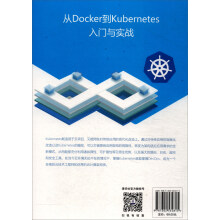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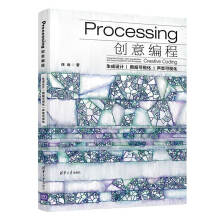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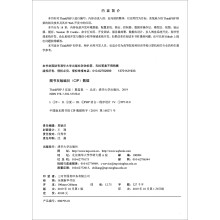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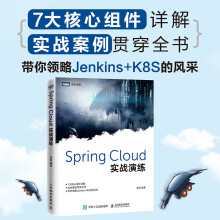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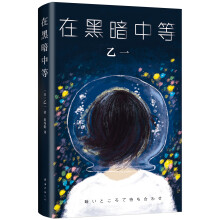





古罗马诗人想象中的中国影像
也许是得自希腊化时代或更早时期的传说,由于距离遥远和文化差异,中国的形象被赋予了诗意和想象,漂洋过海,在古罗马文献中演化成一朵奇葩。在罗马黄金时代三大诗人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Ovid)的诗作中,赛里斯的形象十分奇妙。而在风格迥异的散文家的作品中—精炼的西塞罗(Cicero)、犀利的塞涅卡(Seneca)和写实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赛里斯代表着奢侈或瑰丽的东方未知世界和人间乐园。
尽管作家们以赛里斯的故事作为其宏篇大论的注脚,或壮丽诗篇的点缀,赛里斯国与赛里斯人,还是以斑驳的印象凑出了一幅有趣的拼贴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形象。维吉尔的《田园诗》(Georgics)和贺拉斯的《抒情诗集》(Odes)分别提到了赛里斯人从树上采羊毛和赛里斯国产的坐垫。现存文献中的serica(其形式为复数,单数为sericum),即“赛里斯织物”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公元前1 世纪抒情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的《哀歌》(Elegies)中。自此以后,赛里斯这一名称便与西方世界的丝绸供应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古典世界以来,这种价抵黄金的名贵织物的来历成为西方作家笔下的难解之谜。而赛里斯商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经商的诚实与奇特方式,也成为希腊罗马史家津津乐道的内容。
老普林尼对中国人的想象
老普林尼所著的《自然史》对赛里斯的记载颇为详细,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特别是有两处提到了赛里斯人的特征:“(在世界东方)首先遇到的一族人是赛里斯人,他们以其树木中出产的羊毛而名闻遐迩。赛里斯人将树叶上生长出来的白色绒毛用水弄湿,然后加以梳理,于是就为我们的女人们提供了双重任务:先是将羊毛织成线,然后再将线织成丝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劳,而取回它则需要从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这就是一位罗马贵妇人身着透明薄纱示其魅力时需要人们付出的一切。赛里斯人举止温文敦厚,但就像其树林中的动物一样,不愿与人交往,虽然乐于经商,但坐等生意上门而绝不求售。”
接下来的一段描写更具有戏剧性:“赛里斯人居于伊莫都斯山(Hemodus)以外,(锡兰的)人们曾经见过他们,以其商业而著名。(锡兰使节)拉契亚斯(Rachias)的父亲曾经造访过赛里斯国,而使节们自己也曾见过赛里斯人。他们描述说赛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长着红色头发、天蓝色的眼睛,说话声音很粗,交易时不说话。这一叙述与我们的商人所述相同:他们把运去的货物放置在河对岸,与赛里斯人用来易货的商品并列,如果赛里斯人满意就取走货物。”与梅拉所述一样,老普林尼的记载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对赛里斯人贸易方式和外形的描述,在古典时代诸作家中是最详细、最全面的。从他的描述来看,赛里斯人绝非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内地的汉族人的形象,而是具有非常像欧洲人外形的民族。这恰恰与新疆地区当时居住的人民形象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