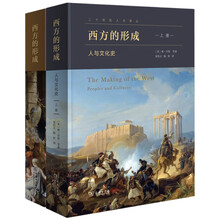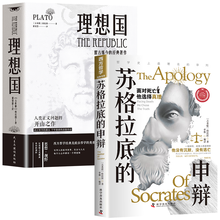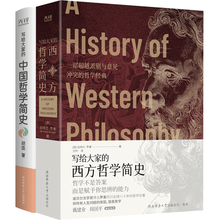天才的诞生之地,晴朗的天空下
营养问题与地点和气候密切相关。没有人可以真正四海为家;凡是必须全力以赴以完成伟大使命的人,在这方面的选择尤为苛刻。气候阻碍或加速新陈代谢的影响极大,任何选择地点和气候方面的差错,不单是会使人远离自己的使命,甚至还可能中止他完成使命的进程,使得他根本无法正视这种使命,使得他身上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动物元气,去取得那种冲入精神王国的自由,去令他意识到:此事舍我其谁?
最轻微的内脏惰性一旦形成恶习,就足以使天才变成庸人,变成“德国式”的凡俗之辈;德国气候本身就足以使强健而英气勃勃的内脏变得意志消沉。新陈代谢的速度与精神步伐的轻快或滞重关系紧密;精神本质上也是一种新陈代谢。我们可以枚举杰出人物曾经生活或正在生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诙谐、狡诈、阴险属于幸福的一部分;天才在这些地方都有宾至如归之感。所有这些地方都有着优越的干燥气候。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天才的诞生有赖于干燥的空气,有赖于晴明的天空——即是说,有赖于快速的新陈代谢,有赖于不断汲取巨大恢宏力量的可能性。我知道一个例子,有一位心智开明、注定有伟大命运的通人,仅仅由于他缺乏选择气候的微妙本能,最终变成了一个狭隘固陋、喜怒无常的专家。假若不是疾病迫使我去寻觅理性,去思索现实中的理性,我自己最终或许也会沦落到这种状况。现在我经过长期的经验,就如用精密准确的仪器对自身进行测定一样,已经非常熟悉气候和天象造成的影响。即便是在极短的旅途中,比如,一次从都灵到米兰的行程,我自己的生理系统便读出了空气湿度的变化。因此我不无惊惧地想起一个可怕的事实:除了最近十年,我的一生中那些有生命危险的岁月总是在一些于我极不相宜的错误地点度过。瑙姆堡、舒尔普福塔、图林根行省的广大地区、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这些对我的生理状况来说都是不幸的地点。
假如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没有留下任何愉快的回忆,那么在这里提出所谓的“道德上的”原因也是愚蠢的,诸如无可争辩地缺乏足够的社交: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缺乏社交,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快乐而勇敢的人。毋宁说,对生理问题的无知——该死的“理想主义”——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是完全多余以及愚蠢的东西,从这个“理想主义”中长不出任何优良的果实,并且无可补偿、无法抵消。这个“理想主义”应该为这些后果负责:我的一切失利、一切对伟大本能的偏离、那些使我背弃一生使命的“谦卑”。比如,我成了语言学家——为什么不是起码当个医生或者其他什么使人大开眼界的人物呢?
在巴塞尔生活期间,我全部的精神食谱,包括日常活动的安排,完全是毫无意义地滥用我非凡的精力,没有任何补给来抵偿这种消耗,甚至也根本不去考虑消耗和补充的问题。那时我全然没有为自身考虑的敏感,没有命令自己去自我保护的本能。那时我将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我“无私忘我”,忘却了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这一点我是永远不能自我原谅的。当我差不多走到生命的终点时,正因为我接近了生命的终点,我开始反思我一生中这个基本的非理性——“理想主义”,是疾病才将我带向了理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