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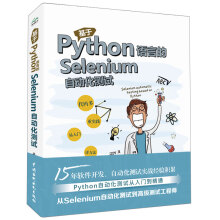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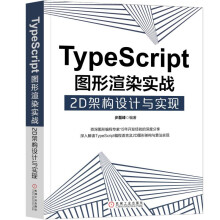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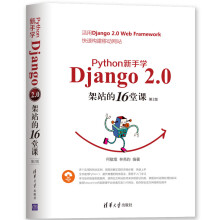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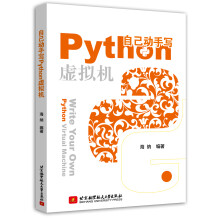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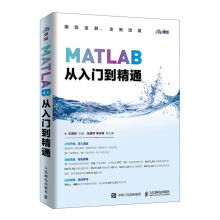



1939年4月1日,战争终于结束了。
当朱莉安娜看到从战场活着回到家的丈夫曼努埃尔,她显得既高兴又难过。
因为,她知道,另外一场战争从这一天这一刻开始了。
为了在这场一家人对抗一个国家的战争中活下去,只能藏着。
一个儿童座椅,这是藏身之地唯*能容下的东西。
他们必须无比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个细微的失误都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甚至连女儿穿着婚纱出嫁时,父亲也只能透过钥匙孔偷偷地观察,哭泣,独自庆祝。
这场每一秒钟都如履薄冰的战争,一直打到了1969年4月12日。
内战,不是三年,而是三十三年。
——————————————
※英国口述史研究先驱,罗纳德`弗雷泽,亲自采访
曾经轰动过整个西班牙的小人物,他的传奇人生。
※一个家庭三十三年的苦难,一个国家半个世纪的痛史。
※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夹缝中,藏起来!活下去!无论什么代价!
——————————————
告发只需要三个人,一个签字,另外两个作证。
唯*的裁决只有:枪决。
活下去也只需要三个人:丈夫、妻子和女儿。
《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个男子为了躲避死刑,躲藏在自己的家中整整三十年。主人公曼努埃尔?科特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米哈斯村的村长,在佛朗哥势力1939年夺权后成为通缉对象。为了活下去,科特斯躲藏在家中直至1969年大赦颁布。本书的叙述基于罗纳德?弗雷泽大量的深度访谈及口述史资料,它记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磨难,也描绘出西班牙至暗时刻。
<四>藏着:又二十年(1949—1969)
玛丽亚
我和妈妈不一样,她一直很悲观……你永远可以抱希望……而且有时候……它会成真,不是吗?
到了交男朋友的年纪时,我面临着一些问题。爸爸从来没有对我的行为约法三章,他在这方面非常宽容,不干涉我。但妈妈不一样,她以为我可能会跟村里不认识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她几乎要抓狂了。人们很快就告诉了她有个男人喜欢我。
“要是让我看到你跟那个陌生人讲话……”妈妈说,“哪个陌生人都别想到家里来,更别说娶我女儿把她从村子里带走。”
因为年轻,我很高兴能认识一个新面孔。但由于妈妈的原因,我没有成为他的女朋友。他给我写了很多信,妈妈看到的时候说她要把它们撕掉。她害怕我会回信,会慢慢爱上这个年轻人,然后嫁给他。要是这样,我就得离开家去他住的地方生活。这是妈妈不愿看到的。爸爸从来不说什么,但妈妈——唉!
我想,如果是他仇人的儿子想追我,他应该会说点什么。父辈做的事不应该让儿子负责,不是吗?不过,我确信爸爸会告诫我。让他的仇人,一个想看他毙命的人的儿子到家里来,不,我不可能这么做。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让他们这么痛心——我不可能答应这么做。
爸爸从来不直接跟我谈论政治。但我经常听到他和爷爷谈事情,有时和妈妈也谈。我了解他的想法,也很清楚村里谁是谁,还有他们的父亲过去做过什么。我不想让他的政治对头到家里来。
直到结婚后我才把秘密告诉丈夫。我们交往的那几年,我不需要谁来告诉我要保密。虽然我爱他,也看得出来他爱我,但男女朋友总有分手的可能。那时就会多一个外人知道——谁说得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不清楚男朋友来看我的那些晚上,他怎么会没听到过爸爸的声音?有天夜里,楼上砰的一声让人吓了一跳。“那是什么声音?”男朋友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噢,肯定是那只猫把什么东西打翻了。”我等待着更多响动,但幸好没有了。后来爸爸承认,他从椅子上起来的时候把火盆踢翻了。
妈妈老是说,她和爸爸处对象的时候外婆不许她做这做那。可是,我看不出来她有什么不同!她不准我在门口等男朋友,而且他离开的时候我不能和他一起走。我星期天和他出去的时候,妈妈也跟着。要是我们去电影院,她会在附近的朋友家等着陪我回去。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对长辈是另一种尊重。如果我想和男朋友去哪里,我绝对不敢直接问爸爸。我会找妈妈说:“告诉他我想和男朋友去某个地方,问他行不行……”妈妈会回来告诉我他的话。并不是说爸爸反对过,只要他知道我们是和可靠的人出去就行。但我只能在问过他后才能答应。男朋友经常奇怪为什么我不能立刻回答他。
我们搬到这栋房子后,我就不那么害怕爸爸会被发现了,因为警卫队没有来这里搜查过。最让我害怕的是他会生病。他身体痛的那天把我吓坏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经历那样的情景。
我是 1960 年结的婚。那是一场悲喜交加的婚礼,因为爸爸不能到场。我几乎疯了一样想找理由从朋友身边溜走,去跟他道别。她们一刻也不让我得闲。“玛丽亚,别把这个忘了。玛丽亚,那个你收拾好了吗?”我走到了门口,行李已经放到车顶了。就在这时我转身跑进屋子,终于脱身了。我跑到楼上亲吻了爸爸,回去的时候丈夫正等着我。“你去哪儿了?”“噢,我忘了点东西,刚刚去卧室拿了。”“不是的,我看到你进了厨房。”他说。幸好车开动了,我们兴奋得没有再说什么。
整个蜜月期间,我心里一直想,我必须告诉西尔韦斯特雷……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最后一天我鼓起了勇气。我们在公寓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说。“啊,什么事?”“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好吧,是这样,我爸爸在我们家里。”“啊。”他看上去并不意外。“是吗?”他说,“我确实感觉偶尔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告诉了他原因,他没有生气。不过,他说我们应该更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想过我爸爸很可能在马拉加。他的一个理发师朋友认识我爸爸,而且经常对他说我妈妈肯定知道他在哪儿。他想过这是真的,因为我妈妈每星期都去马拉加。但他从没真的想过他在我们家。现在他知道了秘密,也和我们一样守口如瓶。
1961 年,我的第一个女儿罗莎玛丽出生了。她有白血病,但我们不知道。我生第二个女儿的那天,她出现了第一次大出血。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在马拉加的医院里。妈妈带她去看了村里的医生。他只说这种情况很罕见。第二天,妈妈带她去看了马拉加的一位鼻科专家,因为她是鼻孔大出血。他告诉她必须要做血样分析。从那一刻直到她五个月后去世,医生让她受了许多折磨和痛苦。她是十九个月的时候死的。
医生从没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一直骗我们说她可以治好。我带着二女儿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无法把罗莎玛丽从她的小床上抱起来。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妈妈怕我用力抱她伤口会脱线。那时候她就开始带罗莎玛丽,直到孩子去世的前一天,几乎都是她和我爸爸在照顾。我觉得比起对我,孩子更爱我的父母,她更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有时丈夫会说:“罗莎玛丽,你不留下来和爸爸在一起吗?”她会回答:“不,不,我要跟外公外婆走……”我的爸爸非常爱她,总是陪她玩,逗她开心。
可怜的孩子,她受了那么多罪!五个月的输血、打针、抽血。 她一个星期要去马拉加看三次医生,他们一直说她会好起来。一般是我妈妈带她去,因为我要照顾刚出生的宝宝。但有一天是我和丈夫去的,他让医生坦白告诉他罗莎玛丽是什么问题。“她会好起来的,就是要时间,没别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给她吃合适的药,孩子会治好的。”
她半夜的时候死在了我怀里,当时我们正在赶去看医生的路上。两天前她刚去过马拉加,但我看得出来她多么虚弱。最后一晚我不愿把她留给父母,我让她睡在了我身边。要是医生告诉我们真相,她就不会那样死在车里。真是太痛苦了,虽然不论怎样都很痛苦,但让她在家里去世是不一样的。
我不能在出租车里哭。妈妈一直说:“别出声,别出声。如果骑摩托的警卫队把我们拦下来,你就要把她留在这里。别出声,不然我们就不能把她带回村子了。”我不得不强忍悲痛,不能哭出来。我只能坐在那儿,假装她还活着。如果警察把我们拦下来发现她死了,他们会坚持把她就地埋葬。从洛斯伯里切斯掉头开始,穿过丰希罗拉再到村里,一路上我必须忍住眼泪。唉!我的神经崩溃了,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谢天谢地,我的另外两个女儿很健康,她们都很乖。罗莎玛丽去世的时候还太小,没法跟外人说起我爸爸。但我的二女儿玛丽亚?德拉佩尼亚懂事后,我立刻开始不断叮嘱她。“女儿,要是你跟别人说外公在这里,警卫队知道了会把外公带走。他们会把他关进监狱,还会把我抓起来,把外婆抓起来,我们都会被带走。”我把同样的恐惧灌输给了她——还有后来的小女儿——就像妈妈对我做的那样。当然,两个女儿没有经历过我的遭遇,她们不了解我小时候承受的恐惧,警卫队不会经常来搜查,她们的妈妈也不会总是被盘问。我必须教给她们这种恐惧。“他们还会把爸爸抓走,把他关进监狱里,”我总在反复提醒玛丽亚,“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什么,姑妈和爷爷也不行,谁都不行。明白吗?”只要她有一丁点要跟别人说的迹象,我随时准备不再让她见我父亲。我一直在留意她。
我妈妈很担心,孩子的姑妈经常来带玛丽亚出去。“女儿,不要让她走,”妈妈会对我说,“她出去会说话,肯定会说漏嘴的。”“可要是我不让她去,他们会觉得我不想他们和她见面。”我回答。我不能不让她去,每次我都会警告她:“玛丽亚?德拉佩尼亚,记住!一个字也不能说!”从来没有,她没说过半个字。她六岁开始上学的时候,我要把她看得更紧了。最后,她有一天对我说:“妈妈,你真的觉得我会跟小朋友们说这件事吗?”
爸爸想了一个主意,不要给他起名字。这是个很好的预防措施。玛丽亚?德拉佩尼亚老是追着他问他叫什么。要是她不相信他没有名字,他会告诉她他叫卡拉达拉玛。然后她会说:“这不是名字,你的真名叫什么?”“卡拉达拉玛。”他总是这么回应。不用说,她是对的,谁会起那样的名字?
这是个玩笑,但毕竟很有用。只有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小女儿差点泄露了秘密。每年平安夜都有一档为穷人制作的电视节目,佛朗哥的妻子会在台下观看。那是一年中最好看的节目之一。我们一直喜欢看,因为有很多明星表演,还有弗拉门戈舞等等。节目开始之前,对门的邻居跑来问:“玛丽亚,你要开电视吗?”“不一定。”我说。如果她来,爸爸就会错过演出。从我们买了电视开始,这一直是我的难题。街坊邻居总想来看电视。头几个星期家里从早到晚都是人,因为我们是村里最先买电视的几户人家之一。最难办的是有斗牛赛的时候,我知道爸爸想看。我会装作头痛要躺下的样子。妈妈会站在她家门口守着,要是她看到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她会告诉对方我不舒服,而且孩子们都在睡觉。我经常要对街坊说:“噢,我不确定会不会开电视。”我的不情愿让他们觉得我很势利和冷漠。“唉!走吧。玛丽亚不喜欢我们在这儿。”他们会说。
总之,去年平安夜节目快开始之前,那个邻居来家里坐下准备看表演。我爸爸不能下楼。突然小女儿进来说:“外公呢?他不来看吗?”她就这么说漏嘴了。“你说爷爷?”我给了她一个警告的眼神说道:“不,爷爷今天不能来,他修鞋子的活还没做完。”我意思是让她明白我说的是我的公公。我在邻居身后又给她使了个眼色。“不行, 爷爷今天来不了,他在干活。”我又说了一遍,她懂了。
那次好险——可这么多年来,有很多次有惊无险的事都可能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但我们总算经住了考验。我从不放弃希望,也许爸爸有一天能自由地出来。我和妈妈不一样,她一直很悲观,总想着那些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事情还没发生的三个月前她就开始想!我很担心,但我不会愁还没发生的事情。你永远可以抱希望——就连女儿生病我也把希望保留到了最后。而且如果你不断希望,有时它最后会成真,不是吗?
……
新版序
序
〈一〉 藏着:最初十年(1939—1949)
最初几个月我一直躲在墙内的藏身处。我的妻子在里面放了一个儿童椅,逼仄的空间让我只能面朝一侧坐,两个肩膀挨着墙。我能站起来,但无法走动。从清晨直至午夜过后,我都被关在那里。
〈二〉 曼努埃尔和朱莉安娜:年轻的日子、村子、政治(1905—193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学校感受到的不公开始在其他方面变得明显。我能说出几千个这样的例子……
〈三〉 共和国、革命和内战(1931—1939)
要是我没有保持镇定,这里就会发生一场屠杀。
〈四〉 藏着:又二十年(1949—1969)
(玛丽亚)如果你不断希望,有时它最后会成真,不是吗?
〈五〉 释放
他穿上鞋后不知道该怎么走路。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朱莉安娜)必须搀着他,因为他一直滑脚。就算现在,他走路的样子也和以前不同。我看得出他跨的步子很大,好像对自己没把握一样。
〈六〉 今天:曼努埃尔
重获自由最初的那些天里,我觉得很反常。我已经太习惯藏着,习惯了藏着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以至于其他任何事都让我觉得不正常。
注释
大事年表
译后记